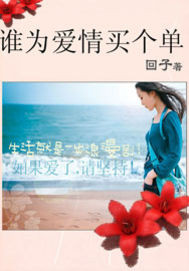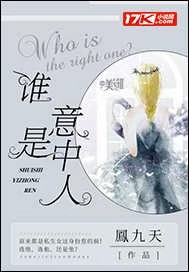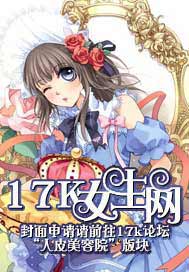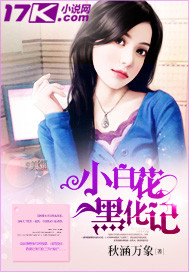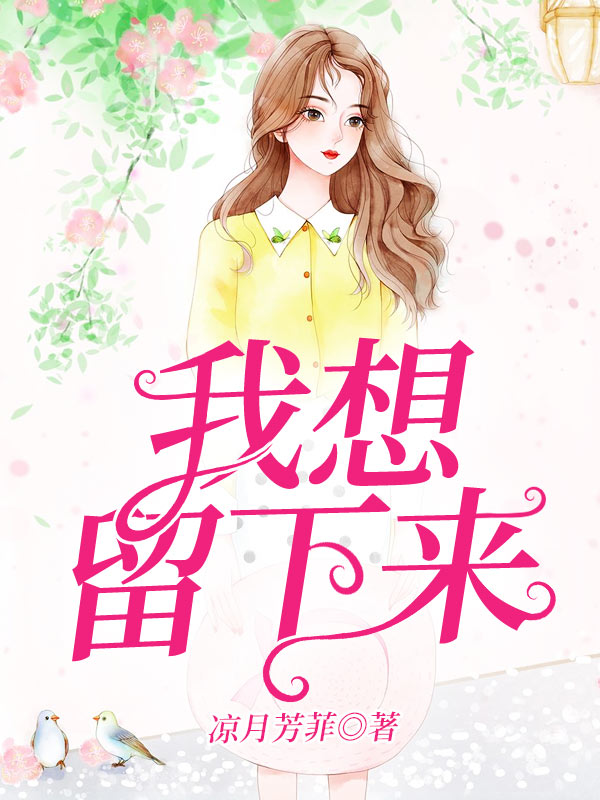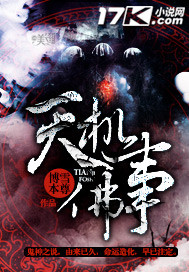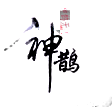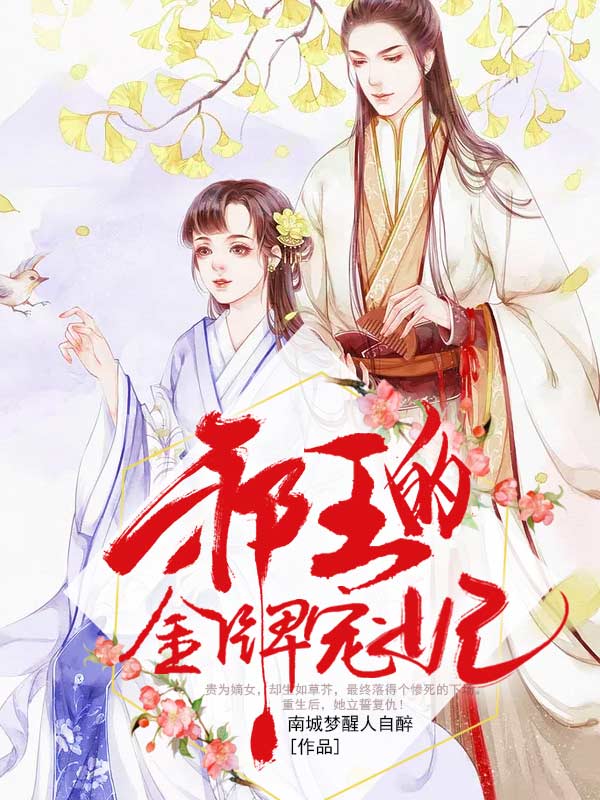杨家玉准备了一桌很丰盛的晚餐。七晕八素,样样俱全。两瓶张裕干红葡萄酒。亲手做了土豆沙拉。是专门托人从上海捎回的日本土豆。韭菜炒鸡蛋。买了一斤提山坡喜欢吃的蛏子。
这蛏子吃起来鲜,收拾起来可是麻烦死了,你得先拿淡水饮它一个小时左右,洗净沙砾控水后晾一会儿,然后投入滚水,待半开瓢时出锅,趁热剥壳。
剥壳时稍有不慎即会将碎壳片儿落进肉里,像玻璃一样锋利的碎片儿要刺伤人的,一斤蛏子约300只,她花去了半个下午的时间才将这些蛏子一只只剥出来。
乳白色的蛏子浆液奇美无比,单独盛进一只碗中,提山坡喜欢伴着酒一道喝下。
还有个儿大、肉肥的文蛤,也是夏天难得的美味。
听提山坡说,这钓蛏子、搂文蛤简直就是艺术。
蛏子是一种带壳筒体的动物,成年的蛏子长约十厘米,生长在浅海的滩涂上。
其巢是一个深一米左右的井状水洞,水洞的方向千差万别,纵横交错,而每个水洞里只有一只蛏子,它靠吸水浮沉,速度极快,天晴时浮在洞顶接受阳光和捕捉食物,遭遇天敌时则立刻潜至洞底。
逮住它需要一种特制的钓具。一根30厘米长、针一样粗细的钢丝,一头固定在一段竹篾上,另一头的末端弯成一只隐钩,蛏子在浮至洞顶时会用一个平“8”字符号将自己通道的方向伪装起来,那个平“8”字符号其实正是它的口腔,有经验的钓者一看就知道其通道的方向,将钩子在平“8”字上轻轻一摇,然后在它作出反应之前猛捅下去,就会将它半路截住。这个动作要求手力、速度和柔性完美无缺的配合,否则不但钓不到狡黠的蛏子,还会惊动它邻近的同类。
文蛤,当地人通常称之为“大蛤蜊”,有两扇生满棕色花斑的硬壳,分布于蛏子所在滩涂以下的深水区。逮大蛤蜊不叫“挖”,也不叫“捉”,而称为“搂”。
退潮后一直往下走,到水深齐腰时就可以搂了。也要有专门的家什,那就是一个铁齿钯,铁齿钯上镶了8-10根间距5厘米左右的铁齿,与长长的木柄呈65o角。作业时双手扶住柄中央,柄尾搭在肩头,一只耳朵紧紧贴上去,可以不要眼睛,向后缓缓倒行,当铁齿搂到大蛤蜊时,壳齿相触,就会有轻微的,如同金属般的脆响沿木柄传到耳朵。剩下的事情就好办多了,搂者首先按住铁齿钯不动,再走过去用脚背将大蛤蜊托起,最后被丢入系在木柄上的网兜里。
这种收获方式世代相传,已经存在了成百上千年。蛏子、大蛤蜊生了一茬又一茬,好像永无穷尽之日。但是近若干年以来,人们再也不满足于这种生产率极为低下的收获方式了,把25马力和50马力的拖拉机开进了海滩,然后像犁地一样一遍又一遍地将海滩的肌肤切开、掀起,于是海滩遍体鳞伤、面目全非,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蛏子、大蛤蜊遭到灭顶之灾,几乎被赶尽杀绝,连其幼小的子孙也多未能幸免。
蛏子消失了。大蛤蜊也消失了。拖拉机也离开了。
现在的蛏子和大蛤蜊,基本都是运自外地或人工养殖的,所以不仅价钱昂贵,也大不一样,只好发聊胜于无之慨了。
每次说及此事,提山坡多半就会来气。他说这些人的罪行丝毫不亚于发动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他们摧毁了裸眠谷,摧毁了大海,马上就要杀人了。
在提山坡出现以前,杨家玉对海味的认识不多,海蛏子、文蛤都是提山坡教会她吃的。
提山坡说,你闭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