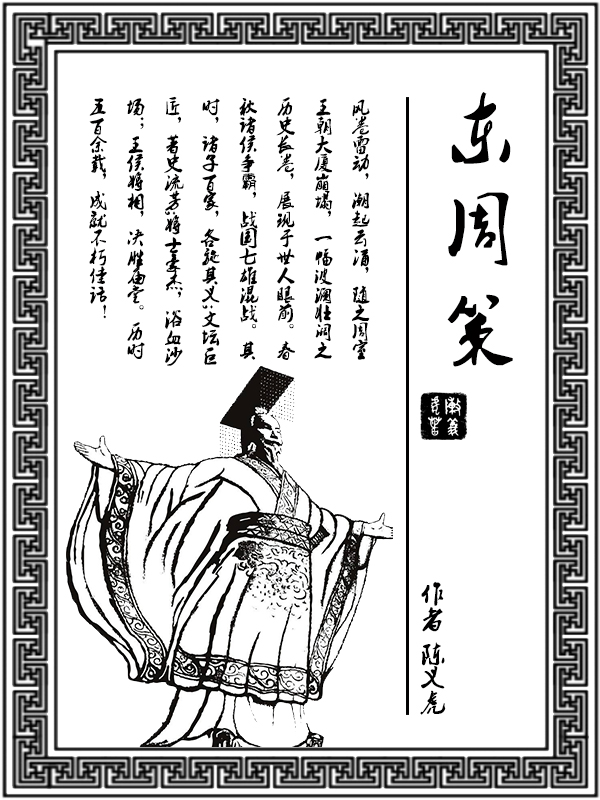阮闿的一声大喊终于使廖淳、二娃子与泥鳅三人停下了脚步,原来廖淳他们在听到阮闿讲述大树江村村民被杀的始末的时候,便已经怒火中烧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而此时阮闿却并没有把他们打听来的消息说完,除了大树江村村民们被杀的始末之外,阮闿他们还打听到了另一件事情。
朝廷派下了人来,目前正在郡中治所江陵,而据说这黄耀便是通过他在江陵的商人亲戚走的关系买的官,所以他得到了朝中来人的消息便赶紧动身去了江陵,估计又是走关系去了。
廖淳听了怒道:“什么?!去江陵了?什么时候走的?”
阮闿答道:“应该是今天午后的事情,因为据衙门里的人传出来的消息说,朝廷的人到了江陵这消息是中午才从江陵边传过来的。”
廖淳不等阮闿说完,便对着众人大吼一声道:“走!跟我去追!”说着就又要起身要往庙门外跑。
这时陈幕拉住廖淳道:“等等!”
廖淳问道:“又怎么了?再不追,他就要到江陵了。”
陈幕反问道:“追?去江陵的路有那么多条,你又不知道他走的是哪一条,往哪儿追啊?”
被陈幕这么一说,廖淳倒被问住了。而阮闿似乎又想起了什么,说道:“听衙门中的一个杂役说,他听到这狗官与他的县丞二人中午的时候曾在说华容道那边的事情,我想这狗官会不会走的是华容道?”
阮闿刚说完,泥鳅便站出来连连摆手否定道:“不可能,你是外乡人可能不知道,这华容道险,在南郡这边是出了名的,不说豺狼虎豹,单就那险峻的地形,那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达官贵人们便都吃不消走,所以这狗官怎么可能放着那一条条好好的官道不走,却来走这险峻的华容道,来遭这份罪?”
泥鳅一说,众人都觉得泥鳅分析得有道理,这华容道是可以排除了的。
但姜兰甫却说道:“泥鳅说得固然有理,但我倒也认为这狗官很可能走的就是这华容道。”
姜兰甫此言一出,众人便都看向了他,想听他到底能说出些什么道道来?
姜兰甫接着说道:“刚刚阮闿兄弟说,那狗官是中午才得到消息说朝中来了人的,而他午后便赶去江陵,走得如此匆忙,这说明他在赶时间。我以前来过南郡,对这边也有些了解,从中庐到郡治所江陵走最近的那条官道,也得穿过两个县,怎么着也得三四天的路程,但若是走华容小道,过了华容便是邔县,而过了邔县就是江陵了,邔县到江陵有宽敞的官道,那狗官要走的其实也只有华容这一小段的险路,而却可以缩短整整一半的路程,因此我觉得这狗官会走华容。”
众人听姜兰甫这么一说,也都觉得有理,这样一来到底走哪条道去追便又不知该如何抉择了,若是换了人多的时候顶多兵分两路,但现在一众人能打的,一共还不到十个人,那狗官要是随身带了县里的守军的话,众人要是分作了两路,那即便是追上了,也抓不了这狗官。
廖淳问陈幕道:“你怎么看?”
陈幕很干脆的回答道:“不知道。”
不过他回答完后,伸手一把扯过了边上的姜半仙道:“老家伙,你不是号称半仙吗?算算,那狗官到底走哪条道啊?”
姜半仙本来就是有些怕陈幕的,被他这么猛然间一拉,更是吓了一大跳,不过马上他就发现,其实陈幕并没有打算把他怎么样,于是胆儿也就又变大了,他用手掸了掸被陈幕拉乱的衣服,又拿捏起他那副算命先生的腔调来,缓缓的说道:“这个,占卜之事,只有疑事不决、左右为难、举棋不定之时才向天买卦,但如今这事又何用占卜啊?”
陈幕原本只是随便一问,他想既然选不好走那条道,那就让姜半仙算一算,算出哪条是哪条,权当听天由命,真算错了也无所谓,但姜半仙竟然装腔作势的这么说,陈幕便还当是他又在耍滑头不肯卜算,于是就火了起来,又扯着他的领口,一把把他给拎了起来,骂道:“老家伙,又给我耍滑头,现在还不是‘疑事不决、左右为难、举棋不定’的时候吗?快给我算,到底走哪条道?要是是算错了,我就再帮你松松筋骨。”说着又把自己的拳头捏得是咯咯发响。
其实姜半仙原本也没想要耍滑头,只是他装着腔调说话这语速便慢了,而他只说了前半句还没来得及说后半句,陈幕便已误解了他的意思,火了起来。经陈幕这么一恐吓,姜半仙便又吓得魂飞天外,于是也不敢再拿腔捏调的了,赶紧说出他后半句话来道:“此事确实不用算,我也觉得姜大侠说得在理,那狗官有县城内的守军护卫,根本就不会怕什么豺狼虎豹,指定走得是华容小道。”
陈幕听了这才放开姜半仙道:“娘的,早说不就结了。”
不过陈幕刚把姜半仙放下便又觉得,这姜半仙是在附和姜兰甫的话,想拿姜兰甫做挡箭牌,于是便又一把扯过还没理好被他抓乱衣服的姜半仙,恐吓道:“老家伙,不要以为你附和姜兰甫的话就没事了,要是说错了,我照样扒了你的皮。”说完才一把推开姜半仙,而后才又看向廖淳,去询问廖淳的意见。
廖淳听众人商讨了半日,原本暴怒的情绪也有些冷静了下来,他想了一下刚刚泥鳅、姜兰甫以及姜半仙三人的话,说道:“既然姜兄跟姜半仙都这么说,那么我们就走华容道。走华容道比走那些官道要近一半的路程,即便那狗官走的不是华容道,那我们也可以赶在他的前面在江陵城外截住他。但是华容道窄,我们去追那狗官时难以埋伏、隐蔽,不知道那狗官随身带了多少兵士,所以大伙还是小心为上。”
众人听了尽皆点头应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