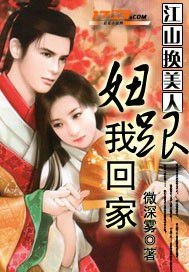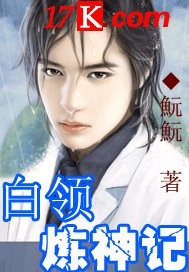御医进进出出,不多时连民间的大夫也被请来,再后来,听说直接派人到西戎和宁国去请医者,并发布通告:谁能救醒鄂尔苏赢皇子,赏黄金万两、暖玉矿山一座。
何不言奔着矿山来了。
诚然这是后话了,应含絮后来知道:何不言的到来,皆是池崇安排。
此刻,应含絮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阿喜和阿敏抱着绒毯过来,却被喝令不准为她添衣,唯有远远看着她渐渐不支,不到半个时辰,她已唇色发白、黑睫结霜。
“这样下去可不行……”阿喜说,“我去请大驸马。”
片刻后,大驸马没有来,鄂尔娜尹公主来了。
她走过应含絮身边,没有停留,径直往里去。
进了寝卧,看了眼昏睡的兄长,却未问候,直接对女皇说:“前段日子我拿嫂子出气,将她打了个半死,现在还没恢复呢,可以说是提前为哥哥出了气,母亲现在责罚她,着实是伤上加伤,过分了些,快叫人送她进来吧?”
“我知道你一开始就跟她不和,现在是为的什么要替她求情?你看看你哥哥,不知道怎么回事,竟跟个活死人般醒不过来!”
“母亲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嫂子兴许就是无辜的,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执意责罚她,这不是闹得自家人不和嘛?您一向教导我将来要恩泽天下、仁义为怀,怎么这一次自己反而……”
“行了行了,道理一大堆!”女皇打断她,板着脸生闷气,“我知道你的来意,罢了,就到傍晚吧,傍晚的时候,让她进来。”
“只怕她身子骨弱,没办法撑到傍晚。”
“我都已经做出让步了,你就不能消停些嘛?”
女皇亦是个固执的人,这大约也是母系社会最终会被父权体系打败的原因之一吧,女人总是感性的,并且不肯承认错误的。
***********************************************************************
临近傍晚的时候,应含絮也感觉自己快要撑到了极限,落在身上的雪已经积了厚厚一层,最里面的开始化冻,变成水渗入身体,寒意刺骨。
她摇摇欲倒,眼前一片花白,直至一抹紫影飞快逼近,将她扶稳。
应含絮抬眸,看到表情紧绷的辛容贺岚。
“我抱你进屋。”他说,随即附身欲将她抱起。
应含絮却拽紧了轮椅扶手,不肯动:“别……”声音出来都是寒气,虚弱不堪,可固执到死。
“你想死在这里吗?”辛容贺岚低低地怒问,带着狠意。
对,就是这抹狠意,应含絮心中恍然,正色问他:“苏赢昏睡不醒,是你干的嘛?”
他冷冽一笑:“不过是一起牵手走了几步路,叫唤都变得更亲切了?”
他嫉妒,他吃醋,他发狂,应含絮心中了然:“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纯粹是为了自己?不现实。
可是辛容贺岚还没来得及回答,应含絮便失去了得到答案的力气,终于因为受冻过度,而昏厥。
辛容贺岚一把将她抱起,转身往驸马府去。
鄂尔娜尹追出来,匆匆跟上,问他道:“我已尽最大努力向我母亲求情,再过半个时辰就能送她进屋了,你为何非要过来?你这样做要是被人看见,惹来非议,你怎么解释?”
“再过半个时辰,她就死了。”辛容贺岚只有这一句。
随即他粗鲁地窜开了自己卧室的门,把应含絮小心放倒在床上,然后回首怒斥鄂尔娜尹:“把门关上!”
鄂尔娜尹扣上了门,一脸委屈:“这么凶做什么?我都说我已经尽力啦!”
“你上次鞭打她的帐,我还没与你算呢。”辛容贺岚冷冷道。
鄂尔娜尹心中一慌,更觉憋屈:“辛容贺岚!这是你跟我说话的态度吗?你只是我捡回来的驸马,你的命是我救的,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的,你这样顶撞我怨怼我,就不怕本公主……治你的罪?”
辛容贺岚侧首一瞥,眼神冷若刀剑:“你大可来治我的罪。”
吃硬不吃软的鄂尔娜尹,怎么舍得治他的罪?她立马收拾了怒颜,与他道歉:“好了好了,我错了,我去请御医来,给她看看还不成吗?”
结果御医不来还好,一来,声称应含絮被冷气逼入骨髓,至阴至寒,必须要至刚至阳之男子赤身裸体为她取暖才可恢复。
辛容贺岚二话没说开始脱衣。
鄂尔娜尹当即急了:“你这是要做什么?给她取暖,随便找个男人不就行了!”
“不要再让我听到‘随便’两个字。”辛容贺岚警告道,“你出去。”
鄂尔娜尹不依,眼泪在眼眶内打转:“你是我的驸马啊,你跟她,不是早就应该断绝关系了吗?你这样,让我情何以堪?”
“所以我才叫你出去。”辛容贺岚的态度稍稍好转,口吻轻柔,“你不会明白我跟她经历过什么,两具都正在一点点死去的身体,才最适合相互群暖。”
鄂尔娜尹被他温柔眼神戳中心中柔软,泪如雨下:“你不会死的……”尽管不舍、尽管不甘、尽管一万个不情愿,嫉妒到疯狂,可最终仍是黯然转身,跑出门去,倚在门外廊柱下,克制自己不要去想屋里的温存,一个人压抑地哭。
***********************************************************************
池崇抱住应含絮,肌肤相亲,似熟悉,又似陌生。
窗外雪花飘飞,轻柔地纯净了整个世界,却又因着它融化的命运,而无情地宣告着红尘轮回的无奈。
这样透彻的寒冷,很难让池崇不去回忆那一年池府湖泊,当他闻讯赶来,只看到应含絮冰冷尸体孤单橫呈的时候,整个人瞬间如冻结般不能动弹的绝望,心在胸腔内凋零成碎片,全世界在一瞬间倾塌成灰烬。
那个时候,也是这样抱着她的身体,她的身体没有温度,凉得好像一只木偶。
没有忍住,池崇的热泪滴落在应含絮的颈侧,不知道昏睡的她,能否感觉得到这颗炽热?
***********************************************************************
应含絮醒来第一眼,看到何不言。
何不言叹气:“从前微胖的时候,看起来白白胖胖还挺可爱,现在瘦成这样,简直丑到不忍直视。”
环顾四周,应含絮锁眉:“难道我回了宁国?”
看也不像呀,除了何不言,其它一切看起来都是雪国的格调。
“是我来了北银国,来治你新任丈夫的昏睡症。”何不言解释道,“听说有矿山拿。”
“哦……”应含絮黯然,“我也有病。”
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何不言愣住,须臾,点头说:“没错你的确有病,旧疾、内伤、外伤、受寒、脑子进水,病得不轻。”
“有得治吗?”应含絮反问。
何不言笑:“池崇是你最好的良药。”
应含絮浑身紧张,盯着他问:“你也知道池崇……不,池崇已经死了,你现在看到的辛容贺岚,不是他!”唯恐何不言是常琴的人,应含絮警惕得很。
何不言又叹气:“就算我原本不知,被你这么一说,也大概摸得到点端倪,应含絮呀应含絮,长得丑也就算了,怎么脑子还不灵光?”
应含絮一副要灭了他的狠样:“你知道的太多了,我不会让你回去告诉常琴的,我要杀了你。”
“呦呦呦,凭您老这样还想杀了我?”何不言啧啧叹息,“你现在爬都爬不起来,怎么杀我?何况你要是杀了我?谁来救你的腿,谁来救你的心,谁来救你的池崇?”
“你会救池崇嘛?你是常琴派来的人,常琴只想杀了他!”
“没错,常琴的确是想杀了他,但我不是常琴派来的人。”何不言急了,“说你蠢不是骂你,你从来就没分清过好人坏人,我曾经为常琴做事,你难道看不出来我只是奉命行事吗?”
“你奉他的命,你就是他的奴仆……”
“我有个亲妹妹叫何不笑在他手里!”
应含絮怔住。
久久沉默。
应含絮幽幽问:“常琴做了那么多丧尽天良的事,过去你们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跳出来点醒我?”
“我理解池崇当时的愤懑和嫉妒,宁愿看你受伤一次,总好过一直忍受你的排斥,至于其他人……”何不言撇嘴,“谁会在意太子爷身边多一个蠢女人的死心塌地呢?”
何其赤裸裸的讥嘲?自己在他何不言眼里,果真是个又丑又蠢的女人,不知世人是否也是这样看待呢?
应含絮可怜兮兮地侧过身去,说:“我想睡了。”
被何不言一把揪起,怒斥道:“你才刚起来又要睡?你新婚丈夫却有可能永远都醒不过来。”
应含絮则极其淡定:“你既然是和池崇站在一个阵营内的,那想必鄂尔苏赢昏睡一事,你也有参与吧?”
何不言果然面露愧色:“药呢……的确是我给池崇的,但我只是让他下少许量,谁想到他把三个月的量全下进去了,没把人弄死算不错了。”
“三个月的量?”应含絮蹙眉,“怎么……你们本来打算让鄂尔苏赢在三个月内都处在一个时而昏睡时而清醒的状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