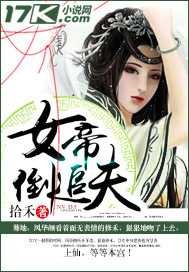颜溪声音好像带着哭声,但又好像在笑似的,她埋首在西门筑的怀里,脸被遮住了,所以此时此刻没有人可以看出她的真正情绪,她的声音在西门筑的怀里响起:
“其实我一点都不感到悲伤,我感到很幸福,真的,我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一个人,从来没有为一个人这样付出过,因为遇见了西门筑,我开始变得会很用力地去爱一个人,我这一生,没做过什么大事,我唯一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来到这里,遇见了你,然后,与你相爱,与你度过那么多的有笑有泪的日子,你让我学会了很多很多东西,让我幸福地拥有了自己的血脉,让我感受到生命里的每一缕清风,每一丝阳光都是那么的弥足珍贵,你让我相信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让我觉得自己是被爱的,是有底气的,所以,我才能在一些事情上,比以前变得更加坚定,更加的强大。”
“我以前一直没对你说过什么表露心声的话,直到你走了之后,我发现我有那么多的话想要和你说,想告诉你很多很多我的想法……现在你回来了,真好,一切好像还不晚,我们还有那么长的时间去诉说我们心中的所感所想。”
西门筑静静地听着颜溪的话语,他的眼睛里掠过一丝意味不明的情绪,看起来有一些幽暗,此刻的他表情很是奇怪,当然颜溪看不到,当颜溪从他怀里抬起头的时候,他的表情又恢复如常了,她看着他,笑盈盈的:“我说的,是不是啊?”
“是,我们还有一辈子的时间,我们会永远在一起,再也不分开。”西门筑笑着再度把颜溪揽进了怀里,可在颜溪看不见的角落,他的眼神又变得有些奇怪了,充满着让人完全读不懂的情绪。
时间过了很久,久到颜溪就快要睡着了的时候,西门筑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
“之前你说有一个男子一直在保护着你,那个男子,是谁?”西门筑状似无意地问道。
“是谁很重要吗?”颜溪笑了,顿时睡意全无,手指戳了一下西门筑的胸口。
“那个……也不是很重要。你继续睡吧。”西门筑目光躲闪地说道,表情也有点不自然。
“吃醋大王,真的是……”颜溪无奈地摇摇头,“我估计我不把那个男子的事情告诉你,你这一整晚都会睡不着了吧。”
西门筑讪讪地笑笑,颜溪看了直摇头。
“他啊,叫孙行远,是长净的朋友,长净有要紧事去了,他就来代替长净的位置,来暗中保护我,知道了吧?”颜溪对着西门筑说道。
“知道了。”西门筑点点头,好像在沉思着什么,颜溪刚想问他在想什么,为什么表情有点不大对劲,可是他却以一句“累了,要睡了”打发了颜溪。
颜溪也没有多勉强他,只是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颜溪自己也陷入了沉思,开始在软榻上辗转反侧起来。
颜溪,颜溪,颜溪……
颜溪永远也无法忘记孙行远那样呼唤她的声音,也无法忘记他那样握着她手的力道,他抱着她在怀里面,他在她耳边说,颜溪,别离开我,不要离开我。那样痛苦的呼唤,声音像是从喉咙口里挤出来的,充满了艰涩,却也饱含着那么强烈的感情。
那样的声音,那样的饱经痛楚,对她而言,是那么的熟悉,好像他是她生命中某个重要的人一般。
还有他的眼睛,那样桃花潋滟,好像有无数水波在里面荡漾,充满着迷离的眼睛,也是那样的熟悉,尽管他有时候眼神间充满了淡漠,可是她还是能从他的眼睛里,读出故人的味道,好像他们认识了很久似的,尤其是在交谈的时候,他们,有那么多的默契,好像,他完全知道她的想法一样。
这一切,虽然他没有刻意表露,可是她还是能够依稀感觉得出,有些情绪就好像藏于彼此呼吸的空气之中,于无声处脉脉流淌。
她还记得,他的心口附近,有一道陈年的旧疤。
这一切的一切,只是巧合吗?
颜溪这样想着的时候,忽然就狠狠地摇了摇头,自己真的是神志不清,有病了,西门筑就在她的身边,就在她一睁开眼睛就可以看得到,一伸手就可以够得着的地方,为什么她还要想东想西啊?有时候说不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是这么奇妙呢?有些人就是可以一见如故,就是可以倾盖堪比白首,有些人就是长了一双桃花眼,看起来好像对每个人都包含情义一样,实际上只是他眼睛里生来就好像缭绕着雾气一般,时而轻佻得可以,时而深邃得可以。
身上有疤痕又怎么了?他是一个树敌多广的人,连脸都可以毫不犹豫地给人划成那样,更何况胸口?他要被人杀死,也好像并不是如何意外的事吧。
她为什么要想这么多呢,真是的,西门筑就在她身边,要是西门筑知道她现在脑袋里满头满脑的都是别的男人,估计会气得暴揍她一顿不可,好啦好啦不想了,睡觉。
颜溪压下心里的想法,渐渐的,就沉入了梦乡,再一次醒来已是第二天,马车外面清风骀荡,艳阳高照,是难得的好天气,颜溪的心情难得的大好了起来,仿佛得到了重生一般,瞥了一眼西门筑的睡颜,颜溪对着阳光露出了大大的笑脸,好像她又回来了,不再是那一个清冷如霜的江湖女侠客,而是以前那个,爱笑的,充满了朝气的,对什么事情都保有乐观之心的颜溪。
一切,都好像又有了一个美好的开始,颜溪此刻的心里,充满了源源不断的能量,世界上再没有比此时此刻更幸福的时候了。
一个月之后,颜溪和西门筑从东边回到了煌国的府邸里面。
这几年的时间里,煌国皇帝西门炳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这种状况一直从五年前西门筑参加作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当时才有人才敢那么胆大妄为地在西门筑身后捅刀子,因为当时已经有人对煌国的皇帝逼宫,所幸煌国皇帝虽然身在病中,但依然有运筹帷幄的不凡见识,力挽狂澜,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扼杀掉了躁动不安的反叛势力,不过令他遗憾的是,对于他戍守边关的最疼爱的儿子,他是鞭长莫及,能及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不久前,听到儿子回来的消息,他当然是比谁都高兴,不过他现在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甚至都已经缠绵病榻,连站立,都已经成为奢侈了。
事实上西门筑早在两个月前就回来了,他是被护卫们在梁国的边境处找到的,当时的他看起来很落魄很憔悴,目光也很空洞,好像已经完全不记得谁是谁了一样,后来西门筑被接回府邸,找了大夫诊断他的脉搏,大夫也无法对西门筑的病症下什么定义,只说西门筑很可能被摔坏了脑袋,神志不清,失去了某部分的记忆。毕竟,他是从那么高的悬崖上摔下去的,还活着已经算万幸了,一点事也没有,那可能才奇怪着。
可是西门筑睡了一天之后,第二天醒来,就冲着所有人问:“颜溪呢?”
大家没想到他还记得王妃,都很高兴,于是对西门筑说:“王妃去外头找王爷了,听说她现在已经到了东棠国内。”
西门筑就叫李秀带人去找颜溪,***命去了,可没想到李秀前脚刚走,西门筑后脚就跟上了李秀的步伐。
他很渴望见到颜溪,越早越好。
西门筑和颜溪回到王府的时候,很多人都很高兴,且不论府邸里面的人,西门雪沿是西门筑的姐姐,高兴乃是正常,府邸里面的护卫受了西门筑太多的关怀与照顾,兄弟般的他们对西门筑的回归感到由衷的高兴也不是什么大事,要说的是京城里的百姓们,听到颜溪五年寻夫,最终皇天不负苦心人,将自己的丈夫找了回来的事情,都沸腾了起来一般,将这件事情从大街传到了小巷,对于这对郎才女貌,情比金坚,矢志不渝,如胶似漆的情深伉俪,大家都表示了祝福,并将其当做传奇一般在大街小巷传颂。
当然,正统人士对此可谓是不屑一顾的,男儿嘛,要么就应该征战沙场,要么就应该饱读诗书,报效国家,尽管西门筑是王爷,可是他们只是表面上尊敬,心里并没有多佩服的成分在,儒家思想教他们从来都是妻为夫纲,宋明理学也告诉他们存天理灭人欲,儿女之间从来都是私情,虽然他们很清楚西门筑也曾经金戈铁马,但是对于这一些情情爱爱,他们从不认为这有传颂的必要,连锦上添的花亦算不上。
尽管市井小民显得没文化,容易被煽动,但在真性情这一方面,还是要比那些书读得多,满脑子成见的官员腐儒们更实在,更知道把握手头的幸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