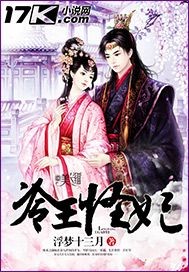“南风啊,你都不问堇程哥要带你去哪里吗?”
“不是告诉我真相,加去救人的吗?”
“那这么久了,为什么不问我真相?”
“我在等堇程哥主动对我说啊,其实我比任何人都想要知道,但是……你心情不好,很不好,所以,我主动问你,你心情可能会更不好,你要是想说了,自然就会跟我说的,虽然我耐心不是很好,但是还是忍得住的。”
她是真的很相信他吧,就算到最后起疑了,可是看到他把茶水喝下去的时候,她心里涌动的,只有浓浓的悔意和懊恼吧,所以,她才会那么的没有戒备,让他轻易地得手。
其实,她是很聪明的,以她平日的性格,她当时完全可以想,是不是他已经事先服了解药,所以什么毒也不怕了呢?
她现在流了很多血,她现在已经晕过去了。
她马上就会死了。
他再也听不到她唤着堇程哥时甜软的声音,再也见不到那单纯无忧的笑脸,再也不可能感受到她一丝一毫的存在,他的南风,那一路跋山涉水而来,在他身边存在了那么多年的温暖晴明的气流,如今,就要彻底地化为水雾,消失不见了。
突然好舍不得啊,一想到那个人,就那么再也不见了,就感觉,心里被硬生生挖去了一大块一样,上穷碧落下黄泉,都不可能再见到她,就那样,永永远远地分别了,再也触及不到。
可是,他已经做好决定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辆富贵堂皇的马车疾驰而来,高头大马眼看就要踩碎躺在地上的虚弱女子。
“南风!”
人来人往的京城大街上,人们只看见一个落魄的高大男子生生地勒住了马脖子,他在寒天的冷风中跳下马来,不顾一切地往地上躺着的女子疾驰而去,那样的眼神,那样焦急如火的眼神,逆着长风而来,聚集到了女子的脸上,砰通一声,一个翻转,她将女子从铁蹄下硬生生救了下来,而他的后背,被马蹄踩过,一口鲜|血如雾花一般,猛的喷了出来。
拥着那样血流如注的身体,他突然抑制不住情感,歇斯底里地狂吼了起来:“你醒醒,南风,醒来啊!”
颜溪再次醒来,见到的,不是席堇程,而是西门筑憔悴的脸孔。
颜溪脸色苍白,可西门筑脸色,比她似乎更白。
“你醒了。”他握着她那只没有受伤的手,轻声地说道。
颜溪只是两眼空空地望着天花板,望了一下,又觉得很累一般,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不要睡。”西门筑皱着眉头道,“大夫说,你醒过来以后,短时间内不能再睡。”
是怕一睡不醒了吧。
颜溪只好听话地睁开了眼睛,却犹自一副困倦的,丝毫提不起精神来的样子。
为了努力不让自己睡着,她在努力跟西门筑找着话题,想到了什么似的,说道:“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很奇怪的梦,我梦到一向谨慎的你被人下了毒,吐了血,还会抽搐,活死人一般躺在床上,我梦见堇程哥对我砍了一刀,我梦见他说蔚若姐姐还没死,我梦见我已经死了,”颜溪说话声音很轻,她也轻轻地皱着眉头,困扰地说道,“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奇怪的梦呢?”
“颜溪……”西门筑心里百味杂陈,手臂上的疼痛应该会折磨得她痛不欲生,可是她还是要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这是一场梦,她当时,到底是经历了多痛苦的境况呢?
他吻了吻她冰凉的手背,他的唇很温热,却似乎没给她带来丝毫温暖。
“你不要这么伤心,席堇程他,已经断了一只手臂。”
颜溪轻轻转动虚弱的眸子:“你做的?”
西门筑摇摇头:“他自己断的。”
“当时,我赶到京城的时候,四处派人寻找,找到了你和他,他在一处医馆里,我当时质问他是谁把你弄成这样的,他说是他,紧接着,他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砍了一只手臂下来,说是赔你的肩上之伤,然后,他叫我告诉你,他对不起你。”
他不想在病弱的她面前说死这个不吉利的字眼,所以他没有告诉她,席堇程还说,如果她死了,他一定会把自己的头颅砍下来祭她。
颜溪眼波动了动。
“我们回去吧,西门筑,好不好?”
“可是你肩膀上的伤太重,根本禁不得颠簸。”
“没事的,我命很硬的,我忍受得住,回去,好不好?”
他握住她的手:“虽然这是东棠的皇宫,可是我会保护好你的,你不用怕。”
颜溪摇摇头:“我们回去找许窦吧,你中了毒,不要拖了,我们回去,好吗?”
她为了证明自己的没事,强撑着坐了起来,还对他笑笑,可下一刻,就被他紧张地拉进了怀里。
“不要乱动了。”
“回去。”
“待在这里。”
“回去。”颜溪看着西门筑,说道,“我本来就说过,让你先回去,可是你又放心不下我,现在不仅没让你好好休养,还让你拖着疲惫之躯千里迢迢赶到这里,当我刚才醒来看到你的脸时,第一个感受是像上了天堂,可是马上就知道,自己对不起你了,你不该出现在我身边的。”
“如果我的病养好了,你的病久拖不愈了,我会很想把自己吊起来打的。”颜溪闷闷地说道。
其实,他比任何人,都不想她待在这个地方。
可是她的身体实在太虚弱了,总不能因为想保护她不受到心灵的伤害,就不顾她的身体了吧。
不行,现在绝对不能回去。必须等她身体养好再说。
而至于他的病情,其实——他根本——
没有病。
没有人能够在他眼皮子底下下毒。
他当时是自己服了毒药,但他有解药,只是当时,他没有想到那毒药物性那么强烈,他没有一点力气,后来是真的晕倒了,他看到颜溪跟席堇程走,却只能发出细弱蚊蚋的声音,之后,就是整天整夜的晕厥,待到他醒来的时候,他才叫人找颜溪的下落,可那时的颜溪,已经受过很严重的刀伤了。
“颜溪。”
“嗯?”
“我之所以来东棠皇宫,一方面是因为既然来东棠京城了,以国家之名来访问一下东棠国君也是必须的,另一方面是,我是在东棠这里中的毒,国君有义务派遣最好的大夫为我治病,若是我一个不好病死在这里,东棠国和煌国会开战的,现在关系好不容易缓和点,谁想打仗?”
他继续七里八里地游说,就这样半哄半骗地把关心他到不行的小妻子安抚好了。
龙涎香的气味在室内袅袅飘散,一黑一白,两个身影,对坐饮茶。
西门筑雪白的貂裘松松垮垮地披在外面,里面是松绿色的映有银色底纹竹节的锦缎,腰间的一尺镶边腰带上垂着一块通透的和氏璧,唇红齿白,细长的凤眼如三月桃花,轻佻地半阖着,闲闲饮茶的姿态,优雅自若,颇似画中人。
皇甫炎一身黑裘,此时此刻的他并没有看见蔚若时的那样温柔耐心,但也并不像遇到寻常的来客一般就算微笑也有几分寒气,他此刻看西门筑的感觉,怎么说呢,有点像看一个老朋友,但又充满戒备。
“是你杀了席堇程?”西门筑并没有那样好的耐心,事实上他也懒得编造一个玲珑圆通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意见,皇甫炎又不是他谁,他干嘛要顾及不唐突了别人?
皇甫炎果然是一愣,不过也很快缓下神色来,说道:“我什么也没做。”
“是啊,你什么都没做,只是你的下人不小心到了宫外,不小心经过了席堇程的身边,然后不小心地在席堇程耳边交谈,说颜溪被病痛折磨多达数日,惨叫声三日不绝,终究还是撒手而去,最后,不小心地看到了席堇程当街自杀的样子。”西门筑淡淡说来,端起喝茶专用的精致盖碗,轻轻地推开了茶盖。
和聪明人说话不亮瞎灯,皇甫炎并无否认,只是沉声说道:“你想如何?”
“我不想怎么样,还是跟以前说的那样,我给你你想要的,你给我我想要的,记住了,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蔚若见到颜溪。”
皇甫炎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只是皱着眉头问道:“素闻煌国五王爷放纵不羁,是煌国皇上的掌中之宝,一生锦衣玉食,我曾经让苏昀差点要了你的命,你知道一切是我做的,却并没有对我行报复之事,反而还一派悠然地和我私下谈条件,到底是为了什么?”
西门筑一愣,笑道:“当然是为了江山社稷啊,为了东棠和煌国能够两国安好,永结秦晋,就算我吃一点亏,忍耐一下,又有什么呢?我们煌国人就是有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上至皇子下至贩夫走卒都深刻地铭记不忘国忧的理念,怎么样,是不是很伟大?”
皇甫炎表情严肃地看着西门筑,年轻的掌权者眼中渗透出一股敬慕:“的确是很伟大。”
西门筑“噗”的一声将茶水喷了出来,哈哈大笑,形象全无:“这种话你也信?”
皇甫炎抬起眸子,只是淡淡地看了西门筑一眼,像是福至心灵一般,笑了笑,没有说话,没有任何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