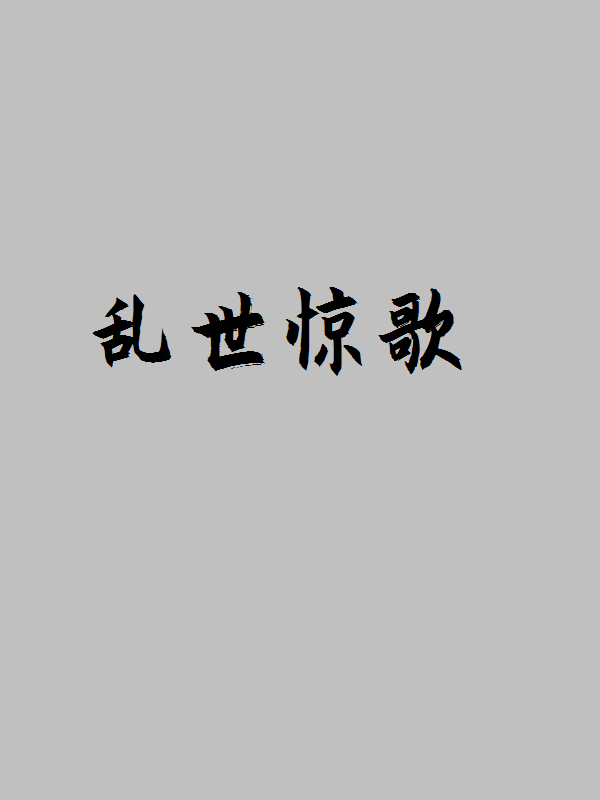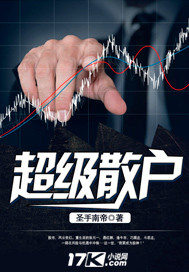而另一边,在穆玦被穆霍天留下之后,穆瑾就有所察觉不对了,估计穆霍天有心让穆玦做这大城主吧!
穆瑾这个人,平时看着粗枝大叶,但是心机却深的很。和穆凌那种看着高深莫测,实则头脑简单的家伙相比实在是高的不是一个档次。
故而穆瑾察觉到的,穆凌却是毫无戒心。出了大城主府之后,穆瑾怕被人跟着只好直接回了自己府上。收拾妥当之后才悄悄去了穆凌府上,打着拜访的口号去想办法对付穆玦。
虽然穆凌不聪明,但是多少还是有些脑子的。穆瑾那么提醒了几句之后,他心里也起了疑心,随后看向自己的二弟:“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做?”
“当即我们所想的不过是我们的揣测,”穆瑾眯了眯眸子,上次受的伤太重,他现在多少还有点儿后遗症,再加上也不知道喻小桥已经不在三少主府上了,多少对穆玦还有点儿忌惮,要不就直接上去杀了穆玦了。
“当务之急我们应该是搞清楚父亲的想法是不是已经变了!”那次穆霍天和喻小桥说话的时候,虽然自己听到了。但是他怎么能肯定穆霍天不会改变想法呢?
穆瑾这话说完以后,穆凌沉思了一会儿,随后抬头道:“这有何难?我自有办法!”
“既然如此,那边好!还希望大哥能尽快处理这件事!”穆瑾虽然这样说,但是对于穆凌的办事效率还是有所怀疑,不禁在心里下了一个决定。
而这边穆玦回了少主府之后,刚进书房便看到坐在书房上坐一袭白衣的穆铭。
穆玦看着他皱了皱眉:“做什么?穆霍天暂时还死不了!”
“阿玦,”穆铭张了张嘴,“你可是还恨着我?”
“恨不恨又能如何?”穆玦淡漠的说完目光落在书桌上,“穆霍天已经答应让我做金城的的下一任城主了,到时候……你想做什么也与我无关了?”
“你想与我断绝关系?”穆铭一惊,“阿玦,为了那个女人真的值得吗?别忘了,现在白仪才是你的妻子,而且她怀了你的孩子,你就忍心……”
“呵呵!”穆玦听着他的话不禁露出一抹讥讽笑,“从小到大,我一直以为哥哥是最疼我的人,我一直一直把你当最亲的人,可是呢?你竟然可以坦然的跟白仪勾结该死我的孩子,还让桥桥彻底离开我,还帮着白仪给我下药……”
“哥,”穆玦咬了咬牙,“你不觉得你很虚伪吗?”
“你……”听到穆玦的控诉,穆铭的脸色越来越差,“你都知道了?”
“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道理,应该是哥哥交给我的吧!”穆玦说完转身就要走,若不是拿日他命人偷偷的去查那催情香的出处。恐怕他现在都被他那位好哥哥欺瞒着。
穆玦自小神中媚毒,媚毒顾名思义和媚药没有区别。自然他对身体的自制能力要比一般的男人强,对于强.暴喻小桥那夜,那也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是自己想要碰那个女人。
自然,对于白仪下的药他自然是不屑一顾的。只是,炉子里的香料却霸道的很,据他所知除了自己的这位好哥哥,没人可以做到。
随后他又命人查了白仪的侍女,幸亏白仪的侍女都是自己都上的人。知道自己的手段,仅仅是一把剑就吓得全招了,包括白仪让喻小桥喝下滑胎药的事。
他倒是没想到,自己最亲近的人,竟然可以狠心害自己,以及自己的孩子。
坐在椅子上的穆铭只觉得手抖的厉害。低垂着头,眼神里满是迷茫与不安,上次被喻戈捅了那么多刀,虽然没死。但是失血太多,多少留了后遗症。
为了那个女人,真的值吗?穆铭还是欺骗着自己,说这是为了阿玦好才做的。其实当初给了白仪催情香,一半的原因是因为穆铭想要报复喻戈。
因为喻小桥是喻戈的妹妹,他也知道喻小桥对于阿玦不是完全无情的。所以他以为只要让喻小桥不好受了,喻戈也会难受。
只是他却忘了,自己的弟弟穆玦对喻小桥的情谊也是那么固执那么深。想到这里,穆铭不禁眼中闪过一抹狠厉,都是喻戈,都是喻小桥。
这一切都是这两个人害的,为了阿玦,他一定不会放过这两个人。
至于穆玦,出了书房之后一时还真的不该去哪里去了。他和白仪成亲之后,虽然白仪依旧住无香居,但是对于主院那个女人也不放过。
仗着自己的公主的身份,也实在是没人敢拦,连主院都能随便出入。
这些想着就让他觉得头疼,为什么,偏偏是那个女人和他成亲了,明明一切都可以把握在自己手里的。
想到这里,穆玦不禁看了看自己的双手,终究是自己还不够聪明,被人耍的团团转。失去了亲人,失去了爱人,也失去了孩子。
穆玦早已经死了吧!失去喻小桥那一刻,他就心死了,活着也不过是行尸走肉。
等到他再回过神时,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华客居,曾经喻小桥住的院子。穆玦苦笑了一声,推开门走了进去,却是满眼的洁白。
母亲生前一直住的是无香居,而华客居是自己的院子,只是他中毒之后,母亲便把他接到了无香居住了。
如今想想,似乎把喻小桥安排在华客居是天意啊!虽然他当时没有过什么想法,但是喻小桥却如同这院子,成为自己最重要的东西了。
进了屋子之后,华客居已经落满了灰尘,因为常年不住人,故而没人打扫。
穆玦跑了一圈四周,看了看桌子上腐烂的水果心里更加苦涩。女人就像这些水果,要是不好好珍惜,就会腐烂。
从怀里摸出那块古老的木牌后,穆玦的眸子闪了闪,想哭却不能!他不是女人,他还不能哭,所以他只能任由着心,一直一直的刺痛下去。
金城夜色降临之时,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孩子都陆续的回了自己的家。
而此刻,一条昏暗的小巷里,一个四五十岁的老者看着眼前的黑衣人,又瞄了眼架在自己脖子上的刀:“好汉,这是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