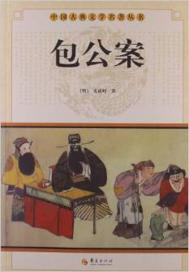远山如黛,薄雾慵起,圆盘般落日,一点一点倾斜。
女孩大概四五岁年纪,明眸善睐,肌肤胜雪,垂两个小小髫,左边簪一只栀子花。
她站在门口,脚下一条小路,曲曲折折,深入小山。
群山嫩绿,山脚下,只几里巨柳做深碧色,衬得花忽然姹紫嫣红了。
“芽芽。”一妇人唤道,“进屋子吧?天很晚了。”
此妇人极年轻,拖长长乌丝,挽一块天蓝色绢帕,布衣荆钗,眉眼婉约。
“我不想回家。”女孩说,“我等哥哥回来。他说带泥模儿来。”
“哥哥不会回来的,芽芽。”女人说,“他跟胡三爹当学徒,要五年才可以回来。”
“五年要多长,妈妈?”女孩问,她弯下腰,折一只小花,这花朵烂紫,凝露珠,娇柔的花粉落在女孩的手指,手指越发细嫩,近乎透明了。
“春天要来五次。”妇人说,“花儿要开五次,柳树要绿五次啊。”她仰起脸,大而明艳的眼睛满是泪水,“你的哥哥还来的及送芽芽出门子吧?”
女孩的注意力被花粉吸引,没有再追问。
天边,太白金星升了上来,再远处,是一弯月牙儿,苍穹竟然碧青,白云不再流动,慢慢被天风撕成了翠儿。
妇人携着女孩的手,带她进屋,女孩从母亲手臂处回望,月与星升得高了。
夜已经深了,女孩趴在窗台边,她看着月牙儿,这月牙默默地在天空移动,像蜗牛一样慢。
星星又大又亮,一堆堆,一簇簇,银河越发明亮,银河水嗡嗡得流淌,震落许多小星星。
小院落,干净又整齐,院里种许多花,花儿在风中摇曳,篱笆的院墙,吊着去年的枯藤,院里的春韭嫩嫩香香,大朵的婆婆嘴开了遍地。
“芽芽儿。”有人喊她,她抬头看时,一张小脸露在竹篱外,旺旺在喊她。
旺旺轻手轻脚地溜过来,把一大把野花递给她。
这花刚刚脱离花枝,新鲜甜蜜,芽芽高兴起来。
“扬扬哥走了吗?”
“嗯。”芽芽说,“哥哥要走五年,他答应带泥模儿给我,他说,扬州的泥塑最有名。”
“我知道。”旺旺说,“可是……”
他沉吟着,吞吞吐吐。
“什么事?旺旺哥?”
“我听人家说,胡三爹不是好人。”旺旺说,“他专门拐卖小孩子,把他们养起来,然后卖掉。”
“卖掉?”
“是啊!他把小孩子拐去后,养大了,才会卖掉!”
“他是个拍花子的?”
“是啊。”旺旺担忧地说,“胡三爹拐小孩子,大家都知道。扬扬哥不会是被他拐卖的么?”
芽芽愣住,手里的花朵落下来,凌乱的花瓣铺了一地。
月光水银般溅落,芽芽蹲下去,慢慢捡起花儿。
“这是在后山摘得吗?”
“是。”旺旺说,“爸爸坟头有好多这种花。她们开的整好。”
“你又去看伯伯了?”芽芽说,花儿娇嫩,禁不得这样子散落,她怜惜地收拢起来,花瓣轻折,淡墨的痕迹污了这嫩色,“白白又打你了吗?”
“他敢!”旺旺说,伸出手臂,看着肌肉,“吓死他再打我们!你看看,我已经很有劲儿了。”
“不信,你来摸摸看。”旺旺说,“我是大孩子了,我可以保护妈妈,照顾妹妹了!”
芽芽开心地看着,星光下,这男孩带着奇异地自信,明亮的眼睛快乐地眨着。
小院落的东边,是三间作坊,门前摆着纸扎儿,橘红色窗口影着长长的身姿,妇人在做纸扎。
窗口下,立着纸扎童子与童女。这对纸人默默地站着,长衣大袖,粉面红唇,眼若点漆,春天的风毫奢得吹过来,他们摇摇地摆动起来,跟这对小儿女打招呼。
“嗨!”旺旺说,“你们好,听说听到。”
“听说哥哥,听到妹妹。”芽芽嗔到,“他们是弟弟妹妹呢!”
“嗨呀!芽芽。”旺旺说,“他们是纸扎,不是真孩子!大婶每天扎好多纸人,都是你的弟弟妹妹吗?”
芽芽低下头,手中花朵更萎缩了。
“后山有的是,这叫打碗碗花,不要再可惜了。”旺旺说,“我明天带你去摘花儿,映山红都开了,比这个花好看,我带镰刀去,砍一大抱送给你?”
月儿越发柔和,天空晴朗,蓝丝绒垫子一样,钻石的珍宝镶嵌遍地,春风的甜蜜漫无边际地荡漾起来。
旺旺伸开长腿,跨过篱笆墙,进入夜色,他回家了。
芽芽想走到妇人的作房,她逡巡在小窗外,思忖良久,不敢进入。
纸扎的童子与童女看着她,眼睛竟然眨动起来,夜色苍白,他们仿佛有了生命,灿烂地复活了。
芽芽呆呆看着他们,他们走过来,长大的衣服沙沙响着,拖拖拉拉地在地面移动,这对纸孩子围住了芽芽。
“你们活了么?”
“什么活了么?”
“像我一样,是个真的孩子么?”芽芽定定地看着他们,“你们跟旺旺哥一样了吗?”
“真是傻孩子!”这对纸人对视,都眨眨眼睛,复又笑起来,声音刷啦刷啦地响,咯吱咯吱地颤动,让芽芽觉得牙酸,“我们是纸人,纸扎的,不过……”
他们停下来,又互相看看,再扭过头看着小小得作坊,风吹过来,他们仿佛凌空飞走了。
“芽芽的妈妈跟别的工匠不一样。”童子说,“她用心血扎我们纸人。”
“纸人终究是纸人。”童女说,“我们早晚会成了灰烬,她多余呕这心血。”
“我们不喜欢这心血!”童子道,“我们要这滴心头血干什么?我们又没有肉与骨!这样血,滴进我们心口,白白浪费了。”
芽芽听不懂,她知道自己母亲手巧,她每天都做纸扎,她待在作坊里,不许任何人进去。
“她倒不如做些纸花来!”童子说,“每朵纸花滴一滴鲜血,纸花会变成鲜花,可以卖好价钱,可比扎纸人上算,她为什么执着做纸扎?真是蠢女人。”
“她不会蠢太久了。”童女说,“她做了十几年纸扎,扎了万千个纸人,她的血要滴干净了。”
“我真的不明白。”他们又抱怨到,“她为什么要扎纸人?为什么把鲜血滴进纸人里?做这无聊的事,白白……”
芽芽看着小作坊,妇人低头的剪影,拉长在白纸上。
她温婉地垂着头,侧脸线条流畅,睫毛挺翘,流苏地纸条在她手里起起落落。
“一万三千六百五十个。”童子说,“她为了什么?可怜的小芽芽!真是可怜。”
作坊门打开,妇人抱一对纸人出来,芽芽伸开双臂,准备扑进妇人怀里。
月色如银,夜色阑珊,暮春的空气,温暖安谧,风慢悠悠地吹着,花香流过来,无处不在。
芽芽觉得困倦,她想扑进母亲怀里,她觉得要睡了。
她变得蝴蝶一样轻盈,飘飘荡荡地飞起,晚风仿佛把她吹了起来,她落进一个冰冷的怀抱。
一滴血落到她的脸上,知啦一声钻进她的皮肤。
妇人的脸色苍白,她一手托着女儿,一手把纸扎垒在墙角,那对纸人低垂着头,装的若无其事。
妇人看着它们,目光森森,带着万千恶毒,这目光如刃,仿佛刨开这对纸扎的腔子,破开他们空虚的胸膛。
夜凌乱,花香肆意,春天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