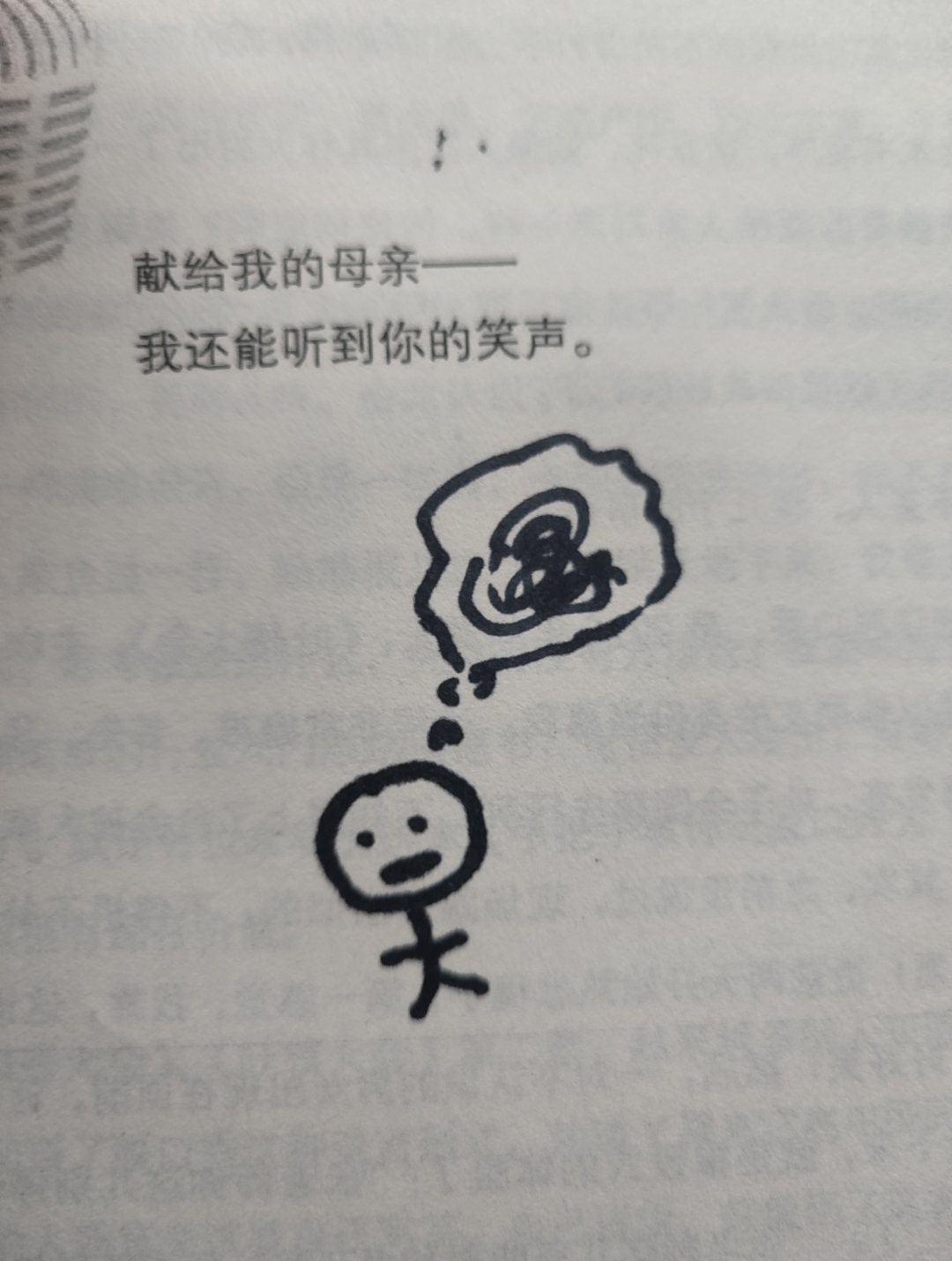60年代初,在我的少儿时期,常常听村里的老人讲一些鬼呀神呀的故事,还有什么狐狸精、白衣红发的女鬼等等……听起来怪吓人的,那些胆子小的大人或者是小孩、一听这些都吓跑了,我的年龄虽小,但却爱听。
那时候的农村人穷苦,农闲时节大多数人都爱聚拢在一块靠闲聊乱语打发时间。在大人有声有色的胡吹乱谝中,我记取的最深印象是,那些鬼神们想要什么就能来什么,他们一点都不会饿肚子。
我家的娃娃多,劳力少,一年到头极度地缺粮!全家仅靠我父亲的一点工资接济维持,年中一半的时间都是饥不裹腹饿着肚子在饥饿中度过。我父亲挣的钱几乎全部用来买粮了。由此,我的父亲非常愤怒,非常地恼火,他每一次要去买粮或者买粮回来,他都会对他的子女们或恶语相向或拳脚并用棍棒相加!并且还大骂他的儿女们是——吃人贼,贼怂等等戾气歹毒的恶语。
每一次挨打过后,我都会跑到野外,在没有人的地方情不自禁地想念和羡幕那些个“鬼神们”,我要是能变成鬼就好了,让家里年年都不缺粮。
听说晚上的天色越黑就越能碰见鬼。在好几个天黑如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我还真的跑到野地里、坟堆里找过鬼,可惜!一次也没有撞见过。
烈日当空,炎炎夏日里的麦收时节。农村各户都忙碌着抢收自家的麦子。这一天,我家也收割了。等把一捆捆麦子用架子车拉到生产队的麦场里,然后堆码整齐后,天已经麻麻黑了。各家都把自家的麦子堆成垛后,都会留下人夜里来看护,都生怕第二天来晒麦时少了几捆。
这一夜,我家的麦垛留下我看护,尽管那时的我还不到十岁。
白天割麦、拉麦、堆麦垛劳累了一天,天一黑,我就趴在麦垛上睡着了。
许是冥冥之约,不觉间,我自已醒来并起身,离开了麦场无知无觉地朝着南面走去。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四野里一片黑暗,听不到一点声音。我摸着黑向前走啊走啊。突然,前方出现了亮光,我向着光源处跑去。跑到了发光的地方,才发现那发光的地方是从一棵大柏树的树腰处发出来的。再一细看,原来是树腰处聚了一堆“莹火虫”,萤光闪烁,十分亮眼。柏树下的四周还有零零散散的萤火虫飞来飞去,我跟着萤光这里一跑,哪里一看,跑着看着,这才看清楚这里是一个墓冢。那棵粗大的柏树几乎是从这个墓冢里长出来的。我实在累了困了疲惫不堪,就坐下来靠着柏树睡着了。
这棵粗大的柏树,在树身的下面有一段是半空半实、有一个人们常说的树洞。树洞里有一支白狐,它的身子虽然在树洞里,然而树外面的一切它看的清清楚楚真真切切。树外面的小孩此刻就与它隔着一层树皮,它俩几乎是身子挨着身子。
这孩子紧靠着它渐渐地进入了熟睡。这是它祈祷和期待已久的事了,它目不转睛看着小孩,心里在说:“怀胎八年有余,你的气数已经不足一个半的时辰了,今夜“子时”一过,母亲就给你“还魂送魄”,明天午后时分我就要分娩,让你脱胎换骨重新来世。时辰不能出错,不然你就没命了”!它深情地注视着他。
时间倒回“八年零十个月”。这天夜里,有一只狐仙正路过一个村庄,它是一只修炼了几世的狐仙,与人们常见的狐狸有着天壤之别。此刻,她正乘着祥云途径此地。
当经过身下的一间房屋时,听到屋子里有幼儿的哭叫声,她于是停下来,透过屋顶往里看。屋子里有一男一女两个大人,那女的正在给抱在怀里的一个幼儿喂药,幼儿拒绝吃药又哭又闹。哭闹中的幼儿突然弄翻了放在一旁的药碗。只见那男的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一把从女人怀里抓过幼儿远远的摔出去,幼儿“咚”地一声碰在了一面墙壁上。幼儿惨叫了一声,随之从幼儿的体内立时飘出了一缕魂魄,这魂魄不偏不倚、径直向着她飘来。见状,白狐急忙吸气,一口将将要“破散”的幼儿的魂魄吞下了肚。她又面向屋子里的幼儿隔空念了法咒,再施了些法术,给他安魂定魄稳定了幼儿的气息,不再让乘下的魂魄从孩子的体内跑出来,暂缓住了幼儿的性命。
她的这么一“吞”,就给自己带来了麻烦。因为,从这一刻起,这个幼儿的生死将由她来承托。一个人的魂魄出了壳人就距离死之不远了,那个幼儿之所以还没有断气,那是因她接住幼儿的性命之“魂魄”。
幼儿的魂魄在她的肚子里有了着落,不会四处飘散成为“孤魂野鬼,魂魄反而还能得到发育健康成长。等到足月后母亲分娩,他就能重获新生。
因果不能改,智慧不可赐,真法不可说,无缘不能渡。道法无边,难渡无缘之人。
然而白狐自己呢?她不是没有顾虑,在她意识里迅速闪问过自己,“这到底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有天意?近万年的修炼会不会毁于一念”的念头。但她更熟知救人性命济世渡人得道升仙的道理。她先救下幼儿,然后微闭着双目定下神来,通过幼儿的“五相”来推算孩子的天数、气数、定数等延续性命的轮回法则。
“天数在我、定数在十,气数已失之八九”。她仰望天空,观察天星,诚然是得天时,然后掐指推算,修胎需八年十个月。等到胎气满月我的仙血一落地,那么这孩子就会魂魄还原、血随母性、脱胎换骨、超凡脱俗半人半仙了。她“叹”了一声若有所思,默念道:“安危相易,祸福相生。万世修行、道法自然,今遇劫渡、道在我心,若不赴尘、必遭天谴”。她又朝着九天之域望去,在心里默默说到:“莫非是妈妈送子,特遣我过来的”?
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触摸着我的脸,还能听到有一种奇怪的声音仿佛在唤醒我,我睡眼醒忪,朦胧中看见一个像似鸡毛掸子样的东西,它一下一下在抚摩着我的脸。是什么东西抚弄我?这是什么啊?我坐起身来。“啊”,猛地被眼前的东西吓了一跳。在距我不到半步远的地方,站着一个雪白色、模样似狗、不知其名的动物,是它用尾巴抚我的脸。
村子里的狗我天天见,长这样子的我还头一次见到。我看着那个粗尾巴,想起老人们常说的“狐狸的尾巴粗,像鸡毛掸子”,再看它的表情对我很友好,很温和。“啊,它是狐狸”。我又惊又喜,又倍感亲切,急忙站起身问它:“你是狐狸吗?真的是你吗?”
它对我点了点头,样子就是说:“我就是狐狸。”
农村人在农忙时节下地早。我看见狐狸开始不停地在我面前转圈,它的两只后腿还不停地蹬着地,样子显得焦急想离开此地。还没等我多想,它就朝一个方问跑了起来。
我没有犹豫,它跑,我也跟着它跑,我紧跟其后不想再离开它了。
我俩一路小跑,来到一个大深沟的一处徒峭的崖顶上停住。狐狸朝崖下面看了看,转过头又看了一眼我,然后它身子一纵、飞身跳下崖去。我只是愣了一下,也不知从那里来的胆子,没有多想也跟着它一跃而下。
我睁着眼晴躺在地上,觉得天旋地转,脑袋嗡嗡作响,身上隐隐作痛。我活动了一下身子,身体无大碍还能活动,于是坐起来环顾四周,黑咕噜噜地什么也看不见。我又想起狐狸,它在哪儿?“狐狸你在哪,你在哪里?”我喊了两声,没有听到动静。我想可能是走丢了!
但是有一种感觉让我坚信我们俩都在这里,彼此距离也不远。“它是不是受伤了”?我在心里发问。不管有多难,我一定要找到它,一定要找到它,我下定了决心。
(那只狐狸就跳进这里。此时,它就在他的前方不远处的一个偏僻的地方)。
狐狸一到这偏僻处,就急忙伏下身子,它一个闪身就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女人。此刻,她的五内翻滚,腹部剧烈的疼痛,痛苦让她不住地颤抖,她在不停地呼唤着我:“别回头,孩子,快往前爬,你快出去啊”。在她下身,不住地淌出鲜血,她在这里分娩。
这是哪里呀?我真的是身体到了黑漆漆的地方没有了方向和目标。我瞪大眼睛在黑暗中摸索着,摸索了半天什么也没有摸着,倒是被什么东西绊了几个跟头。不能凭瞎摸,千万不能着急,我没有心灰意冷,努力地让自己平静下来,看能不能听到或者感觉到什么。
我好像是听到了声音,又感觉是它的声音,那像是痛苦的声音,这传过来声音仿佛一泉眼泪,又似一腔血水淹没了我的心。
我顺着有声音的方向爬行寻找着,向前爬一会、停下来听一会,生怕出了闪失浪费了时间。
我顾不了爬行中的磕磕碰碰,在急切的寻找中我感觉不到疼痛,但是我俞发清晰了声音位置,就在前方。
我一刻没有停歇,拼尽我浑身的力气向前爬寻找它。
“它一定是受伤了“,在爬行中我仍然想着它呀。
是?是?我似乎意识模糊说不清楚,很难用言语描述我此时此刻自己的感觉,只感到心疼,一边爬行一边胡思乱想。我越发感觉到和它之间存在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已经不能割舍、我已无法抗拒的关联,而且还越来越强烈。
突然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啪啪两响,我拍了拍自己的耳朵,听觉好着呢没有问题呀,怎么会听不到了呢?我心里一着急就站了起来。“天哪,”前面有光亮。我急切地开始狂奔,尽管脚下面坑坑洼洼路不平,我忘乎了所以,疯了似的朝着梦想和希望飞奔而去。
我跑到了亮处,这里的光线确实好。我目光扫视了一圈,这才看清楚并且意识到这地方是个洞口,而且还是一个口小肚子大的石洞。洞是半圆形的,地面凹凸不平,到处是乱石块和石渣。地的中间高两边低,两侧还有不小的流水,两股流水在洞的出口处汇成一股流向洞外。
我又瞧自己,是浑身的泥土,头上、胸腹部、胳膊腿上多处伤痕累累,有的地方血肉模糊,小腿上有一处都皮开肉绽了。
我又开始焦虑起来,心里极度地惴惴不安,因为在这里我还没有看见它。
它去哪里啦?它在哪里?我又疯也似地朝着洞内大声呼喊:“狐狸,你在哪里?你看呐,我在这里等你呀”。
我竭斯底里声嘶力竭到了忘我的状态,我又想再回到洞里去,找不到它我就不出洞了。脚下突然一滑一个趔趄,我栽到水流里。
我被水流冲出了洞口就飞流直下掉落下去。
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又是那样的匪夷所思。就在我将要堕地,决定生死的瞬间,从横钭里飞身过来一个人,他一把在空中把我接住。
搭救我的人是男性。我们不曾谋面素不相识。他面目清秀看样子三十大概,穿一身军人绿,雄发英姿干练稳健,长得像电影演员王心刚。
从这里看去,那洞口距离地面直上直下大约三百余米。我想如果没有他我就完了。
一切仿佛是事先安排好了的,他抱着我来到一平缓处把我放下,从他早先放在这里的一个包里拿出瓶子、纱布等不少东西。
他叫我躺好不要乱动,自己拿着纱布等去旁边的水池里湿水,回来后给我清除、擦拭身上的泥污。
“你小子的造化可真大啊”,他说话的语气很温和。
“谢谢叔叔救我”。我在感谢他。
他话不多说,动作有条不紊地做着清创、消毒消炎、做伤口缝合等医生该做的事,很专业的样子。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心里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我的眼里流着泪,男儿有泪不轻弹,平时再苦再委屈我从不掉泪,尽管我还小。失望、失落、我的内心很沮丧。
“你很坚强,很优秀”,叔叔给我竖起大拇指夸我。
我知道他之所以这么夸我,是因为他在处理伤口过程中没有使用麻药和止疼药,但是我一声没吭。但并非我没有疼痛感。
我很礼貌地给了叔叔一个微笑,没有吱声。
此刻,我确实笑不出来。躺在那里,我眼泪盈盈表情发呆,像一根木头似的,任由叔叔给我缠了一圈又一圈的纱布。
我憋着实在是难受,“你在哪里呀”我没能沉住气忍不住的喊了一声!
叔叔无动声色,继续做他的事情,他把拿出来的东西装回包里,又从包的旁边拿起一个类似背袋一样的套袋。
他在动我的腿,之后又在我的后背和腰部做着绑扎的动作。做完了这些,他过去背起地上的包,然后非常小心地扶起我像背背篓似地把我背在他的背上。这一切,他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吗?我心里自问。
我静静的爬在叔叔的背上,脸很自然地贴着他。
当我们要离开这里的时候,叔叔给我指着那个洞口说:“孩子,你一定不能忘了今天的日子,不要忘记了那个洞”。
终身难忘,我动情的点着头说:“我忘不了,不会忘记的叔叔”。
叔叔动情地又说:“今天是你胎胎换骨,重新来世的日子,那个洞,是你的“狐狸”妈妈生你、你重获新生的地方啊!孩子”。他的话音一落就转过身去,他迈开步子健步如飞,我们离开了这里。
“狐狸生我、我脱胎换骨重新来世,这是怎么一回事呀?”我一脸懵逼莫名所以爬在叔叔的背上,反反复复地琢磨他的意思?
有大约二十多分钟,叔叔背着我走进了一个院子。我俩进来的时候,院子的大门是开着的,进门后叔叔就顺手把门关上了。
进了院门往里走,正面一左一右有两间瓦房,叔叔背着我进了左边的房子。
房子里紧连着一面墙砌了一个大炕,炕上的被褥都铺叠的整齐干净,炕的一角还有一张吃饭的桌子。
叔叔放下我,让我先静静地躺着不敢乱动。他说都饿了弄些饭去。再放下他身上的其它东西后,就出了房子。
我躺在炕上,虽说身子不敢动,但是两个眼睛却没有闲着。我瞧见靠近炕头的一边还挂着一个门帘,在门帘的后面还有个套间。正看着,我听见有人在说话,是男人女人的声音。再仔细听,是叔叔和女人在谈什么,这时候,我刚才悲恸的情绪被这里的情景冲淡了一些,不再那么的沮丧了。
都像是刚刚做的一样,才不一会儿,叔叔就弄了一桌子的饭菜,并且还有酒。
叔叔喂了我一碗鸡汤,又给我喂了一碗饭我就吃饱了。他坐在我的身旁开始自己吃,他吃着饭菜,一边自斟自饮。几杯酒下肚后他说给我讲个故事。
他是从“前面的”八年零十个月的那个夜里给我讲起的。他对我说我妈妈是修身了近万年的狐仙,他是我狐狸妈妈的亲弟弟,是我的亲舅舅。
我木然地惊呆了,发着愣看着他,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我竟然全然不知,在我的身上居然还会有这么多的故事。
我想不起来我自己的事情,此时能想到的全是狐狸,整个脑袋里装的全是狐狸。我自责起自己的年少无知,怎么对妈妈的关爱一无所知,我颇为惭愧的对舅舅说:“请你原凉舅舅,我太没有记性太无知了,你所说的我慢慢会想起来。”从未听说过的故事,我能想起来什么呀,眼下我也只能这样应付。
我的话刚说完,房子外面走进来一位长得很美丽的女人。舅舅看见她走进来,连忙下了炕抢上一步扶着她。“看她才二十多岁的样子,舅舅为什么会扶着她呢”?我在心里发问,似有不解。
她接我的话说:“怎么能怪你呢,你不能说自己无知,肉身凡胎怎么能知晓神通之事呢,再说了,你还这么小”。她的表情和霭,说话的语气平缓,一字一句,不紧不慢,言语之中流露出十分的庄重和文雅。
“就是,就是,姐姐你说的是”,还是舅舅的反应快,他替我打了个圆场。
她是舅舅的姐姐,我在想我该怎么称呼她呢,一时楞着说不出话来。
见我还没有言语,舅舅又说:“姐姐,他和你是头一次见面,是怯生吧?”
我说话了:“您是姑姑吗,姑姑好?”
她微愣了一下,面露难色,略带着一脸的苦笑,没有说什么。只是盯着我看,同时,又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到我躺着的炕边。舅舅一直扶着她,她坐到我的身旁。
屋子三个人,此刻,谁也不说话。她一边看着我,一边用手抚摸着我的额头、我的脸颊、还有我裹着纱布的每个部位,她还是没说话,依然只是看着我。
其实,从她进了房子,当我第一眼看到她时,我的心里也不知道为什么,说是倍感亲切、还是似曾相识等等都没有言过其实,反正看到她我很激动吧,那感觉很复杂,一时说不明白。
过了一会,站在她旁边的舅舅说:“姐姐,我在炕那边给你拿个被子,你靠在被子上和他说话能舒服些,你的身子虚弱、别太累着了”。舅舅说完就上了炕,抱过来一个被子,在紧挨着我头的炕头把被子放好,然后下炕扶着她上炕让她靠好被子后舅舅才下了炕。
我的眼晴也移到了她现在的位置并且注视着她。同样,她也侧着头在着我,我俩的目光相遇。我不知道说啥好,只问了一句:“姑姑你是病了吗?”
她对我微笑着点了点头,只是看着我仍然没有说话。
我:“姑姑你吃药了吗,我看你脸上的气色不太好,脸色苍白。”
“小小年纪,你还懂气色。”她噗嗤一声笑了,笑容很甜美。“我让你舅舅给咱俩用药膳调理调理就好了,你不用担心”。
“好的”,我点了点头。
但是,看着我和她都躺在舒服的炕上,还有舅舅的服伺,我又想起了狐狸,尽管我还有疑心,不太相信舅舅说的“狐狸生养”我的话,但我的脑子里和我的心房里全是那个狐狸的影子,而且还会出现它正在受苦的样子。"它在哪里呀?它还好吗?”我一下子又颓废沮丧了起来,两行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我的这些反应都被姑姑和舅舅他们俩看到了,他俩都劝我说那狐狸没事,让我静静地养好伤后狐狸会回来看我的。
他俩越劝我,我越按奈不住,由最初的担心它,一下子上升到了一种对它强烈的思念,进而达到了一种疯狂程度。
“我不想躺了,我要回到那个洞里去找它,走遍天涯我也要找到它"。感情的骤然升华让我完全失去了理智。我突然猛地翻过身去,想从炕上爬下去回去找它。
身边的姑姑一把拉住了我,舅舅也急忙跑过来把我摁住,我还在挣扎着,我忽然一把拉住舅舅,我开始痛哭。我哭着喊着:“舅舅,我狐狸妈妈还在洞子里面受苦受罪呢,请放开我,让我回去找我妈妈,舅舅,你也不能把你的姐姐留在那里呀!”我已不再理智,崩溃地失声痛哭起来了。
在我忘乎所以放声痛哭中,我又听到还有人和我一块儿哭。
“天哪,你俩怎么都哭起来了。”看着此情此景,舅舅着急了。他摇了摇还在恸情中的姑姑说;“姐姐,你看,孩子哭你也哭,与其说缓一缓,还不如现在就把实惰说清楚算了,免得一家子难受,迟早都得说嘛”。舅舅又继续说:“你也看到了,这小子虽然闹腾,说了肯定没事,孩子的身子骨好着呢,他精神上也能撑得住,你莫太操心了”。
经此一说,姑姑放开了手。说:“缘由己求,福由命造。你说的也对,他到现在还不知道谁是他妈妈,不明就里呢。难免心里难受,没有必要对他隐瞒了,还是你说了好”。
“那我现在就给他说,但是你得有个心理准备。”舅舅在给姑姑说话的同时,他也在偷偷的给自己"打气"。
我已经停止了闹腾,全神贯注地张着耳朵要听舅舅说什么,可是舅舅哼哼唧唧,这个、这个,这个了半天也没说上一句话”。
我急着又想闹,姑姑说话了,她对我说:“你看着我,我就是你的妈妈。”
这不可能,我根本不相信。“你是姑姑,不是我妈妈,你这么年轻,我的妈妈是狐狸。”我的声音有了一些放肆。
“肖杰,看样子,咱俩再怎么解释他都不会完全相信,只有让他亲眼看到我的原身,才会打消他的疑虑,解开他心中的疑团。”是姑姑说话。
舅舅:“哎,真拿你没办法,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让你见见你的狐狸妈妈吧。”舅舅扶着我的头,让我靠在他身上。
姑姑在我身边,我只见她的身子一闪,她就不见了,在她的位置立时出现了一只狐狸,是一只白狐。
我的脑袋嗡地一下,心似乎都跳到了嗓子眼了,狐狸在炕上给我摇着头、动着身子还摇着尾巴,还不停用尾巴抚摸我的脸。她又从炕上跳到地上,在地上转着圈,再用两只后腿蹬着地……
狐狸作完了那些动作后,她跳到坑上又回到了原位躺下身子,她身子一抖,立时,姑姑又出现在了我的身旁。
我“哇“地一声哭出声来:“妈妈,我的头一下子贴到了妈妈的怀里。”
几天来,在舅舅的细心照料下,我和妈妈都恢复过来。在这里,我知道了妈妈的名字肖霄,舅舅叫肖杰。妈妈还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肖山。我们一家人相依融融,心情愉悦。妈妈、舅舅给我谈天说地,让我耳目一新。她姐弟俩又是谈经论道,又是诵读经法,当然,其中有我能听懂的,多数听不明白。
又是几天后,这天晚饭时,妈妈给舅舅说:“小杰,玉虚宫挂起了素色云界聚仙旗,门山的年会也怏到了,我要去几天,小山你先替我带着,我不在的时间里,你先找个好去处好的学校,让他去上学,而后再教他学习一些道上的知识,我一刻不会耽误,理完了事情就回来。
妈妈说的去几天,事实上却是几年啊!有道是“天上一天,人间一年。门山在哪里?
我们一家人要离开这里了。妈妈、舅舅和我,我们走出了家门。
我环视了四周,除了树木和野草,再看不到一个人和一间房子了,在这看似山顶的顶端,原来就建着我们一家独院,就住着我们一家人呀。
我走到一高台处,打眼远望,山下面的原野辽阔,田间地头里还能看见有人在忙着夏收。
妈妈和舅舅在摧着我离开,我跑过去问妈妈:“妈妈,咱们走了,这里的房子怎么办?”
妈妈微微的笑了,说:“这房子会自动消失掉,像风一样漂落到星辰大海里,别问为什么,以后你去了就知道了”。
身轻气爽神情奔放,天高云淡、惠风和畅。我仰望苍穹,放开了喉嗓大声“吼”了一声,在身后留下了一长串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