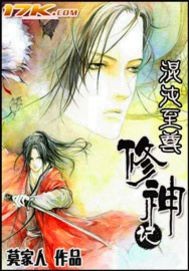泰戈尔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站在你面前,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朱小毛说: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是我坐在她面前,而她却要打我。
----------正文----------
出租车停在了位于玄坛弄的一座半旧的六层楼下,吝啬的路灯释放出苍白慵懒的光线,阴暗幽深的弄堂里窒息般的沉寂。
孔白谨慎地四下里看了看,轻手轻脚地走进了黑洞洞的楼道,摸索了好一阵子才勉强打开了铁门,当客厅灯光亮起的时候她快速地从门上揭下一张纸条揉在了手心里。
“啧啧,真不错!”朱小毛光着脚板在屋内伸头缩脑,东瞅瞅,西望望,看什么都觉得新鲜,整个就一刘姥姥。
这是一套老式的三居室套房,建筑年份应该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墙壁上贴的是时下非常时髦的素色墙纸,屋内家电家具一应俱全,一看就知道是城里非常殷实的小康之家,朱小毛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房子,不过那是在梦里,醒来后就只剩下口水了。
“不要乱碰,我去烧水”孔白嘱咐道。
朱小毛的屁股刚刚触及真皮沙发,闻言很识趣地站了起来,又伸出衣袖揩去了沾染的水渍。
孔白走进了卫生间,很快里面响起了煤气热水器的烧水声。
“这还差不多”朱小毛欣慰地说道,他已经被冻麻木了,手脚一点知觉也没有,这个时候世界上没有比洗个热水澡更令人向往的了。
孔白迟迟没有出来,门缝里冒出了热腾腾的水雾,耳边传来了哗啦哗啦的流水声。
“喂,我说水好了没有啊?”朱小毛冻得实在受不了了,走到门外敲了敲门提醒道。
“再等等”。
“得等到什么时候啊?”朱小毛冻得直哆嗦,真想从门缝里钻进去算了。
“等我洗完了”孔白脆生生地回应道。
朱小毛翻了个白眼,一口气没上来差点噎死过去。
十分钟、二十分钟,孔白还是没有走出来的意思,听得出来她很开心,耳边除了流水声之外,还飘来了几波惬意的**,确切地说是歌声,但在朱小毛听来,这声音简直是不堪入耳,猪的音乐天赋都比她要高一倍。
“我他妈真是剔了肉的猪蹄---贱骨头啊”朱小毛恨不得一脚踹进去把孔白拉出来,不过他没这个胆量,只能蹲在门外等待孔白出浴。
谢天谢地,流水声终于停了下来,朱小毛欣喜不已,唰一下站了起来,眼巴巴地盯着房门。
十分钟、二十分钟,纵然朱小毛在心里千呼万唤,但孔白却始终没有走出来,耳边隐隐传来了嘤嘤的啜泣。
朱小毛又冷又饿、又气又急,刚想抬手敲门,脑袋晃了晃之后一头栽倒在了房门上。
漫长的黑暗过后,耳边传来一阵阵凄厉的风声,身上顿觉灼热异常,仿佛置身于烈日的烘烤之下,鼻子里又隐隐闻到了一股焦糊的肉香。
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赤身裸体,被绑在一根粗大的铁杆上,身下是熊熊燃烧的火堆,孔白蹲在火堆旁,脸上带着快意的狞笑,一边狂流口水,一边卖力地往火堆里添柴。
“我的妈呀,烫死我了”朱小毛醒了过来,猛一翻身,叭叽一下摔在了冰冷的地砖上。
“你醒了?太好了,刚刚差点儿把我吓死啊”朦胧中孔白的笑容和梦里一样狰狞。
“你干什么?烤猪呢?”朱小毛吓得眼都直了。
孔白端坐在沙发上,双手各执一只电吹风,还在咝咝地往外冒着热气,难怪会有一个那么恐怖的恶梦,整个就一烧烤活人嘛!
“来,再吹吹”孔白舔了一下湿润的嘴唇,微笑着举起了电吹风。
“你饶了我吧”朱小毛吓得连滚带爬逃出了三米之外。
客观地说,孔白的“烧烤”技术的确不咋地,刚刚朱小毛摸了一下身上的零件,还好,四肢齐全五官尚在,只是头发和眉毛似乎不太完整,衣服也被烤黄了。
“真对不起,把你给忘了”孔白很诚恳地向他道歉,女人一般都有极强的自恋倾向,特别是在洗澡的时候。
朱小毛苦笑着点了点头,他直勾勾地盯着孔白,骤然间两眼大放异彩,又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
乖乖,眼前坐着的哪里是人啊,分明是天上的仙女嘛,纯的。
黑发如瀑明眸浩齿面若芙蓉,再配以粉腻无暇的肌肤和凹凸有致的曼妙身段,岂是用一个“美”字能形容的,只要看一眼就令人神情恍惚、飘飘欲仙,对了,北在哪儿啊?
朱小毛越看越着迷,越想越生气,敢情这造物神真他妈不是东西,人家孔白在天上玩得好好的,你凭啥赶她下界?让男人痴迷让女人妒忌,你这不是唯恐天下不乱吗?拜托,为了社会安定家庭和睦,把她重新收回去成不?
“漂亮吗?”孔白颇为不悦地问道,这种眼神她早就习已为常了,也不在乎多这么一对。
“又黑又丑”出乎意料的是朱小毛竟然摇头不止。
“嗡”孔白眼前一黑,脑子里天旋地转。
她感觉自尊心受到了致命的摧残,自从褪去了青涩之后,无论她走到哪儿都是焦点,慕美而来的追求者少说也有一个加强营,并且还在持续扩编之中。
但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眼前这个猥琐男竟然会用这么难听的字眼来评价她,看朱小毛这副样子,大有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之感。
“大吧?”孔白发现朱小毛一直出神地盯着她,看得连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很肥”朱小毛点了点头,视线始终不离她的胸前。
“你个流氓”孔白一吹风机砸了过去。
朱小毛眼疾手快,接住了能置人于死地的吹风机,笑嘻嘻地说道:“你肯定已经很久没有打扫过屋子了”。
孔白翻了个白眼,手又悄悄地摸向了另一只吹风机,心想,小样儿这回非砸死你不可。
朱小毛指着孔白,笑道:“要不然也不会有蟑螂爬到你身上了”。
“呀”孔白尖叫一声猛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一只肥硕的蟑螂此时已经快爬到她的脖子上了。
“我好心提醒你注意蟑螂,你倒好,还骂我是流氓,你真是麻袋里装猪---黑白不分啊”朱小毛笑弯了腰。
“真对不起,是我……”孔白意识到是自己想歪了,脸上顿时红白交加,内心自是惭愧不已。
为了表示歉意,孔白扎上围裙亲自下厨做了一顿可口的夜宵,两人风卷残云般地一扫而光,吃得满头大汗。
“你是不是只会烧方便面呀?”朱小毛把挂在嘴角的一截面条送进了嘴里后笑着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孔白惊讶不已。
“我用眼睛看的”朱小毛指了一下垃圾桶,里面被方便面袋子塞得满满当当。
孔白幽怨地叹了口气,连碗筷都没收就抱着枕头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这一坐就坐到了天亮,反倒是朱小毛更象是这儿的主人,他系着围裙忙进忙出,又洗又刷又拖又扫,忙得不亦乐乎,等孔白结束了漫长的神游后,眼前已焕然一新。
“我总觉得这房子好象不是你的?”朱小毛揉揉眼皮坐在了孔白身旁。
“何以见得?”孔白露出了一个疲惫的笑容。
朱小毛苦着脸伸出黑油油的双手,而后又指了一下悬挂在客厅墙壁上的一张三口之家的全家福,里面并没有孔白。
“对,这房子是我小姨的,几个月前她出国了”孔白很自然地挪了动一下身体,与他拉开了三尺多宽的距离。
“那你家在哪儿啊?”。
“家?”孔白楞住了,片刻之后她麻木地说道:“我没有家,现在这儿就是我的家”。
朱小毛眉头微微一皱:“不会吧,看你的样子应该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呀,你的父母亲呢?”。
孔白红着眼圈低下头去,带着哭腔轻声说道:“去了”。
“去哪儿了?”朱小毛随口问了一句,折腾了一晚上,他的脑子已经疲惫得转不过弯来了。
“你这头死猪”孔白愤怒地站了起来,手持枕头恶狠狠地砸向了朱小毛。
挨了一顿温柔的教训之后朱小毛终于又恢复了神智,但任凭他怎么道歉,孔白仍然不依不饶,两人围着一张沙发追来打去,一时间鸡飞狗跳,客厅里变得热闹非凡。
等孔白好不容易平息了雷霆之怒,天色已经大亮了,朱小毛张大了嘴巴靠在沙发上累得直喘气,还得提防孔白出其不意的“枕头攻势”,心弦一直崩得紧紧的。
“你多大了?”孔白发现朱小毛的性格非常外向,乐观自信的笑容始终挂在脸上,只是这张脸长得确实不怎么样,与他的纯真性格极端不符。
朱小毛惊悚地摇了摇头。
孔白:“你该不会蠢到连自己几岁都忘了吧?”。
朱小毛咕哝了几声后说道:“如果我问你几岁你会告诉我吗?”。
孔白笑了:“难道你不知道问一个女人的年龄是很不礼貌的吗?”。
朱小毛一本正经地说道:“难道你不觉得问一个男人的年龄也一样吗?”。
这种奇谈怪论把孔白逗乐了,她轻轻咳嗽了一声,说道:“那算了,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朱小毛突然问道:“你属什么?”
“我属Z……”孔白连忙闭上了嘴,心想差点儿上了朱小毛的老当。
“嘻嘻,你属猪,今年25岁,对吧?”朱小毛很是自鸣得意。
“你才是猪呢”孔白被气得脸都红了,这个其貌不扬的朱小毛狡猾狡猾地。
“没事没事,属猪好啊”朱小毛笑着说道:“那咱俩还真有缘哪”。
孔白将他打量了一番后不相信地问道:“你也属猪吗?”。
“不”朱小毛严肃地摇了摇头:“我是养猪的”。
话音刚落头上重重地挨了一下,孔白气急败坏地高举枕头,又开始满屋子地追打着他,朱小毛嘻嘻哈哈地闪过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还时常转过头冲着孔白扮猪脸直哼哼。
“咣,咣,咣”就在两人游戏正酣时,门外响起了激烈的拍门声。
孔白的脸色突然为之大变,枕头也失手掉落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