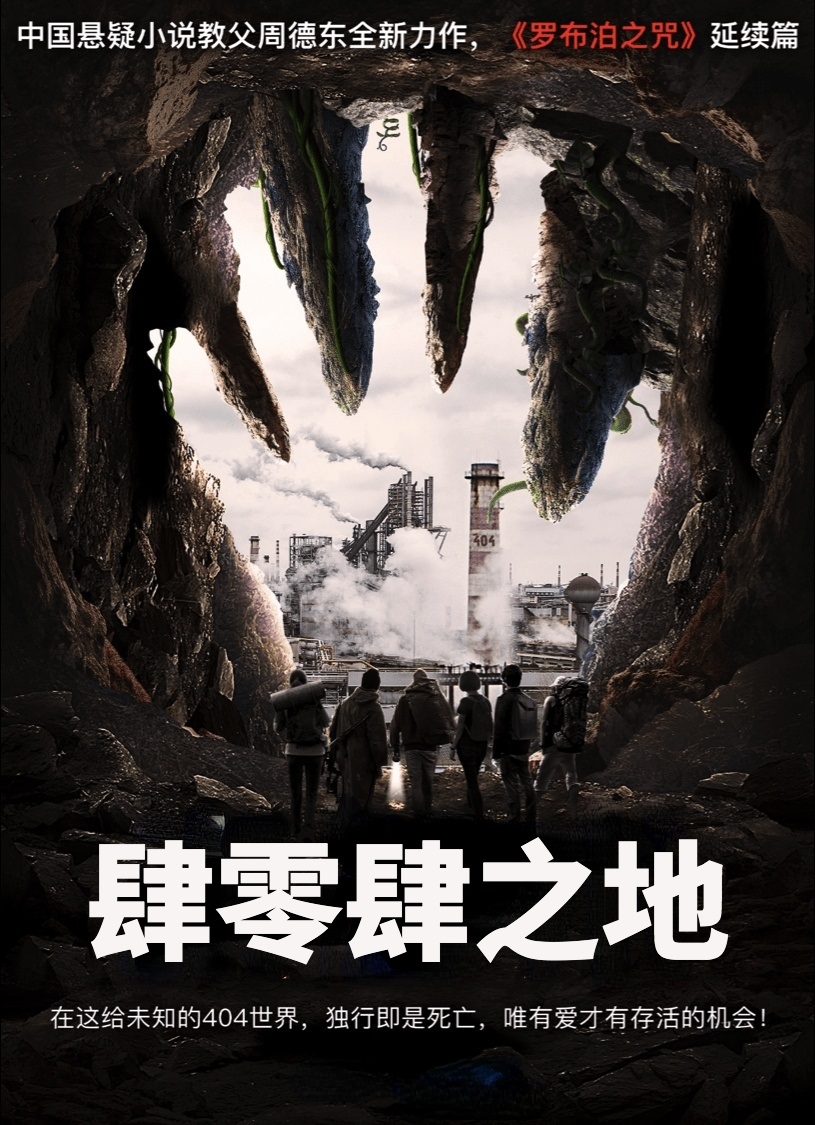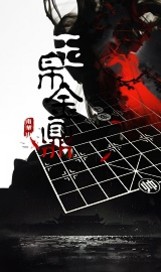清晨,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
这一天的天气很是晴朗,无风,无雾,也无云。
在这样良好的天气里飞行,恐怕会令无数飞行员和机长们欢欣鼓舞,也会让无数旅客们心情愉悦。蓝天碧草、天地分明,哪怕生活里有一些窝心的事情,在这样的天空中飞行自也能将之忘得一干二净。
然而事实上,今天地窝堡机场候机大厅中已是满满的愤怒累积,嘈杂的抱怨声和鼎沸的喧闹声已经让机场工作人员胀大了脑袋。早有等得不耐烦的旅客们开始打电话向各大航空公司投诉,更有甚至已经开始嚷嚷着退票。而各大航空公司也纷纷来电向机场询问情况,却发现他们拨打的电话总是在占线中。
三十二架航班延误,误点四个小时以上,而机场给出的延误理由竟然是“天气状况不佳”。
“否则我还能怎么说!?告诉全天下:我们之所以让大半个机场都在这里等着,只是为了等待一架官老爷飞机的起飞?而这架飞机之所以慢慢腾腾的只是为了等待一个人!?”来自调度塔上的声音显得有些愤怒,事实上他真的很愤怒。调度塔内所有人都很愤怒,因为透过调度塔的玻璃窗可以清楚的看到机场内的所有情况。
他们看得清楚那架飞机,也看得清楚那个唯一的乘客。
此刻,那架挡了所有航班的飞机正独自霸道的停泊在跑道端点,蓝白的机身干净明亮,显然是刚刚才被擦洗过的。无数机务人员还在四下里忙前忙后,为这架飞机检查着根本不存在的技术故障。而这架飞机的乘客,此时则正在无数人的团团簇拥下,在慢慢腾腾的从远处挪来。
挪来说明很慢,事实上是相当慢。视线放大后可以看清那是一副推床,推床的旁边走着朗飞鸿和他所有的下属,他们的面色都有些不大自然,好像受了多大的刺激一样。而推床的左手边走着一身邋遢的陈杰,这位大美女双眼通红,头发有些凌乱,显然已是一夜未睡。而此时躺在床上的,自然就是石穿。
雪白的绷带从头顶一直缠到了脚踝,从旁边看去这家伙此时更像是一具来自埃及的木乃伊。这幅样子确实很引人侧目,是要受了多重的伤才能被绷带缠成这幅模样?然而更让人侧目的:则是石穿所享受到的待遇——整个机场只为一个人服务的待遇。
朗飞鸿还清楚的记得昨天深夜那个电话的每一个字,每想到这句话,朗飞鸿都要全身颤抖一番,心底不寒而栗。他的大上司,用一个从未有过的愤怒语气在电话那头吼道:“立刻把石穿接到北京!我会安排全中国最好的外科医生为他进行治疗!全程由你们护送。我再告诉你一遍,如果这次再出现任何意外,记住,是任何意外!我要亲手你进军事法庭!”
石穿到底是个什么人?是哪门子的大人物?他哪里来的这么大的面子,竟然会让局长大人关切至此?连夜调派整个乌鲁木齐市最好的外科医生为石穿进行抢救还不算,竟还要封闭整个机场,将石穿转移到北京去?在这个国家里,恐怕没有几个人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吧?
朗飞鸿低头看了看床上那一动不动的“木乃伊”,心底里无数个靠谱亦或不靠谱的猜测酝酿而出,让他的脑袋瞬间运载过限。
而相对于朗飞鸿的好奇加疑惑,陈杰的心情却显得有些平静。那一夜狂风暴雨般的心情,在得知石穿脱离危险期后,终究如雨后云开,春风化雪,陡然变得宁静而安详。连陈杰自己都说不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快?
明明刚刚她还在心惊于石穿那最后毫不留情的一剑,明明她刚刚还在为石穿留下那一地的修罗场而感到阵阵恶心反胃。明明她之前的心情一直都是复杂而纠结,怎么突然就……
陈杰看着石穿被稳稳抬上了机舱,看着他被人轻手轻脚的固定在了车厢内特制的病床上,并小心的为他注射了安定作用的药物。这时,脑海中乱七八糟的思绪全都因放松而被深深的困倦所驱走。陈杰拍着小手打了个哈欠,俯身趴在石穿的身旁的座位上进入了睡眠。
而目睹了这一切的朗飞鸿则眼皮跳了跳,觉得自己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又很聪明的没有将它记住。替陈杰系好安全带后,他也赶忙找到了一个舒服点的位子,半躺着开始休息。故意不去考虑陈大美女和国安局某人之间的感情传闻。
不管石穿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总之,他自己回到北京之后势必要有一场暴风骤雨般的训斥和惩罚。没有好的精神迎接这一切,那是绝对不行的。
飞机在心惊与心安的对撞折磨下滑翔、起飞,直冲天际。指挥塔内一片欢呼,被愤怒和抱怨湮没了四个多小时的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也终于从心惊走入了心安。不管那个大人物是谁,他终究是滚蛋了……
三个半小时后,北京郊外一栋别墅的房间内,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正并肩站在病床前,关切的打量着病床上的“木乃伊”。
房间装修的很是精致,看样子是刚刚才被改造成病房的样子,干净、舒适、复又带着一种女性居所特有的温馨。消毒药水的味道和百合花的香味夹杂在了一起,一时间尚未散尽,让床上的“木乃伊”微微皱了皱眉头。
“真是不敢相信啊,快五十年了吧,居然还能再见到他。”男子感慨着说道。
“是啊,更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没有一点变化,仍旧是那个时候的模样……呵,真是羡慕呢。”女人捋了捋鬓边有些发白的鬓发,神情显得有些温婉。
“我已经把事情告诉老板了,老板暂时不会出面,不过他醒了之后,老板势必会见他一见。”男子的声音忽然变得有些大,似是要让女人听清楚。
女人双眉一挑,问道:“你想说什么?”
男子满脸戏谑的道:“我想说,你要不要先把你那几个国际会议给推掉?要知道,他在养病期间你就要去各国开会见不了他,而他醒了之后见了老板,估计你更没有时间去见他和他说说话了。”
女人的脸颊微红,啐道:“我这不就已经见到了么?还要见什么?好啦,你在这里照顾着吧,有事我再来!”说罢, 不等男人说什么,高跟鞋的叮当响动便渐渐远去,只在门口留下一个窈窕的身影。
男人叹了口气,似是对着病床上的石穿又似是在自言自语道:“唉,大人物的想法还真是无法理解。算了,谁让我只能是个小人物呢?老大,你可快点醒啊。要不然,她可就真的不敢来见你了……”
如果这句话被朗飞鸿或是他的下属们听到:堂堂国安第七局局长大人竟然会称自己做“小人物”也不知他们会作何感想。但对于石穿而言这些东西现在都没有什么意义,他首先要养伤,其次在养伤期间他还有些其他有意义的事情要干,没功夫浪费在这种揣测他人心思的无聊事中。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傍晚,石穿睁开自己沉重的眼皮悠悠转醒。他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把他送到了这个地方。但是他没有发现手铐,也没有发现监视他的警卫或封锁窗子用的铁丝网。他摸了摸胸口处,发现玉佩和那件得自古墓的东西都还在,更是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于是乎,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判断——这里是安全的。
既然安全,那就不需要再去冒险。
于是乎,石穿便放心的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养伤。每日里都有负责护理他的护士前来为他查看伤口并且换药、重新绑好纱布,然而每次来那年轻貌美的女护士都没有说出任何一句与养伤无关的话。石穿也没有问出任何自己心底的好奇。只顾着消灭那些美味可口的病号饭。
时间在这种沉闷却又安定的气氛中悠悠而过,眨眼便已经半个月了。半个月的时间里,石穿和护士要了一些杂志和书籍,并且通过申请弄来了一台小型的液晶电视。每天躺在床上的时间里,他就通过电视、杂志和各种各样的书籍来恶补当今社会的一切知识。
他知道现在最受人们喜欢的艺术形式已经不再是芭蕾舞或样板戏;他知道了中国已经换过了几代领导人;他知道了中国建成了三峡、发射了载人航天器还举办了奥运会;当然,他也知道了他老叔死于1974年11月,他死之前受了很多苦,无人在床头送终,直到死后多年才得以平反……
放下手中的书,石穿望着窗外的天空一时间有些失神。虽然早知会是如此,可亲眼确认这个消息仍旧让他心底狠狠的一阵刺痛。
“老家伙,你就这么走了?就这么把那个承诺丢给了我,让我这么半死不活的继续为你卖命……”嘴里碎碎念着,可眼角却隐隐有些发红。
忽然,房间门被人敲了几下,透过门口的窗子石穿隐隐看到了一大束百合花。这些天来,每日里护士都会为他的房间换上一束百合,石穿对此倒是已有了些习惯,因此随意的道了声:“请进”。
推门而入,石穿有些惊讶的发现百合后面的面孔竟不是那每日里呆呆板板的美貌护士,而是一脸娇笑如花的陈杰。
重新穿回白色连衣裙,穿着高跟鞋,留着披肩发的陈杰笑吟吟的将百合放在了石穿的床头,毫不客气的将他手中的几本书放在一边,美丽精致的脸蛋凑近了对石穿问道:“好点了么?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