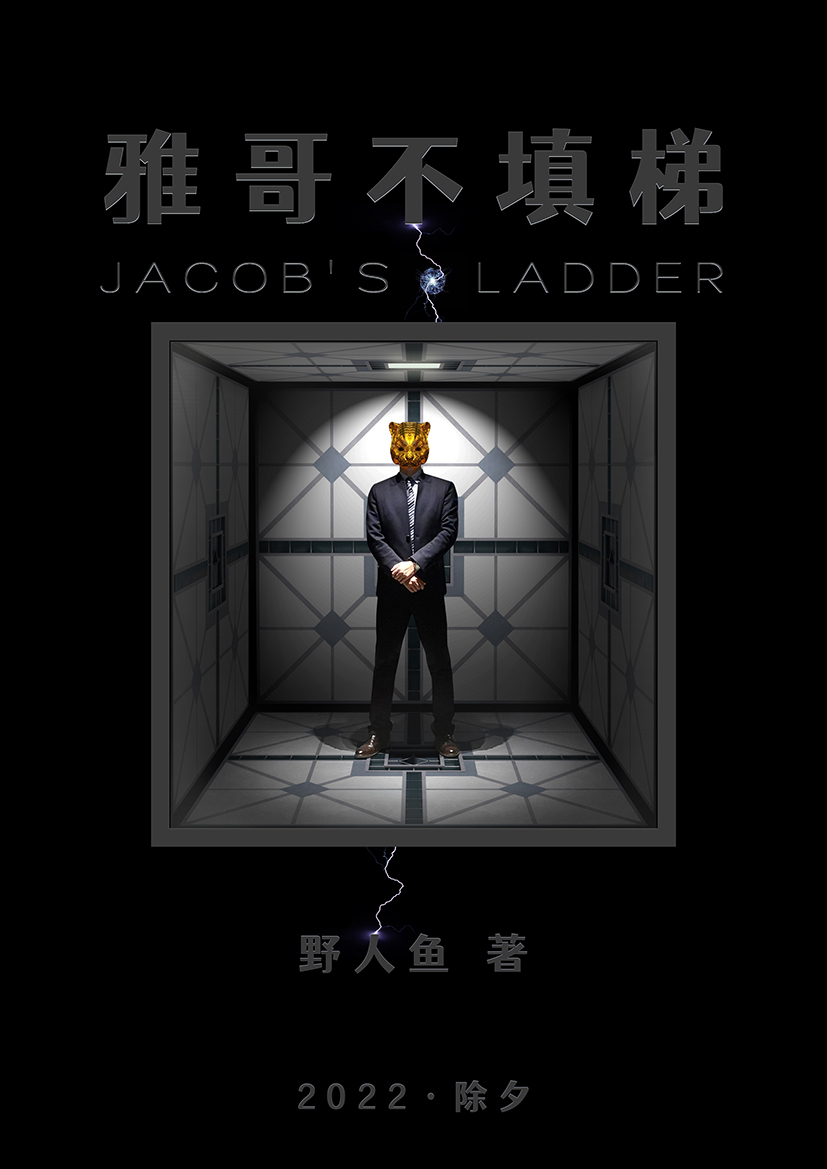长舌吊死鬼、红衣枯骨女、披发溺死魂、黑白无常索……很久很久以前,当石穿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村头巨大的古树下,那个老人就常常以讲这些荒诞不经的故事吓唬小孩为乐。
石穿还记得,那篝火旁、槐树下,身周不时有蝉鸣蛙叫响起。老人抽着旱烟,眯着眼睛,说着村子里以前发生过的古怪历史,说着狐狸、黄鼠狼和蛇精怎样迷人心窍,如何拍掉人身上三盏灯的可怕故事。
四下笼罩在阴暗中的山里时不时会响起一两声狐狸叫,让小伙伴们无不是瑟瑟发抖,偏又好奇无比的聚在一起,聚精会神的听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家伙吓唬着自己,就那样过了一个又一个有趣的夜呢。
想想看,在那个时候啊,倒是只有石穿自己是个例外呢。
在那星光灿烂的孩提年代里,整个村子唯有他石穿会边听故事边啃着玉米,翘脚坐在石头上,咧着小嘴嘻嘻哈哈的指点笑骂着,全然不把那些狰狞可怖的东西放在心上。因为他从小便不相信这些鬼神之说,他不相信,他的父亲和那个叫做副总司令的家伙也不相信。所以在当时的他听来,所谓鬼怪不过就是一些荒诞不经的笑话罢了。
可是如今,当这个诡异可怖的场景清晰无比的浮现在眼前时,饶是石穿也不由得感到无助的心慌、心悸。那些本来只有在梦里、故事里才会出现的东西们此刻竟似集会一样聚集在了眼前,就聚集在他们栖身的平台之下,一个个抬着根本没有五官的头颅,直勾勾的盯着自己。
没错,它们一定是在盯着自己。身体内数不清的细胞都在发出同样的声音:那些该死的东西正在盯着自己!
“那……那些都是什么东西?难道,都是蝼蛄?”石穿惊恐的问向身边的罗月,想当然他得到了预料之中的答案。罗月勉强用手支撑住身体,换了一个舒服的坐姿,撩了一下遮住眼角的头发对石穿道:“没错,就是蝼蛄。不过,你如果现在就开始吃惊的话,那还真是有些太早了……”
石穿深深的做了两个吐纳,却仍旧没有压抑住狂乱的心跳。刚刚对付一个蝼蛄人就耗费了他大半的体力,此时若是这么多的怪物一拥而上的话,就是十个石穿也只有葬身于此的结局吧。
罗月随手放下了58式*****的喷头,叹了口气道:“算了吧,本就没有出去的希望了,早些死了也早些解脱了。”
“你在胡说些什么!?”石穿恼怒道:“现在还没有到生死存亡的关头,别说这些丧气话!”
“呵……”罗月轻笑道:“是啊,你叫石穿是么?你之所以现在还没有说丧气话不是你有多么勇敢,而是你还没有看到让你震惊的东西,更没有看到无法解脱的死局。”
“死局?”石穿心头忽然一震。
“没错啊——死局,兵法中有一种地形叫做死地,棋局里有一种残局叫做死局……说到底,还是老人们说的最到位,上了奈何桥,心中就只剩下‘奈何’两个字了……”罗月说着,眼眶中的泪珠却已经同时滚落了下来,洗净了她被灰尘遮蔽的脸颊。
白皙的皮肤,就像是剥开蛋壳的蛋清一样欺霜傲雪。呜呜的啜泣声响起,在这个空静的洞穴里被衬托的如此哀伤、如此绝望。到底是什么,让这样一个绝美的女孩儿彻底失去了希望?到底是怎样的难关以至于成了女孩儿眼中无解的死局?
难道说,就是眼前的这些怪物么?
哭了一阵,罗月用衣袖擦了擦眼泪,忽然笑道:“真是的,都快死了还哭什么。革命者应该流血不流泪,倒是让你笑话了……”
“没有的事”石穿此时心情已经平复,一边和罗月说着话一边开始思索下一步的行动。围在平台周围的蝼蛄人越来越多,不过它们大多都聚拢在手电筒光线的地方,那应该是与生俱来的趋光性所导致的。看样子暂时不会来招惹石穿二人。
可是……石穿看着那忽明忽暗的手电光亮,心中却又开始了一丝焦急。大功率的手电筒耗电更是厉害,一旦电池里的电量耗尽,那么聚集在一起的蝼蛄人们恐怕不会对石穿二人怎么友善的。而如果真到了那个地步,恐怕就真如罗月所说,是不死不休的死局了吧……
“想听听我的故事么?”罗月忽然说道,让石穿略有些怔楞。罗月也没有等石穿的回答,自顾自的说道:“我老家在四川,却是在北京长大的,家就在原先地安门外不远的地方,小时候我经常跑到那高高的城门楼上去玩。”
洞中忽然吹起的风抚乱了她的头发,却没有抚乱她的思绪。罗月双手抱住膝盖,陷入了回忆之中,嘴角却挂着甜甜的笑容。石穿在旁边听着,丝毫没有打断的意思。此时,平台下的怪物们又多了几分,拥拥挤挤的都凑到了手电筒的周围。
“我的爸爸是民国的一名普通法官,妈妈则是北大的教授。我两岁的时候全家搬到了北平去,那时候啊,北平还刚刚从日本人手里拿回来不久。父亲和母亲的待遇都不是很好,因为很快又开始打仗了,他们这些清水衙门里自然也没有什么资金。小的时候,我和其他的孩子没有多少区别,既没有穿的多好,也没有什么佣人、轿夫之类的,我没觉得别人怎么普通,别人也没有觉得我怎么特殊……”
罗月说着,石穿听着,下面的蝼蛄人则在“吱吱”的叫着。身边是几具静静倒在那里的骷髅,平台下却是越聚越多的蝼蛄。
“北平解放的时候我很害怕,因为好多当兵的都涌进了城里。但是爸爸妈妈却告诉我不用怕,说好日子就要来了。那一天我还记得,大街上人山人海我就骑在爸爸的脖子上拍手看着解放军一排排的走过地安门。他告诉我:‘好日子就要来了’。后来,我也一直这么认为的。即使是当那座家门前的地安门被拆毁的时候,我也一直认为好日子越来越近了,因为爸爸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手电筒的光线愈发的不稳了,灯光忽明忽暗,照的那些怪物的身影也是一个个光怪陆离。罗月的眼光里,石穿正在随手抛着绳索毫无规律和冷静可言,样子像极了破罐破摔的失意者。
罗月说道这里顿了顿,复又低下头去“但是,到了五七年的时候,爸爸和妈妈忽然都变成了右佬——无可救药的右佬。而我也忽然变成了‘小右佬’——无可救药的小右佬,学校里面的同学再也不和我要好了,没有人理我也没有人过来关心我。包括老师在内,所有人都在让我写检讨书,让我自己认识自己的错误。可是,我用了很久很久,都没有发现自己到底哪里错误了。却又不得不写下那么长那么长的检讨书……”
“啪!”的一声轻响,手电筒终于灭了。聚集在平台下的蝼蛄人们霎时间一阵骚乱,“丝丝”的叫声不绝于耳,听的人耳膜生疼。罗月仍旧在平静的说着,石穿也仍旧没有打断,一边向平台下扔着绳索一边静静的听着。好似,不远处即将到来的危险,对他们已经再也没有意义了一样。
黑暗中,石穿似又在罗月的脸上看到了一星晶莹。“然后呢?”石穿第一次出声问道。罗月猛的仰起头,深深的吸了口气。
“然后啊,然后我就跑到禁闭室,狠狠的……狠狠的扇了我爸爸一个耳光。”罗月忽然又一次把头埋进了自己的膝盖里,双肩不住的颤抖着,哭着,哭着。石穿没有说什么,仍旧在静静的倾听等待着。平台下的蝼蛄们叫声越来越大,这些本来也听不到多少声响的虫子此时发出的声音竟然如此的刺耳,而且越来越响。
过了良久,罗月把头重新抬起来,黑暗中的双手擦了擦脸。“然后啊……我对自己和其他人说:我是党的孩子,不是右佬的孩子。我要和那两个人划清界限。于是乎,老师又开始喜欢我表扬我,同学们也开始和我接触,说我的思想觉悟变得高了,政治理想变得正确了。组织上还认为我的行为具有代表性,让我到其他学校去演讲。你知道么?是一个人的演讲!只属于我一个人的演讲!”
罗月的声音都带着一丝激动,石穿甚至能够想象得到,当时站在讲台上意气风发的小丫头该是多么的自我陶醉。胸前带着鲜艳的小红花,无数个学校数不清的同龄人要向她学习要为她的“勇敢”和“正确”而鼓掌。
“十八岁的时候,我报名参军。因为之前表现的极为出众,所以身为右佬后代的我居然通过了政审也能够进入军营,成为一名解放军的战士。来到四川,走进西藏。在战争中立功、受奖。一切的一切都变得那么的美好,爸爸没有骗我,好日子真的来了,好日子真的已经来了。直到……直到……”突然,罗月又一次哭了,只是这一次她没有抑制,哭得很伤心,哭得很难过。
嚎啕之声震动了整个山洞,那些聚集在平台下的蝼蛄们终于发现了把目标重新定在了两个人类的身上,无数张没有五官的面孔霎时间又投到了平台上来。数之不尽的脚步声隆隆响起,如同正在攻城的部队。
“直到”直到发生了什么?罗月没有说,石穿没有问。他当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她本来以为美好的生活变得不再美好。可是,石穿却又应该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啊,怎么会美好呢?
当心底里的良心和自己一直所接受的理念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候,当整个人被传统和现实撕裂成两半的时候,生活又怎么会变得美好呢?
骑在父亲脖子上欢笑的女孩儿、扇了父亲一个耳光面貌凶狠的女孩儿、没有参加父亲葬礼决绝的女孩儿……最后啊,只能是眼前这个哭泣的丧失了所有希望的女孩儿吧?难怪她这么轻易就放弃了希望,难怪她口中一直都在喃喃嘀咕着“死局”。她的心,是不是也早已随着那个突如其来的噩耗而一同埋葬了?
无数的蝼蛄人开始攀爬起了岩壁,“咯咯”的低吼声四处回荡,就如同一群看见猎物的野狗。野狗的数量多了,就算对手是独狼也不再会放在它们眼里了。何况独狼的身边正有一个哭声,哭声还是如此没有气力。
死局,无解可用的死局。
“都成为历史啦……别多想,喝点水,然后我们就走吧”突然,石穿对罗月笑了笑将那刻着字的水壶塞进了她的手里,语气就像是在对邻家小妹说着春日的郊游一样的轻松写意。
走,去哪儿?
罗月捧着水壶疑惑的抬起头,58式*****突然喷出的火光映亮了她那婆娑的眼睛和眼前那坚毅挺拔的背影。一束火光霎时间涌出,四个刚刚爬上平台的蝼蛄人浑身着火刹那间解体坠落了下去化作了满地灰烬。
又是一阵让人头皮发麻的悲鸣之声。
然而,在火光照映下,罗月二人却分明能够看到平台下正在攀爬的蝼蛄人已有近百个!而远处的黑暗中还不知到底隐藏了多少!密密麻麻的蝼蛄人有些还穿着人类的衣服,有些是绿色的军服,而更多的则是破烂不堪的木质扎甲。
更让人心惊的是,有几个蝼蛄人的手中,罗月甚至看到了武器,好像是木棒又好像是石块,可不论是什么那终究都是武器!会使用武器的怪物!若非那僵直可笑的动作,却又哪里分辨的出他到底是人还是怪物?这难道就是真正应该惊讶的地方?
58式*****烧毁了一批怪物又来了一批,打散了一队又来了一队。
反反复复,好似永无止境。这些由虫子构成的怪物们也好似根本不知道恐惧为何物、死亡为何物一样。前赴后继,一往无前。
身前的石穿紧咬着牙,将身后的罗月牢牢挡住。手中的喷枪死死的攥着,捏柄一直捏在最底处。空气中,很快便漂浮出了一阵烤焦的味道,而且越来越浓。
罗月轻轻呷了一口水,嘴角尽是苦涩。
终于,又一次到了所谓的死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