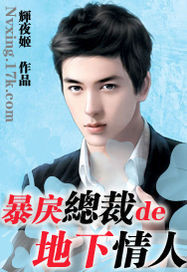共和国十九年,西元一九六七年,正月廿四,夜
北京藏经馆胡同,如今的北京反封建胡同。虽然时才入夜,但胡同内家家房门紧闭火烛不燃,静悄悄的,静悄悄的不起一声犬吠鸡鸣,好似一个幽暗的深渊。
从深渊尽头最高的那座吊脚楼顶上看去,正西方的孔庙大院里一团熊熊烈火烧得极旺。跃动的火焰如一只肆无忌惮的狂舞妖魔,正在不断的撕扯摧残着人们脆弱不堪的灵魂。狰狞咆哮、耀武扬威。
“呼”的一声。火光突然咆哮着窜起,噼啪的燃烧声伴着“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声震动屋瓦。狂舞的火焰耀眼夺目,将整个死气沉沉的共和国都城勾勒的一清二楚。
微风卷带着腾空的灰烬和纸卷焦糊的味道飘然而至,自石穿鹰钩似的鼻尖前飞过。石穿轻轻的嗅了一下,猛地睁开紧闭的双眼,一声叹息对着那冲天的火光长长的吐了一口白气。
并拢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他习惯性的轻轻按在自己的眉心处揉了揉。一声叹息便是此前的一生过往,从此以后前尘种种都将似那惨白的云烟,在冰冷的夜空中渐渐凝聚又渐渐飘散……
“朋友,给我一口酒”石穿放下手指,对并肩坐在他右手边的青年说道,没有丝毫客气。石穿从不曾对自己的朋友客气。即使这个朋友,与他相识不足一天。
身旁的青年苦笑了一声,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身上有酒?这个时候,酒可不是那么容易弄到的。”
“我不但知道你身上有酒,而且还知道你身上藏着的是地道的窖藏烧酒。更知道它在现在是多么不容易弄到。”石穿微笑着说完,又闭着眼睛轻轻的嗅了一下。直到这时,那个青年才明白石穿是如何知道自己身上有酒的。
他轻笑了一声,把腰间的军用水壶取下递给了石穿,没有丝毫的犹豫和推脱,虽然他的酒在现今价值几多粮票,虽然他认识石穿也仅仅不到一天。
一仰首,含有六十多度酒精的液体滚滚冲入石穿的喉咙里,辛辣刺骨。他的喉结上下窜动,一直持续了十多秒钟方才停了下来,哈出一口炽热的白气。
“好酒!好酒!好久没有喝到好酒啦!哈哈哈哈……”石穿将水壶一把递还给那个青年。青年也仰首喝了一大口,当然,他喝得不似石穿那么凶猛。但仅仅一口就让他洁白的脸上腾起一层红晕,好似一个羞涩的姑娘。他看了一眼面色如常的石穿,飞快的拧上了壶盖。
“你叫什么名字?我的朋友?”石穿又品了品嘴里残存的酒汁扭头问道。这个问题很怪,身为朋友,又怎么会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呢?然而事实就是他确实不知道,而且他们两个也确实是朋友。
那个青年晃了晃有些眩晕的头,笑道:“岳枫”。
“真名?”
“我只能告诉你——岳枫。”
“好吧岳枫,你的酒从哪儿来的?”
“从我母亲那里。”
“你还有母亲?”
“只要是人谁都有母亲,我为什么会没有?”
两人对视一眼,忽然哈哈大笑。正西方的火焰在这一刻再次突然爆炸似的向天空猛地一窜,不知又有多少图书古卷被丢进了那恶魔的腹中,临死前发出了呜咽的鸣叫。
“你能帮我什么?”石穿搓了搓手,再次毫不客气的问道,他跟朋友从不客气。
岳枫叹了口气,反问道:“你真的要去救他?”
“马上就去。”
“你可知道,若是你成功了,明天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
“我不知道”石穿轻哼了一声,锐利的眼睛紧盯着远处跳动的火焰,好似火焰正在他的眼中跳动,他淡淡的说:“但我知道的是,如果我失败了,明天至少要有二十颗人头落地,我要用那些混蛋的血铺成十丈长路。以作祭奠……”
远方的火光忽明忽暗,火光打在石穿的脸上就像打在了一柄雪亮的刀锋上。而偶尔发出的橙红色,就像刀锋上即将滴落的血珠。
冲动——就如同其他人对石穿的评价一样。可转念一想,如果石穿不冲动,他又为何成为石穿?
岳枫叹了口气,道:“一辆牛车一副棺材,两套绿色军服外加三天干粮。只有这些了。”
石穿点了点头,带着刀疤的手掌重重的拍了拍岳枫的肩,道:“带上这些东西在塔园东街等我。”说罢,他不等岳枫回答,颀长的身影缓缓自五人高矮的屋顶站了起来,脚下瓦片一声轻响,石穿片刻便稳稳的落在了楼下的青石板上。
胡同里仍旧静悄悄的,没有哪怕一声犬吠鸡鸣。石穿就像是一只敏捷到极处的野猫,身影旋即便在黑暗的城市里湮没。
正西方,大火最后一次爆炸似的腾起,满载着红卫兵们狂热的欢呼声缓缓熄灭。屋顶上,岳枫重重一声叹息,再次给自己灌下一大口烧酒,转身离去。黑暗好似汹涌的洪水般,刹那间淹没了所有的光明……
都城已经入夜,可喧闹声却总是在搅碎着惯常的平静。
不知是不是商量好的,从反封建胡同一路向西,沿途竟然先后出现了十余支抄家队伍。那些佩戴着红袖标提着手电筒和木棒的红卫兵们,一个个飞扬跋扈,悍然砸开居民的屋门直闯进去,将里面正在熟睡或是正在用餐的人拖拽出来。更有一些直接就是劈头盖脸的殴打。
打啊,砸啊,为了领袖的号召而去努力啊!只要打烂了旧世界,砸碎了旧规矩,新的世界就可以在废墟上建立起来啦!
可是这些半大的年轻人还不明白,如果世界和规矩全都打烂砸碎,那么他们又要用什么去建立崭新的世界呢?靠拳头板砖?还是碎石残渣呢?
那墨香浓郁的书斋前,鼻青脸肿的主人亲手捧起自己的藏书,一声叹息将之抛入了翻腾的火堆;那阴森幽暗的梨园外,身着戏服头戴木枷的名角们跪地指天赌咒发誓,将自己比作牛鬼蛇神,两行浊泪却花了脸上精美的粉彩;那往日相敬友爱的邻居呦,你为何要说我背叛革命,面目变得如此狰狞?那原本懂事乖觉的孩子啊,为何你今日踢打着你的父母,声色俱厉的要与这些“过错”一刀两断?
满地伤痕。
这个夜里,京城内火光四起烟笼大地。可不知,那些被点燃的,是百无一用的“四旧”还是整个民族积累千年的文明?满地破碎的纸页擎着石穿的双脚,让他一路唏嘘一路龋龋独行。
忽然,石穿停了脚步。那是一处欧式风格的民居外,一名年轻的女子正在被几个红卫兵殴打,而她的两个幼小的孩子正在那里声嘶力竭的哭号。他看见了那两个孩子,于是又想起了一些并不愉快的往事。
烦乱、压抑、愤怒……惨叫声和哭号声交织在一起传入耳朵,实在是让人难以忍受偏偏其中还夹杂着殴打者不休的喝骂。可石穿没有出手也没有出声。他只是用右手双指按了按眉心。因为……现在他还不能惹人注目。
旋即抬脚,石穿继续沿着自己早已确定的路线,在火光遍地的都城内快速穿行,奔向自己的目标。
目标在北京航空学院。
于是乎他在东门外停下,看了看黑夜之中仍旧人来人往的门口,双手抱胸把八角军帽的帽檐压低,斜倚在门墙外等待着。既然这里便是目标所在,那么他就要等——他在等着自己的体力恢复到最佳状态,等待最佳的行动时机。
为了这个时机,他从大西南一路辗转北上,风餐露宿。抛弃自己光明无比的前途、抛弃自己安稳无比的生活,甚至成为自己以前最为厌恶的“人渣”也在所不惜,只为了这个目标,只为了这个时机!这样的机会,很难有第二次。
故而这次行动决不能出错,故而他需要等,他不在乎短短的十五分钟。
感受到体内力量再次充盈起来后,充分热身的石穿顺手从背后抽出了惯用的****,并将之收在了右手的衣袖里。他取出一件准备好的红袖标戴在左臂上,大摇大摆的走进了这所大学的东门。
“最高指示:将大革命进行到底。同志,您找哪位?”门口站岗的红卫兵对石穿礼貌的问道,言语中并没有多少怀疑。石穿如今也仅仅二十八岁,并不比他们这群狂热的青年大上多少。仅仅看脸的话,星眸薄唇的石穿甚至还能显得更为年轻。而如今的北航正是天下“有理想”的年轻人聚集的地方。
“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同志,我是北京工业学院的,来找你们学校的张有才有点事。”石穿再出口时,原本的一点点陕西腔一扫而空,却是标准的京片子。
那个红卫兵显然不知道张有才是哪一个,其实石穿也不知道,他从来不知道有什么人叫做张有才。他只是想找个借口混进去罢了,于是他就这么混进了北航的校门。
昔日培育高等人才的学校现在早已成了准军事基地的模样,红红绿绿的标语贴的到处都是,以前洁白的墙壁上也不知是被谁画上了大革命的宣传画,画面张力十足,有种让人躁动起来的魔力。四下里巡逻的红卫兵虽然缺乏训练,但也有了点保卫基地的架子。唯一有些差别的,就是他们手中握着的不是钢枪,而是木棒。
“希望薄家的二小子没有骗我……”石穿左右扫视了一圈后,再次压低了帽檐,贴着大树的树荫转身向“地质学院”的教学楼走去。那里,就是他情报中的目标地,他要救的人就应该在那座大楼的二楼拐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