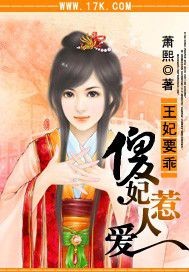那个女人眉眼的温柔从来不肯对我,温暖的怀抱更是没有。
她总是耐心地教导哥哥,对我却是疏远避开,冷生冷语。
明明我那么努力地学乖,极尽全力去讨好她,她为何要对那个一颗真心捧手心的小女孩那般狠心?为什么每一句娘亲带来的不是疼爱,而是训斥?
明明最调皮的是哥哥,那个最让人讨厌的哥哥,那个我疯狂地嫉妒的哥哥。
我以为我只要表现得很乖更好,早晚可以融化她。
可事实证明并没有,她竟将我送给别人!为什么不想养我还要生我?她拜托那家人好好照顾我,为什么不要我了还虚情假意?
我恨极了她……
她强迫我吃下了一种药,这种药会让我忘了一切,可凭什么她能决定我该记得什么,不该记什么?
在睡梦中,我不停地反抗,我不要忘记,我要记得!
长大之后我还要找到她,问她为什么对别人那么友善好?为什么唯独对我这么绝情?为什么唯独不爱我?
她这样丢下了我,睡着的我什么都干不了,我每日恨着,盼着。
若她回来,我会原谅她的,我是这么想的。
可是并没有……
照顾我的那家人没食言,最起码在前几个月中,他们把我照顾得很好。
他们家的那个小男孩老是喜欢来我床头说话。
和我说他昨天学了哪本书,今天会背哪首诗,还老是抱怨隔壁的小虎妞又来找他。
可他不喜欢和她玩,他说要和我玩,因为我是他见过最漂亮的小女孩;他说他知道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是可以成亲的;他说等我醒了带我去抓蝴蝶,烤地瓜,还要教我读书写字。
他会把每天放学路边的花朵摘下,放在我头边,说这是给我的礼物。
他会给我讲各种故事,讲各种道理,他想让我快点醒。
他拉着我的手写下他的名字,说要我记着他的名字,约定好了就不能忘。
我不要答应他,那只是他单方面的约定,我不同意,等我醒了,我要去找那个抛弃我的女人,我要让她后悔,求我原谅,我才不要和呆呆蠢蠢的他呆在一起。
突然有一天,他生病了,再也不能采花送我,也不能来给我讲小故事。
我有些害怕,我挣扎着起来,想要去看他,可我做不到……
我听到他父母说,他病得越来越厉害了,治病要花好大一笔钱,而当初那个女人给的钱财已经全部花光了。
已经在没有办法了,为了能让他好,他母亲把自个儿卖了。
我再听到他的声音时,是他哭喊着让他母亲不要走。
那个每天和我讲话的稚嫩声音,竟已经变得如此嘶哑虚弱了么?
我心疼了起来,即使摔伤了也没那么疼;即使被哥哥欺负也没那么疼;即使被那个女人丢下也没那么疼。
从来没那么疼过。
我想去安慰他。
我想告诉他,之前所有的约定我都答应了,他能不能不要哭?能不能快点好起来?能不能再和我说说话?
在那之后的一年,我时不时能听到他咳嗽,治疗之际痛苦之时,他会不住病弱呼唤着他母亲,也会唤着我。
他那么痛苦,我想看他一眼都做不到。
眼皮好似千斤重,怎么也抬不起来。
渐渐得他似乎好些了,我抑制不住地欣喜。虽然那个庸医说他的病只能靠昂贵的药吊着了,但我不管,我只知道他终于可以下床了,终于能来看我了。
他每次来到我这儿都蒙得严严实实,不敢靠近,不敢再对我说话。
我知道他怕传染我,可我好想告诉他,我一点都不在乎。
病死总比在床上躺到死要好,我只想再听听他的声音,再听听他对未来的期盼,我憧憬着,愿意的。
他偶尔会握住我的手,冰凉的小手在我手心不知疲倦地重复写着同样的文字,洗完又帮我擦干净。
我想大骂他笨蛋,写了还擦,怎么能留下?我又想骂自己笨蛋,什么都没写出来,又怎么能留下?
再后来,我什么都听不到了,手掌上再也没有任何写字的触感。
如果他病好了为什么没来找我,如果病没好,快死了,他能不能来和我招呼一声。
我恐惧到极致,不,不要死!求他不要死!
我恨这该死的命,恨那个狠心的女人,恨这病让他遭受如此折磨。恨再也见不到他。
我要醒,我要见他。我要告诉他,告诉他,他是对我最好的人;告诉他,他我心中最可爱的男孩;告诉他,别放弃,一定要活着。
可直到睁眼的那一刻,我全忘了……
我竟然全忘了!我怎么可以忘?!忘了哥哥,忘了那个女人,忘了猎户一家,忘了他,忘了他反复在我手掌心写下的名字。
他那么反复研写的名字啊!
离开之前,最后一眼,他全然没有一丝血色,小小的身体枯瘦如骨,似乎仅那么一口气。
可恨他居然背着身子对我,居然一声都不吭。
更可恨我居然也一言不语地走了。
这么一切的一切,我都记起来了。
为什么不早一点?早一点,离开的时候我就可以和他说再见;早一点,我就可以找到他;早一点,我就可以见他最后一面。
为什么,不早一点?
“任柯。”
我泪眼婆娑地抱住那个小小的身体,就像抱住曾经的那个小小身影,再不能自己,泣不成声。
“你别哭。你记起什么了?没事,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小小的手掌抹着我的眼泪,却是越抹越多。
悲不由己,我放声恸哭:“不能过去,怎么能过去?枉乐初,你不懂。他死了,死了!可我现在才想起来!我怎么才想起来!”
月娘走之前的那一眼,想来十分嘲讽。
记起了一切的我失去我自己,失去了我最渴望的亲情,我失去那个爱我的男孩。
原来,记起的一刻就是失去的开始。
我再也不想去找回那所谓的身世了,我再也不要去找那个女人,是她抛弃了我,我还找她干什么?
我好想忘记这一切,可我又舍不得忘记他,唯一对我好的他。
枉乐初抱紧我,对我道:“忘记不是方法,要清醒着,哪怕是痛苦着清醒。”
我默默流着眼泪,看着他漆黑的瞳孔反驳不出一句话。
我在里面看到了更极致的裂缝,那是他的。
我不知道怎么回到房间的,只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这夜啊,竟如此漫长……
清晨一缕阳光从皑皑白雪中跃出,洒在结成冰面的域水河上,洒在河岸垂柳,洒在积雪屋檐,却洒不进人心里。
“嘎吱”修五真推门而入,唤了我一声:“任姐姐,该出发了。”
当她看到我红肿的眼时被吓了一跳:“怎么了?”
我扯出笑容:“想起了些伤心往事,没事的。”
握住手心,我低头轻轻吻上手背,敛尽所有情绪,回头对她淡笑道:“走吧。“
当走出房间,枉乐初他们已经在等我们了,枉乐初打量了我一眼后什么也没说。
凌燕肃和修五真一样的讶异,但也没问什么。
我看向曲箫默,他身体好似完全恢复的样子,不说的话,谁知道他的灵体已是落日黄昏?
想起颜妤,我握住掌心,暗暗下定决心。
……
我们一行人来到域水河畔,河畔上人来人往,依旧密集。
想来最后一易,所有烟柳巷的人都不会错过的吧。
域水河上空,青色莲蓬郁郁青青,散发生机。
潇潇、司徒昭颖、寻蜜三人已经提前醒来。
她们落下青蓬,站至冰面上,但她们几人并未退开,反倒留在青蓬下方,各有所思地等待着什么。
河畔上的人群里也有些不安分的,想望冰面上去,却是一踩一个冰窟窿,落入水中被冻个半死。再对比潇潇她们稳步站立在其上,所有人都明白了,只有像她们这样连过两易的女子才可以踏上这层浅冰。
在漫长的等待中,所有人也迎来了主持易主典的百岁老人们。
她们的到来宣示了易主典即将迎来终章。
我的目光始终锁定着颜妤和凌惜爱,她们因获得幻莲境心的部分是最大的,所以还没转醒。
随着青光迸发,浮于颜妤她们头顶的幻莲境心逐渐消融。
“颜妤要醒了。”
曲箫默看得真切,对我们说道:“凌姑娘所获部分最大,怕是还要再等一会。”
凌燕肃惊奇道:“这个幻莲境心有什么好处啊?而且家妹居然还能取得最大的部分,你们在里面到底遇到了哪些事,我真是好奇得很。”
曲箫为他解释道:“最顶级的九瓣不死莲才能生出幻莲境心,在青蓬的帮助下,她们能最大程度地吸收幻莲境心,从而拥有能看穿事物虚幻真假的心眼,并且幻莲境心还能开阔视野,延长视线。若是配合九瓣不死莲使用,效果更佳。至于凌姑娘获得这一部分,还得是任姑娘的功劳。”
我解释道:“这是惜爱应得的,在抢夺幻莲境心时,是惜爱和我一道的。单凭我一人也没办法击碎它,更没办法于混乱之中取得很大一部分。”
凌燕肃拱手向我道谢:“不管怎样,都多谢你了。”
我接受了他的谢意,看向域水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