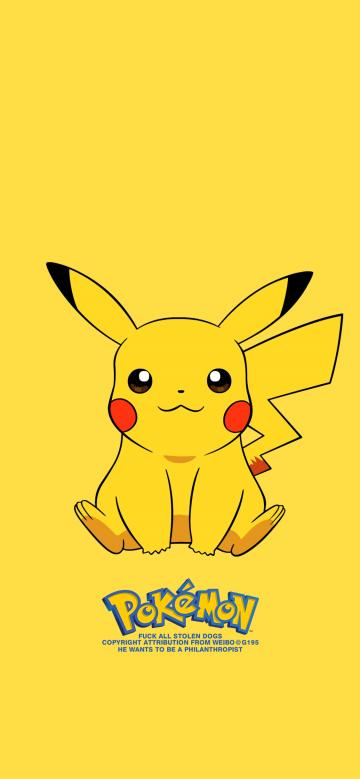春水今日要回剧团了,早上,他开始收拾行李,行李收拾好了,在家吃过早饭后,他告别父母回剧团去了。
演员们都回到了剧团,几天的小别,今日相逢,大家都很开心,相互问这问那。春水又见到了妍萍,他这几天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妍萍。剧团吃中饭的时候,赵团长通知说:“下午两点钟剧团要开会,都不要到处跑了。”
演员们都吃完了中饭,春水洗了饭钵回到自己的宿舍,妍萍又到他宿舍来了,才哥和李姐还在厨房收拾忙。春水迫不及待地拥抱着妍萍亲热,妍萍也回搂春水,亲热片刻,忽听才哥和李姐在门外面说话声,他们要进来了,春水二人连忙相互松开了。才哥和李姐进来后,四个人又说笑聊闲话。快到下午两点钟了,四个人出门去开会去。
剧团开会,赵团长在会上说:“今日开会,主要是春插假回来,剧团后面的工作安排一下,主角老生演员周昌文,也因为要结婚,他没来了,昨天他到过我家里,他说,结婚后他回不回剧团?他现在还说不准。上次李祥也是回家结婚不会来了。所以,今后老生演员,主要是吴志军。另外,招了个新演员,名叫徐吉财,他是有基础的,在其他剧团唱过戏,他可以替代李祥偶尔唱老生角;他也可以演净角花脸。以后演大型的戏,演员还是不夠,还要招人。”
大家看男演员中有一个生面孔,他就是徐吉财,年纪约二十二岁。赵团长说完后,刘导演也在会上说了一阵,刘导演说话,主要还是角色指导。散会了。晚上演戏,来看戏的人比放假前那几天多些了。在这个戏院再演了三天戏,剧团又要考虑搬迁了。
这一天,剧团又在搬迁了,道具上好了车,演员也都上了车,汽车开走了。天气又阴了,但没下雨。湘北的天气,农历四月转初,虽然时节已过立夏,但气温仍不高,人们还需穿秋衣秋裤。汽车在乡公路上行走,演员们坐的仍是露天无篷的货车,大家坐在自己的行李上看四处风景。乡村的景致,盛春已过,到处野草疯长,山上的树木新鲜的绿叶愈来愈浓密了。堰塘边、田坎上可见娇艳好看的金银花藤清香四溢;也还可见艳丽的叫不出名字的野花适时开放;田野里新栽的秧苗已经活蔸了,微风吹过,绿浪起伏,似碧绿的锦缎在飘动。农人们过了春插,其他农活也没那么紧张了,稍微闲适了些。有的人在田里撒化肥,有的人在田边埂上种黄豆。也有人在堰塘边钓鱼。
汽车到了目的地,此次搬迁仍是一个村级戏院,这个村子是在丘陵地带,戏院是建在山坡上的,挨戏院那边是村部,村部也很简陋,几间旧平房,大门前挂着村部的牌子。这个戏院条件好差,没有专门的宿舍和厨房。虽然戏院条件差,但据说这里的人很喜欢看戏。村里领导帮忙安排食宿处,就近的农户只有一家,这家房子不大,三间搭一偏土砖瓦屋,只能租其厨房做一下饭,腾不出可住宿的空屋。最后村里领导只能这样安排演员们的住宿,戏院后边有两间空屋,空屋里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村里领导安排管戏院的人把空屋里乱东西拿走,然后清扫干净,又帮忙在农户家里借了些稻草,演员们便在空屋里打连地铺,男女演员各住一间。因再没有单独的房间,春水和才哥也只能和大家一起开连地铺。重要的东西就放到票房去。这两间空屋也窄小,演员们都勉强挤着开铺了。赵团长和刘导演及王副团长几个领导就到卖票房开了地铺。一切安排好了,当天晚上来看戏的人果然很多。
第二天,天气下雨了,演员们只能在宿舍或戏院内活动。中午时候雨住了,赵团长看了天,说:“下午应该没雨了,晚上应该有人来看戏。”
下午,才哥和李姐请假到李姐家里去了,春水听才哥说,是商量准备结婚的事。下午果然没下雨了,但路面不很干,晚上来看戏的人比昨晚还是少些。
散戏了,演员们都卸了妆,都洗漱完毕。时间才晚上十点半钟,演员们都到了地铺上,必然要嘈闹一会,不会很快睡觉。正在热恋的男女演员便要在一起亲热一会才各自回铺去睡觉。此时门外面又下起雨来了,丝丝凉意透进了屋里。春水已经到地铺上了,妍萍来了,她坐到春水铺上,春水便将她搂在怀里抱着,他将薄被盖在她身上,就这样相依偎着,小声说着亲热话。
春水的地铺是靠墙角边,这边是挨着吴志军的,吴志军原是和江峰睡的,后来江峰走了,吴志军一直一个人睡。?一会儿,演员们大部分都安睡了,只有少数人还在叽叽哝哝小声说话。春水和妍萍还在依偎。春水轻轻地握着妍萍的手儿,轻轻地抚摸。他说:“妍萍,夜深了,大家都要睡觉了,你回女宿舍睡觉去。”妍萍起身回女宿舍去,她的腰间挂了一串钥匙,起身时候,钥匙叮叮当当的响,这响声在静夜里很清脆。妍萍回女演员宿舍去了。
次日仍是雨天,一早上,演员们都吃过了早饭,春水回到宿舍,男演员都在宿舍里,刘喜儿忽然说:“昨天晚上有人搞鬼。”
“哪个搞鬼?”有人问。
刘喜儿说:“文春水和吴妍萍,半夜时候,我听到吴妍萍起身离开的时候,她穿裤子的声音。”
春水大惊,怒道:“刘喜儿,你好无聊!”
“我怎么无聊?你敢说你们没做那事?那叮叮当当的响声,肯定是吴妍萍穿裤子皮带扣的声音嘛。”刘喜儿说。
春水怒道:“刘喜儿你胡说八道!妍萍离开的时候,你听到的响声,是她腰间挂着一串钥匙发出的声音。不是你想的那样。”
正吵时候,王副团长来了,问为什么吵?大家都不做声,春水也不做声,刘喜儿也没说话了。王副团长说:“大家出门在外要像兄弟一样,要团结啊,吵什么吵?”
吃中饭后,剧团开会,在戏院内,王副团长在会上说:“我听说,剧团有人作风不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愿不是真的。你们千万要注意啊,我是剧团专抓纪律的,去年腊月时候,分管文化事业的李镇长找我谈话,问我剧团的情况,我汇报了,他还满意。临走时他又特别交待,说剧团一定不能乱搞男女关系。你们现在谈恋爱,本来剧团开初的时候有规定,是不准谈恋爱的。但现在年轻人到一起谈恋爱也是正常的事情,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你们不要太离谱,不要坏了剧团的风气,不要闹不团结。”
春水心里明白,王副团长是在说他,是有人在王副团长那里说了什么。但春水也不想争辩,怕越描越黑。
赵团长又在会上说:“当初剧团规定不准谈恋爱,也是因为剧团开初建立的时候,演员们学戏阶段,在业务上都还一窍不通,怕谈恋爱会影响学习。其实年轻人到一起也免不了要谈恋爱。这也是人之常情。你们谈恋爱可以,但不要闹不团结。也不要捕风捉影说人家的怪话。”
春水觉得赵团长说得有理。最后一句,春水觉得赵团长是在替他说话。
散会了,王副团长把春水喊到一边,细问上午他和刘喜儿吵架的事,春水做了解释,王副团长说:“春水,你的人品我相信,我信你。这事算了,你也不要再和刘喜儿吵架。”
这天的天气,一直下雨没停,时而小雨,时而中雨。赵团长叹道:“看这天气,今天晚上怕是没人来看戏了。”
刘导演说:“等到傍晚七点钟时候,若是雨还有停,也没有人来买戏票,演员们就不要化妆了。今晚就不演戏了。”
因为外面下雨,演员们不便在户外活动,都在宿舍里,坐在地铺上,把腿掖在被窝里。男演员宿舍里,妍萍在春水铺上和春水挨着坐,春水把薄被盖在妍萍和他的腿上;赵健和方红梅在赵健的铺上俩人挨着坐。男演员们都在。赵健忽然笑说道:“都坐在这里发呆,没有事做,我们说笑话听好不好?”
春水笑道:“赵健,你有什么好笑话?你先说给我们听。”
赵健笑着说:“好,我先说一个笑话:从前,有一个秀才,是个白字先生,他经过文庙的时候,看着文庙二字就读,文朝;因为庙字的繁体字是广字里面一个朝字。刚好,又一个秀才也经过,后来的秀才就说,这位朋友,你读错了,不是文朝,是又庙。前面的秀才就争辩起来,说你个白字先生,明明是文朝,哪里是又庙?二人争吵起来,一个说文朝,一个说又庙。最后打了起来,打架也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二人就到县衙打官司,县老爷问了事由后,怒道:你们二人是为这个打官司?我也断不了你们的案呀,我又不是孔天子!我也不是苏东皮!我怎么知道是文朝?还是又庙?各打五十板,轰出衙门。
其实,三个人都是白字先生,县老爷把孔夫子说成孔天子,把苏东坡说成苏东皮。”
赵健说后,大家都哄然大笑起来。
徐吉财也说:“那好,我也来说一个笑话,其实,我说的是我们家乡以前的真人真事,是清朝末年的事。我小时候听一些老人当笑话讲的。从前,我们家乡有一个趣才,听说还是个秀才,他很聪明,也是个不务正业的歪才,他名叫汪宗儿。这个汪宗儿一生都喜欢捉弄别人,有一次,他看到大路上有几个年轻妇女过路,那妇女都长得漂亮,都提着小蓝子。他就跟别人打赌,说,你们信不信?我马上去跟过路的那几个年轻妇女都亲个嘴儿。有个人笑道:汪宗儿,你如果跟那几个妇女都亲到了嘴儿,我赌你十两银子。亲不到,你输给我十两银子,好不好?汪宗儿说:好,就赌十两银子。汪宗儿连忙跑去拦着几个妇女,说:你们几个女的,刚才为什么偷吃我家的柑子?妇女都说,我们没偷吃你家的柑子啊,刚才大路边上,是有户人家有柑子树,但我们没偷吃啊。汪宗儿说:我不信,你们的嘴巴让我闻一闻,偷没偷吃,我一闻就知道。几个妇女没法,只得都让汪宗儿闻嘴巴,汪宗儿的鼻子贴着女人的嘴巴闻。站在远处的那个打赌的人,还有几个看笑话的人,都笑弯了腰,不得不佩服汪宗儿的聪明。打赌的人就认了输,给了汪宗儿十两银子。”
演员们都大笑起来,刘喜儿笑道:“这个汪宗儿还真是个趣才,闻女人嘴巴,隔远点看,就像是亲嘴儿啊。”
徐吉财又说:“他还有故事呢,都是真事。我再讲一个,有一回,一个农民老伯伯,挑一担大粪,要过一个小河儿,小河儿上是个独木桥,挑粪走独木桥是很难走的,老人有些犹豫。汪宗儿过路看到了,就装好心人,说:老伯伯,你挑担大粪怎么能过独木桥?弄不好会掉到水里去的,你把大粪放下,我一桶一桶帮你抬过去。老人信了汪宗儿,于是汪宗儿帮老人用扁担抬大粪,抬了一桶过去了,汪宗儿弃了扁担就走,走了几步,老人说:年轻人,你还要帮我抬另一桶啊。汪宗儿转过身来说:你这个人怎么人心不知足呢?我帮你抬了一桶,还要我帮你抬另一桶?那一桶你自个儿想办法啊。说后,汪宗儿走了。老人摇了摇头,凝望着汪宗儿的背影,老人一脸的无奈。”
徐吉财说后,演员们又是一阵大笑,吴志军笑道:“这个汪宗儿,怎么这么会捉弄人?那老人为难了,一桶粪在小河儿这边,一桶粪在小河儿那边。他怎么办?”
没有人讲笑话故事了,方红梅忽然提议,她说:“我们猜谜语好不好?我先说一个谜语大家猜:十条田埂八条沟,条条田埂瓦盖头。你们猜猜看,是什么?”
沉默一会,刘文说:“猜不出,你提示一下。”
方红梅笑着伸了伸双手,春水马上明白了,说:“哦,我知道了,你的谜底就是双手,十个手指好比是十条田埂,手指甲就像瓦盖着头。”
“对的。谜底就是双手。”方红梅笑道。
赵健也说了个谜语,他说:“我说个谜语:
生在娘家,青枝绿叶;
嫁到婆家,黄脸消瘦。
不提还罢,提起泪如雨下。”
一阵沉默,没人猜出,吴志军说:“你还是提示一下,打一什么东西?”
赵健笑说:“这东西家家都有,你们可以问一下厨房的李师傅和李姐是什么东西。”
徐吉财说:“哦,那就是刷锅的刷帚啰。”
赵健笑道:“对,谜底就是刷帚。你们想,刷帚是竹子做的,刷帚在娘家是竹子,是不是青枝绿叶?做成刷帚后,是不是黄脸消瘦?放在锅里,锅里有水,不提起来还罢,提起来是不是水淋淋的,像是泪如雨下?”
大家都笑道,是的,是刷帚。
吴志军说:“我出个字谜,你们猜是什么字?
一点点上天,
乌云盖两边,
左腿绞右腿,
缝中一扁担。”
春水马上笑道:“是个安字。”
吴志军说:“春水哥,你怎么这么快就猜出来了?”
春水笑说:“这谜语我读小学时候就听别人说过,那时候就知道是个安字呀。”
徐吉财说:“我也说个字谜:神一半,仙一半。”
春水马上笑说:“那是个伸字嘛。”
徐吉财笑说:“是的,是个伸字。”
春水说:“我也说个谜语:
遇强宁碎也不弯,
只遇温柔心便软,
热情高温烂熟后,
任你喜欢任你餐。”
沉默一会,赵健问:“是不是吃的东西?”
春水说:“是的,是吃的东西。”
赵健说:“那就是挂面。”
春水笑道:“是的,谜底就是挂面。”
妍萍笑道:“我也出个谜语,这个谜语是我小时候,我妈给我说的:
酒杯大的梗,
簸箕大的叶,
看着长,看着结,
结的白果吃不得。”
吴志军问:“打一什么东西呢?”
妍萍笑道:“这是以前的东西,现在应该没有了。以前,好多家里都有这东西,我没看到过,我妈说,以前我家里也有。”
徐吉财说:“这东西我小时候看到过,我看到的时候,我才五岁。我家里也有,我奶奶用过。这个谜底就是纺车。”
妍萍笑说:“是的,谜底是纺车。”
刘文也说:“我说个谜语:
城里来的货,
一手提两个,
酒杯大的眼,
针都穿不过。”
吴志军笑道:“这个谜语我早就知道,小时候听老人说的,谜底就是眼镜儿。”
刘文笑说:“是的,谜底是眼镜儿。”
下午五点钟时候,才哥和李姐回来了。到五点半钟,剧团的晚饭熟了,大家都去吃晚饭。外面的雨还是一直没停,到了傍晚七点钟,又下起了中雨,也没有人来买戏票,演员们都没去化妆,赵团长通知,今晚不演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