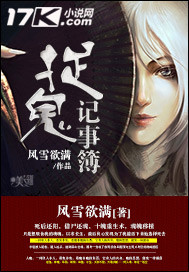第二天早上,在用过早饭后,高岩和司徒允像两个尽职的保镖一般,左拥右护地送凌洁去学校上课。
“这个……”望着像两尊金刚似的站在自己左右、一路引来无数回头率的人高马大的家伙,凌洁一脸的不自在,怯生生地问道,“表哥,司徒大哥,就算你们要保护我,也不用打扮成这样吧?”
说完,她瞄了瞄高岩和司徒允身上一模一样的草绿色迷彩服、宽大皮带、黑色高邦登山靴以及黑色登山包,有点哭笑不得。
“这个是这样的,”高岩尴尬地搔了搔脑袋,解释道,“等一下送你到学校后,我们俩想去爬山运动一下,所以才会打扮成这个样子。”
话虽如此,但实际上高岩在心中哀叹不已:天哪!他一定是发神经了,才会听从司徒允的怂恿,穿上了他从寒赋那里买来的这身所谓的“驱鬼装备”!
但他又无法否认的是,自从昨天后半夜见识了《鬼话连篇》的潜在的力量后,其实他内心深处也对寒赋的这套“装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既然《鬼话连篇》真的能驱鬼,那么寒赋卖给他们的这些肯定也不是水货!
毕竟等一下他们要去的可是白衣女鬼的老巢,要是没有一定的驱鬼装备做后盾,那不是去送命吗?
但现在面对凌洁想笑又不敢笑的神情,面对路上行人不断投射过来的或惊诧或好笑的目光,他真的很想现在就将这身惹人注目的装束给换下来。
与高岩截然相反的是,一旁的司徒允对自己的这身打扮颇为自得,并心安理得地将周围男性路人投来的目光全部定性为“羡慕嫉妒恨”,将女性路人的瞩目则归纳为“崇拜敬仰爱”。
在自得的同时,他还时不时地从衣兜里摸出一面小镜子放在面前照一照,发现镜子中自己的脑门上除了一个昨天被高岩用应急灯砸出来的包之外并无异常,多少感到了一些安心。
说来也诡异,昨天后半夜还清晰地印在他脑门上的那道青紫色手爪印在接触到今天的第一缕晨曦后就自动烟消云散了。亏他昨天后半夜为此还担心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重新入睡,唯恐这吓人的东西会像洗不掉的印章一样一直盖在他脑袋上,怎么也挥之不去!
不知不觉间,三个人踏着温暖的晨光和柔和的潮声走到了秦珊家门口。
清晨淡淡的朝阳打在秦珊家破旧的平屋上,却丝毫没有给这座房子带来一丝的光彩,反而令它灰色的墙面显得更加斑驳沧桑。
“珊珊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去上班?”望着紧闭的院门,凌洁轻声说道。
“今天又不是周末,珊珊为什么不上班吗?”司徒允奇怪地问道。说话的同时,他又在照镜子,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举动在不知情的旁人眼里看起来是多么的自恋,甚至可以说是变态!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渡船乘务员跟我们医生一样,又没有固定的休息日——就算是周末,也有人要坐船的,所以肯定是大家轮着休息的。哎,我说你能不能别臭美、老照镜子了?”见两个骑着自行车路过的男人纷纷朝司徒允投来受不了的神情,高岩忍无可忍,一把夺过了他手中的镜子。
“谁臭美了,我这不是不放心吗?快把镜子还给我!”司徒允正想从高岩那里将镜子抢回来,却听凌洁奇怪地问道,“不放心什么?”
回头对上凌洁投向自己的怪怪的眼神,后知后觉的司徒允终于意识到自己刚才照镜子的行为已经让他无限地接近自恋狂、死变态之类的形象,不由得有些尴尬,只好随口胡扯道:“我就是不放心我昨天在厕所门上撞的这个包会不会继续变大。”
“原来是这样。”单纯的凌洁一下子就让他给糊弄了过去,如释重负的叹了口气。
正当他们打算继续前行时,秦珊家平房原本紧闭的院门突然“嘭”地一下开了。
“珊珊!”司徒允喜出望外,还没看清开门的究竟是谁,就忙不迭地朝着院门口喊道。
但很快,他就大失所望。因为从院门里面一阵风似的冲出来的并不是秦珊,而是一个面容晦暗、五官粗糙的中年男人!
“咦,这不是……”高岩刚想说这是秦珊的父亲,就见又有人飞快地从门里面追了出来,挥舞着双臂,朝中年男人尖声喊道:“爸,你不能拿走这些钱,这钱是要给妈买药的,你不能拿去赌!”
是秦珊!
今天的她穿了件黑色宽松线衫、黑色牛仔裤,一头长长的黑发散乱于脸颊两侧,衬得原本就不亮的肤色更是黯淡无光。不仅如此,她那双原本挺漂亮的丹凤眼此刻红红的,而且使劲地朝前瞪着,看上去有些吓人!
“滚远点!老子生了你,养了你,难道从你兜里拿点钱花都不行吗?”秦父扯着破锣般的嗓子又叫又骂,随即用力一甩胳膊,就轻而易举地将上来拉住他衣袖的秦珊扫到了一边。
“爸,我求你了,妈又犯病了,正等着……”秦珊不甘心,马上又冲了上去,拦住了父亲的去路,大叫道。
不过突然间,她瞥到了站在路边呆望着她的高岩、司徒允和凌洁,不由得怔了怔,因为急怒而变得越来越红的丹凤眼里闪过了无限的尴尬。
秦珊父亲乘着她发怔的这个当儿,飞快地溜到了一边,骑上了靠在院门口边上的一辆破自行车,一溜烟地跑了。
秦珊见状,顾不得高岩他们以及路上其他行人都在朝她行注目礼,撒腿就朝前追去,黑丝般的长发随着她的飞奔在她背后疯狂乱舞,愈加显得凌乱无比。
“爸,你不能把钱拿走!妈还等着买药啊!爸!”
最后那一声“爸”,秦珊几乎是拼尽了全身力气在嘶喊,听得高岩三人心头一震发颤。
然而,她那个所谓的“爸”却连丝毫想要回头的犹豫都没有出现过,更别说是停顿了,反而是加快了踩踏的速度,像奔命一般,骑车朝前狂驶而去。
但秦珊也跑得出奇的快,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就追到了自行车的后边,然后使劲地伸长胳膊,一把扯住了自行车的后座。
咣当!
秦珊父亲没想到女儿真的能追上,更没料到她会突然用力扯住车子,一下子就失去了重心,连人带车摔倒在了地上。
“活该!”司徒允见了,露出了一丝幸灾乐祸的笑容。
但很快,他的笑容凝固在了脸上。
因为秦父哼哼唧唧地从地上爬起来后,二话不说,抡起胳膊就甩了秦珊一个大巴掌,力道之大,打得秦珊就像个陀螺似的一下子就转了个圈,挨了打的右侧脸颊马上就像充了气似的肿了起来。
“这个混蛋!”司徒允发出一声怒吼,摩拳擦掌正想冲上去,却被凌洁一把拖住了胳膊,低声道,“别过去!”
“为什么?”这下别说是司徒允,就连高岩也很是不解地望着她。
“因为珊珊个性很要强,从来就不喜欢别人干涉她家里的事。还有她父亲根本就是个没事都能找出事来的超级无赖,你们要是现在从过去,只怕会乱上添乱的!”凌洁像是哀求一般,小声说道,“所以就让珊珊自己处理这件事情吧!”
“死丫头,再敢管老子的闲事,老子马上就拿菜刀剁了家里那个药罐子婆娘!”秦父吊着一对三角眼,咧着一口黄牙,挥舞着拳头咆哮的样子,活像是一条面目可憎的恶犬!
秦珊不知是被他的那一巴掌打懵了,还是被他最后那一句威胁给惊吓到了,呆立在原地,一声不吭,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再度爬上了已经扶起来的自行车上,双脚一踩脚踏板,骂骂咧咧的离开了。
“终于走了。”看来凌洁也很怕秦珊的父亲,见他离开,像是在水中憋了很久的气似的,大喘了一口气,然后才朝秦珊的方向跑了过去。
高岩和司徒允也紧随其后。
“珊珊,你没事吧?”走到秦珊身边的凌洁伸出手,轻轻地碰了碰她的胳膊。
一直注视着父亲离开的方向、背对着三人的秦珊机械似地回过头,冷冷地扫了站在她身后的三人一眼。
高岩、司徒允、凌洁顿时被她的样子给吓到了。
这时的秦珊,脸色铁青,五官扭曲,一双丹凤眼里没有泪水,却缠满了如红色蛛网般的可怕血丝,眼神又冷又硬,带着前所未见的阴郁,恍然刚从地狱爬上来的恶鬼,哪里还寻得到半点之前那副温柔和顺的样子?
“珊珊……”凌洁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陌生的秦珊,不由得有些害怕。
高岩和司徒允也看得也是一阵心惊肉跳,根本就不敢冒然开口。
“杀了他!”秦珊紧抿的嘴唇里突然迸出了这么一句话。
“什么?”高岩惊讶地皱起眉头——她要杀死谁?不会是……
秦珊的目光冷冷地射向道路远方已经变成一个移动的黑色小点的父亲的背影,声音冷得没有一丝温度:“总有一天,我要杀了他!”
凌洁听了,害怕地用手捂住了自己嘴巴,这才没有让惊叫声破喉而出。
高岩和司徒允也被这女孩此刻的阴郁给震惊到了,面面相觑,根本就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秦珊没有理会三人的惊愕,转身,头也不回地朝自己家的方向走去。
一阵海风吹拂而过,扬起了她满背的黑发。
浓密的黑丝随风狂舞,恍若一道瞬间绽开的黑色羽翼,充满了不祥的意味!
高岩正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令人不安的一幕,忽而间却感受到了一道如冰锥般阴冷犀利的目光。
他马上抬头而望,刚好看了那道隐匿于破旧平房院门缝隙中的黑色人影——一个被黑衣、黑发包裹、脸色却苍白如纸的干瘦中年女人!
秦珊的母亲,一个活着的人,却给高岩一种犹如早已死去的游尸般的阴森压抑感,以至于他的心头难以抑制地浮现出了“她真的是一个活人吗”这样的疑惑,怎么也挥之不去。
嘭!
当破旧的院门再度合上,当秦珊黑色的背影和秦母僵尸般的身躯悉数被这座沉郁的平房吞噬时,高岩紧绷的神经这才稍稍放松下来。
当他回头再看凌洁和司徒允,发现这两人也如同两个不小心搁浅后重回河流的鱼在不停地喘气,这才意识到,刚才来自于秦珊、来自于这个奇怪家庭的压抑感并非只是他一个人的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