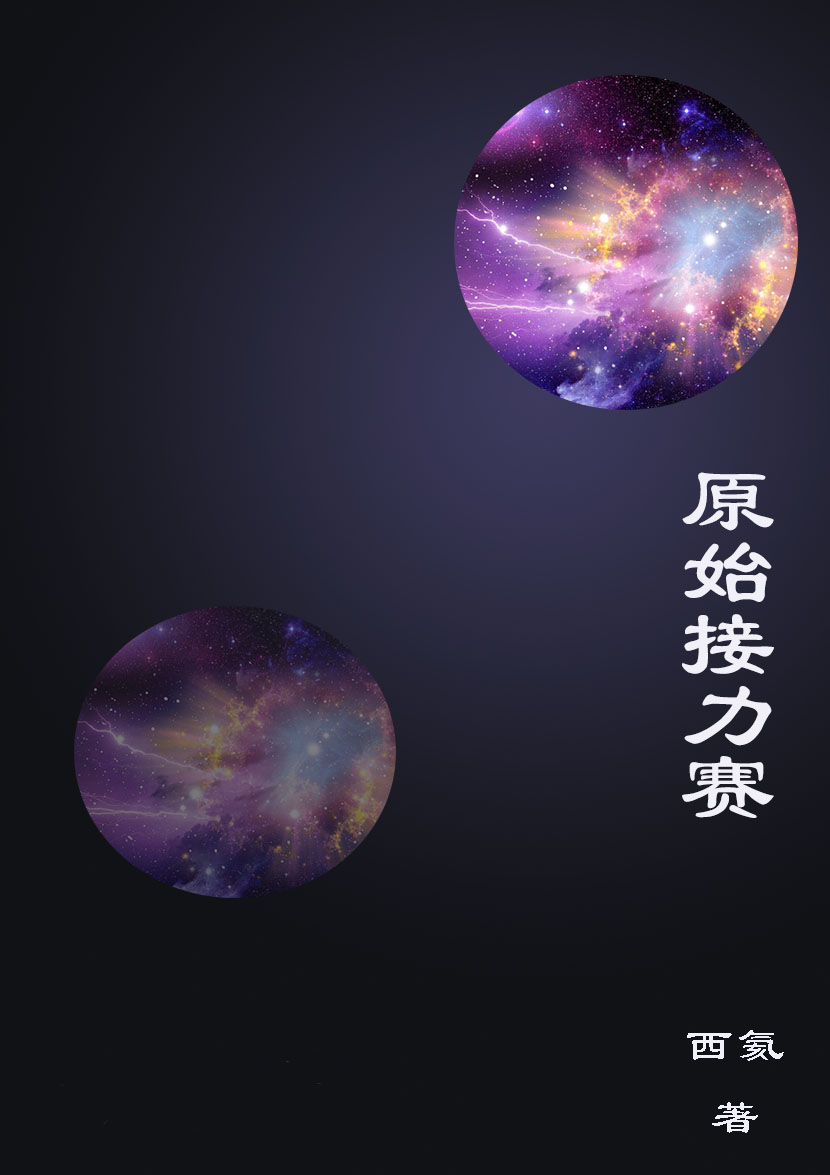驾校入口就在前方,苏立打灯、减速,慢慢滑到大门口,但是自动感应门却没有应声开启。怎么回事?坏了还是停电了?田野解开安全带,准备下车查看。
对面来了一辆车,灯光雪亮,丝毫没有远光灯转换近光灯的意思,不仅如此,车把大路半边都占了,行进之间似乎还有些歪斜,那车突然加速朝这边冲过来。
苏立觉得这一幕有些熟悉,十年前的场景又重回大脑,整个脑海仿佛被几十盏探照灯无死角照亮,全身突然一阵僵硬,在这一片强光里,一辆车向她冲来,躲无可躲,避无可避,只能被轰然撞击。
一声巨响,车身右后侧被来车的右车头撞击,车身剧烈抖动的时候,苏立看到田野伸过来一只手揽住她的头,厚实的肩膀替她卸去了大部分力道。
“苏苏,苏苏,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田野焦急地问,捧着她的脸左右看有没有伤口流血。苏立回答:“我没事。”尽管她脑袋撞得有些发蒙,却并没有受伤,田野松了一口气。
反倒是田野,因为已经解开了安全带,又伸手去捞苏立,整个胸膛重重地撞在前面,脑袋磕在车内镜上擦破了额头,此时正有鲜血顺眼角往下流。
不等田野暴躁,对面车里的人却把脑袋从车里伸出来破口大骂:“你他妈瞎,瞎了吗?挡了大、大爷的道儿知道不?不会开车,上、上什么路?”
田野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回击的人,一声不吭地下了车,一步跨到那辆车前,一拳锤在降到一半的玻璃窗上,车窗玻璃应声碎裂,一个胖头鱼一样的男人瞪着小眼睛坐在里面,他探手进去抓住那人的衣领,老鹰抓小鸡一样将胖头鱼从破裂的车窗拖出来,扔在地上,冷声说:“你再说一遍。”
那人杀猪一样嚎叫:“你这个土匪!撞人啦!打人啦!杀人啦!”田野一个碗大的拳头呼在他脸上,喊叫声戛然而止,他捂住可能已经麻木了的脸,惊恐地往四周看了看,才发现白惨惨的一条路几乎没人,叫也白叫,打肯定是打不过,跑又能往哪儿跑呢,这哑巴亏算是吃定了。
田野看了看车标,BMW,开得起这车的人,家底应该也不差,抽了抽鼻子,不怀好意地咧嘴笑了:“好小子,酒驾啊,怪不得开足了圆灯不走直线呢!”他摸一把头上的血,黏糊糊的抹到对方那张肥油脸上,掏出电话在胖头鱼眼前晃,咧着嘴笑得如同一尊凶神:“你把我朋友吓到了,把我头撞破了,说吧,是要私了,还是我报警送你进去蹲几年?”
地上的哥们冷风吹得一激灵,满肚子酒气吓成汗水湿透了胸背,人瞬间清醒了不少,立马怂了:“哥,哥,别报警,我错了错了,我赔我赔。”他一屁股爬起来,从车里拽出手提包,把里面的手机、卡片、现金,一股脑掏出来捧给田野。田野从里面捡出身份证和名片,举在哭丧着脸的胖头鱼旁边拍照留存,划拉两下现金,估计也就几千块,一把揪下胖头鱼脖子上的金链子,胖头鱼很识趣地把手指上的翡翠戒指也撸下来给他。
这时候苏立也下车来了,站在车边没动,不干涉这边的处理,田野却不想在她面前匪气十足,速战速决,教训教训这小子就算了吧。
田野蹲在他面前说:“我也不讹你,先就这么多,万一不够我这车修理费,我再找你报销。”他扇着胖头鱼那一叠钱拍拍他的脸:“记住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赶紧找人来给你代驾。还有,做个文明人,别动不动就张口喷粪。”胖头鱼点头如捣蒜,田野挥挥手:“滚蛋。”胖头鱼赶紧连滚带爬地滚蛋了。
田野手动打开了驾校感应门,把车开到工位上停好,摊了摊手无奈地说:“明儿又得修车,损失大了。”苏立笑:“你刚不是讹了人家不少。”田野耸耸肩,这种仗着有两个臭钱就螃蟹举爪横着走的人,切他一刀算是轻的。
他把翡翠戒指给她看:“我也不懂这个,你是宝石她亲妈,给看看,能换两个菜钱?”苏立搭眼一瞟:“成色不错,黑市三两万吧,拿人家这个干嘛?看这人估计有点头脸,别惹上什么人。”
“管他什么头脸,做错事就要付出代价!”田野脸上突然闪现一丝狠色。
苏立叹口气,大概美好人生被掐断导致内心的愤恨,以及这些年的不如意,让他增添了狠厉,不再是那个阳光开朗善良仗义的少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和观念,别人无权指指点点。
苏立指指他的头:“哪有医药箱?给你处理一下伤口。”田野翻箱倒柜地在一堆工具里找了一阵,拉出一个护理包来。伤口不大,已经不流血了,也不怎么疼,但他就愿意听苏苏安排。苏立取出大棉球蘸满了碘酒清洗伤口,倒了点消炎的白药粉末在棉花上,涂到伤口位置,再拆开一个创可贴妥帖地包上。
田野像个乖孩子,一动不动让她忙活,完事了开玩笑说:“挺熟练啊,你离护理专业只差一套护士服。”
苏立一边收拾小药箱一边答:“以前常给自己换药、处理伤口,久病成医。”田野默然不语,苏立发现他心疼的眼神,有些不自然地转开了脸,轻松地说:“可惜你这伤口浅了点,不然还能给你缝两针,扎个蝴蝶结。”田野抱着脑袋,像看怪物一样害怕地看着她。苏立轻笑。
突然灯光闪了两下,彻底灭了。田野无奈地说:“这一片电力保障老出问题,晚上动不动就停电。”
他摁亮手机灯,引着苏立走到场子里,果然附近这一片都是漆黑,远处倒是有雾蒙蒙的霓虹。
夜空意外地晴朗,能看到繁星点点、皎月莹白,田野爬上一辆越野车头,把手伸给苏立:“上来。”他们坐在引擎盖上,背靠挡风玻璃,仰面看遥远稀疏的星斗。从很远的地方吹来的风,经过城市高楼大厦的过滤,已经失去了海的咸湿,只剩微微的凉意。
“你还记得吗,很多很多年前,我们曾经这样躺在山里人家的屋顶上,那时候的星星,很大很亮,远比现在像样得多。”
怎么会不记得呢,只是人被生活推着走,那些遥不可及的往事,都放在最深最深的心底了,时间太久,往事薄成一张蜘蛛网一样虚,甚至怀疑是否真实存在过,或者只是曾经做过的一个梦。苏立默不作声,以前的很多东西,都比现在像样得多,星星,糕点,夏夜,汗水,青春,爱情。是以前太单纯美好,还是一路走着把这些丢掉了?谁知道呢,每个人都在不可逆转地长大,也不管你接不接得住生活抛来的任何东西。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对我说过,天上的星星,跟地上的人是对应的,天上星动,下面的人就跟着发生变化,星星滑落,就是有人死去了。”田野遥望着星空,分辨着星座,月光落在他挺直的鼻梁上。小时候只觉得神奇,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大手,如同下棋一样轻轻地拨动着星座的位置,于是人间就跟着悄悄地变幻。
也许,他的家庭,苏苏的家庭,也是被一只大手拨乱了棋盘,于是相爱的人,一个朝南,一个朝北,远远地出走了,怎么都找不到了。生活从一条阳光大道,一个急转弯拐到了一片山野崎岖、荆棘密布的荒野,他非常不甘心,但那又怎样呢,他连叫屈都找不到地方,只能一步一趟地往前踩处一条路。
在他已经接受现实的时刻,生活又给他打了一束光,他的苏苏就站在那光源里,只是她已不再是白衣胜雪、长发飘飘、眉目星河的少女。“我叫苏立,站立的立。”眼前短发干练、眼神清冷的女子,是苏苏又不是苏苏,是历经岁月淬炼后性质大变的苏苏,是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一步一步站立起来的苏苏,那些眉间眼角的冷漠,那些果决生冷的举止,都只不过是她谋生的技能和自保的铠甲。
可是这样的苏苏,同样对他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只是,那又怎样呢?他只能备受煎熬,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合适的距离。他的青春,永远定格在19岁的夏天。
他从小聪颖,但不是个认真读书的人,跟苏苏在一起后,才变得勤奋起来——父亲和老师说得对,苏苏是一个真正的淑女,温柔、活泼、上进、努力,这样的女孩子一定会拥有光明灿烂的未来,如果自己连个大学都考不上,粪桶怎么配得上明月呢?乐队固然有一些收入,田野也执着地喜欢音乐,但是如果音乐不能养活自己和爱的人,那就只能先放一放。有了这样的认识,田野认真地重新规划了未来,决定复读一年,一个是可以全力冲刺高考,另一个原因是复读能多和苏苏做一年校友,他有信心苦读一年,和苏苏一起商量尽量考在同一个城市……
生活很快兜头给了这个天真的年轻人一顿胖揍。父亲重伤住院,自己被当成嫌疑犯关押审问,几个月后出来,他与大学校园无缘,失去了女友的所有消息,父亲身体和脑子基本毁了,生活像是被洗劫过一样混乱糟糕。他的自尊和责任,不允许自己接受身边亲友长久资助,只能一边照顾父亲,一边四处打工,抽空苦读自考。
最难的时候,一天要打三份工,早上到酒吧做清洁服务,两个饭点时间段到附近饭馆当服务生、送外卖,晚上跟着不同的乐队到地下场或者酒吧演出,直到深夜回到家,父亲在钟点阿姨的照顾下吃过了饭,浑身冒汗地躺在床上,手边能扔的东西全在地上乱七八糟躺着,铁骨铮铮锄奸铲恶的老爷子,裤裆里屎尿横流,嘴里呜噜呜噜地发着脾气,一双因为伤痛而歪斜的眼睛里滚出豆大的泪水……能怎么办呢?田野耐下心来,给父亲擦洗干净,家里重新收拾整齐,累得快瘫在地上,天也亮了,该上班了。那两年,几乎是只要给钱的活儿,他都接。
现在的生活,比起那时候来,已经好很多,父亲的情况相对稳定,待在养护院里随时有人照看,比跟着自己强多了,驾校的薪资和酒吧的收入够维持生活,偶尔也会去朋友的健身房当当教练,兴起就跟着乐队去演出,图个欢喜;遇到组织严密的赛车,也会参加,图个赌资。
如果非得说有什么不满足的,就是一直耿耿于怀的苏苏。
可是现在苏苏就在眼前,那又怎样呢?自己的条件摆在这儿,养护院里还躺着个流哈喇子的老父亲,他依然是土根树皮烂泥巴,苏苏依然是白天鹅、是仙女下凡,他们之间的鸿沟一直在,且一直在拉宽,以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青春无敌热爱万岁,现在却是成年人了。
他打定了主意,只能这样,远一些地看一看她,就满足吧。
苏立不知他脑海里心念电转想了那么多,手枕在后脑勺下,一双长腿曲着,梦幻一般地说:“我们都长大了,那些美好的时光,永远都回不去了。”星星还是那些星星,月亮亘古未变,太阳也总是照常升起,只是这人间,每天都上演着跌宕起伏、悲欢离合,时光带走了身体里的一些东西,又多了一些别的,每一天都如常,每一天又都不一样,人在这漫漫长河里,何其渺小。
“苏苏,那些珍贵,一直在心底就好,我们都要努力生活,才不辜负吃过的那些苦。我们不需要回去,我们就像现在,像朋友一样,各自忙碌,偶尔聊天。”田野转过头,看着苏苏黑漆漆的眼睛,认真地说。
苏立点点头。心与心在熙熙攘攘的人世间,偶尔无风无浪安稳愉悦地靠近停泊片刻,足够鼓起勇气继续杀敌。
“你不爱笑了,苏苏。”
是的,她不爱笑了,因为受伤的缘故,左边脸多次手术也没有完全复原,部分肌肉坏死,一笑就会牵拉着整张脸,不但丑,且时刻提醒着自己那些疼痛清醒的时刻。
田野伸出一只颤抖的手,苏立看着那只大手缓慢地伸过来,心跳有一些乱。她没有躲,那粗糙厚实而又温热有力的手掌,轻轻地覆在她曾受伤的左边脸。他叹息地说:“苏苏,你要多笑笑,你笑起来,真好看。一直都那么好看。”
苏立闻言一愣,脸上慢慢地绽开一朵笑靥,清澈的月光下,如同凌波的水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