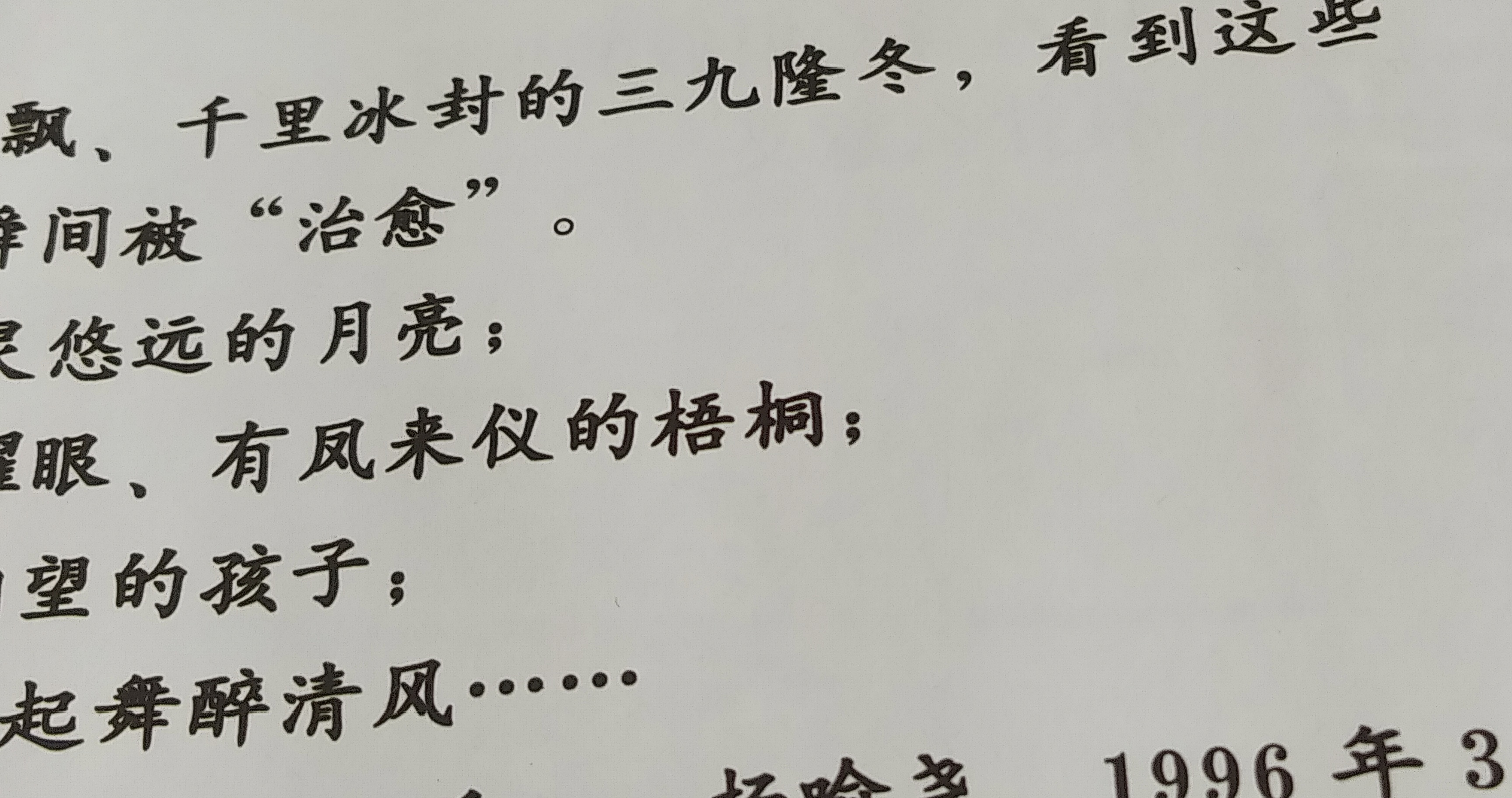十六七岁的暗恋是什么样子的呢?
像被摇晃过的易拉罐,被人猝不及防的打开,砰然而起的气泡黏在手心,似乎怎么也除不尽。
将来的某一天想起,记不清那罐汽水是什么口味,大都是一样的感觉——心酸又乏味。
我是芸芸众生中很普通的一个人,而我自以为这一生最不普通的时候,是在那样一个缺乏勇气的年纪,和江谦做了同桌。
他从隔壁班转过来的那天,是金秋十月风凉,是百步桂花香,前一晚熬了夜的我迷迷糊糊得看见讲台上的他逆着光站的笔直。
他望过来的目光清浅,漫不经心地开口说:“我叫江谦,多多关照。”
上天悲悯世人,于是让江谦这样熠熠发光的天生骄子做了我的同桌。
在我的记忆里,他身上永远有一股股淡淡的花香,十月的金桂,二月的杏花,五月的海棠……
他每次临着我坐下,我总是下意识的紧张,生怕哪里没表现好在他面前出糗,可是江谦总以为我是害怕跟他说话,偶尔会笑我“傻乎乎的。”
我张了张嘴想反驳,可是我们之间并不熟捻的关系让我犹豫之后选择不去搭话,只能一个人回想他嘴角上扬时候的恣意年少。
然后,我可以偷偷笑很久。
真奇怪,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目光开始追随他所在的每一处地方。
学校让年级优秀学生代表讲话,在毒辣似火的盛夏,纵使他的校服袖子挽到了小臂处,还是流了许多汗,讲话介绍,我手中一直握着的冰水已经变得发热,他从台上走下来,那瓶水被我伸出去又收回来,低下头的瞬间他从我的身边擦肩而过……
江谦站在我的身后,阳光从我脸旁掠过,投下一片暗影,我听见他清冷带笑的嗓音从背后传来:“谢谢同桌的水。”
如果心跳有声音,那一刻,大概已经震耳欲聋。
朋友笑着打趣我脸怎么那么红,是太阳照的吧,总之不是因为我身后的那位少年。
学校的芳华道,是我和江谦都会经过的回家之路,不过我从来没跟他同行过。
那条路一年四季开满花,更迭不休,永无交汇。
他每次离校总要晚好几分钟,他的人缘太好,好兄弟分布在年级不同的班,成群结队的说说笑笑从校门出来,外面已经是霓虹灯照,人声鼎沸。
而我假装和他碰见,中间隔了五分钟。
是我独自在校门外等他的那五分钟。
手心湿漉漉的汗出卖了我的紧张,踟蹰不前的我连“好巧啊江谦”这样一句简单的话都不知道如何说起,却是他也看见了我,笑着跟我打招呼:
“好巧啊同桌,你也在这。”
我忙点头,忍住心里突然涌起的开心满足,克制地对他笑:“是啊,好巧。”
校门外晚风总是悠悠的吹,我们之间除了客套的几句话,便没有了下文。
我看着他和朋友们勾肩搭背地朝路的尽头走去,昏黄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的好长好长,江谦的背影依旧是那么好看,可惜他没有回头,没有看见我从一至终望他的目光。
高三学习节奏紧张,换了座位,换了老师,但好像一直没有改变的,是他身上随四季而发的花香,是校外偶遇的时刻,是他站在走廊被风吹的鼓起的校服,装满我所有心动。
很多事犹如天气,慢慢热或渐渐冷,等到惊悟,又过了一季。
蝉鸣不止的那个夏日过去了,我炽热的爱恋却不知何时落幕,但我想阳光穿过了树叶的空隙到达五六年之后,仍心动如初。
毕业的时候,他已经被保送,那天匆匆来了学校,转眼又要匆匆离开。
我站在班级门口,看着他收拾东西,一瞬间胸口处的苦涩压的人难受,我叫了他的名字,他抬头疑惑的表情让我很想笑:
“江谦,祝你毕业快乐。”
他没说话,等出教室的时候,站在我的旁边看着天边铺陈开的晚霞,很轻很轻地拍了拍我的肩:“你也是,毕业快乐。”
走廊上的少年离我远去,留下的,只有我从未言说的碎满一地的暗恋。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江谦的呢?
说不清了,也许是比在教室里更早见到他的那一次,他在街上当志愿者,白白净净又不染世俗的模样;
也许是校学生会检查卫生,空荡荡的教室只有我一个人,他拦下扣分的同学,对我说了句:“没有下次”
……
也许只是他突然闯进我的生活,来的太过惊艳太过惹眼。
这从来不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暗恋,只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
后来,江谦出了国,很多年的同学会都没有来过。
在酒席之间听到关于他的消息越来越少,而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去寻找他的联系方式,别人问起,该怎么掩盖我不从容的窘迫。
即使那么久过去,我还是没能忘掉他。
一九年冬天,他终于风尘仆仆的赶了回来,推开门的时候,迎进风雪,也迎进他的身影。
我埋头喝酒,在灯光杯影中红了眼眶。
出了餐馆,白雪飘窗,鸣笛声响。
他站在路灯下跟别人说话,我好像乘坐时光机,回到了高二那一年。
只是,他好像瘦了,头发也变长了,背影也陌生到让我觉得见他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情。
这一次,他大概感受到我的注视,回过头开口叫我的名字,我就笑了,就像是刚刚放学,只是在校园门口等他五分钟而已。
我曾经最大的心愿就是,他能回头看见我.
哪怕相隔好几年,也终于如愿。
这世界有那么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在泪水里浸湿过的长夜,常让我想啊想出神。
暗恋是什么呢?
是江谦的名字,是我这悠长命运中的相遇又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