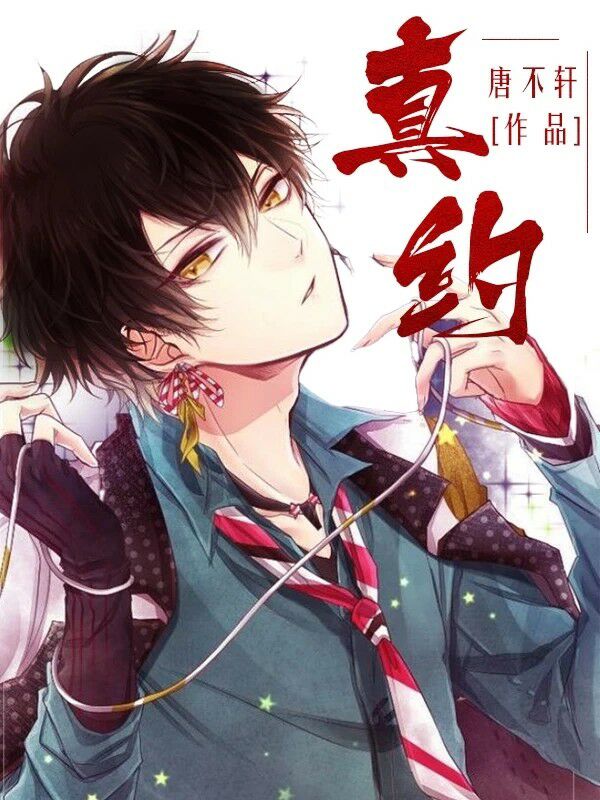整整持续了一个礼拜的收割时间,那一片金黄的颜色才一点一点地被收进了家里的谷库,此间田间地头上到处都堆着一丛丛枯黄的稻草,青蛙最喜欢的就是隐藏在稻草下面,范晓月最热衷做的事就是挪开稻草满田野捉从里面跑出的青蛙,范皊这边在忙着将捆好的稻草一担一担地挑回家,那一边弟弟范晓星小小的身子则坐在田埂边玩着泥巴,水田里范母一边拿着农具洒秧苗,一边大声训斥范晓月的偷懒打滑,范晓月撅撅嘴,将手中提起的稻草放下,慢吞吞地走到范皊旁边挑起旁边那一担更小点的稻草。
夏日里只要水田有水,刚发芽的谷种长势特快,一个礼拜后便是绿油油一片秧苗,农民便要趁刚洒下谷种的当口将田里的花生收完,再犁好田耕好地以备能够及时插秧。清晨天光刚亮范母便将两个女孩叫醒去田地里拔花生。清晨整个村庄安静地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远处有鸡鸣犬吠之声,随着太阳早早地出来,闷热的暑气也悄悄地开始由地表往上升。
等她们来到地里时,别的田地上已经有比她们起的更早的庄户。范皊一一和她们打过招呼便和妺妺开始低头用手拔花生苗,前日下过几场雨,枝叶上到处都挂着晶莹剔透的露珠,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土地松散,倒也不用费多大的力气,轻轻松松就拔了出来。
也不知拔了多久,范晓月有些受不住,周围一丝风也没有了,她抬头看了看已经升得老高的太阳,抹了一把额间的汗水,开始偷懒耍滑起来。她东张西望地四处瞄了瞄,这会儿别的人家大多数已经收工回家吃早饭,田地里除了她们姐妺两个已经看不见别的人影。只见她突然中蹲了下去,在一片绿油油的花生地里慢慢地挪向另一块别人家的地里。在别人家的地里东翻西找,不一会儿胸前的衣服兜住了一包东西,依旧蹲在田地里一摇一摆地来到范皊身前。
“姐,你看。”范晓月将衣服打开,拿出两个钵盂大的香瓜递了一个给范皊。
“哪里的?”
范晓月指了指旁边的田地:“金秀嬢嬢家的,前两天我就瞄好了。”
“这样偷摘人家的瓜会不会不太好?”
范晓月将香瓜用袖子擦了擦,张口就咬,眼皮一掀地看着范皊:“我们以前偷的还少吗?”
范皊被这话一噎,一时竟然无言以对。以前村里每家每户都喜欢另辟出几块地用来栽种瓜果蔬菜,那时地里肥料下得足,结出的果子又大又甜,却也因此引来了不少偷瓜贼,经常将瓜苗踩死,未成熟的果子摘了扔的到处都是,后来乡亲们便想出将瓜种洒在了花生地里,与花生一并种在一起,一则碧绿花生苗可以用来为瓜果遮阴,二则不易被偷瓜贼发现。母亲也会将种子洒在花生地里,不知是她下的肥料不足还是花生苗挡了瓜秧的雨露,那些果子长势甚小歪劣,那时因没得吃,两姐妺经常偷偷干起偷人瓜果的勾当。
“以前不是小,不懂事嘛。”范皊这话说的言之凿凿却明显有点底气不足。
“姐,我怎么发现你现在学习成绩上去了,连傻气也一同提上去了?”
范晓月怼起人来的时候甚少嘴下留情过,范皊懒得与她争辨,将花生苗抱到一堆,用稻草绑成的绳索捆绑在一起,一根竹杆往中间一穿,挑起花生就往家去。范晓月掮起锄头,一手拿起地里间范皊没吃的甜瓜,连忙跟在后面:“你不吃,我带回去给晓星吃。”
院门口就闻到了一股饭香味。范晓月在院里刚放下农具,就一留烟跑去?房里嚷嚷着饿了,要吃饭。范晓星在厨房门口的洋井里使劲地摇着井把,井里的水随着他的力气断断续续地从井口涌出流入下面的水桶里,范母在厨房里一边炒着菜,一边大声嚷嚷地说一些鼓励范晓星的话语。范皊在旁边拿着脸盆,舀了一勺桶里的水洗漱,范晓星看见后立即大喊大闹着不让范皊舀里面他抽出来的水。
“怎么了怎么了?”范母连忙出来,只见范晓星一脸恼羞成怒,胸腔起伏不定地瞪着范皊,手中的瓢勺正滴着水。范皊一动不动地站在另一边,浑身上下早已经湿透,水珠正顺着头发和衣服不断往下滴着水渍。她眼眶泛红,心中着实大恼,拿起旁边的另一把瓢勺舀上水就想往范晓星身上泼去。
范母还没来得及训斥二人,就见范晓星连忙将手中的瓢勺砸向范皊,只听得闷声一响,范皊只觉脑袋一痛,随即又是瓢勺砸在地面上的声音。那瓢勺本是晒干蔳瓜做的,特别坚硬,幸亏范晓星才四岁,力气不是很大。范皊捂着头蹲在地上,只觉得脑袋一边都是嗡嗡地痛,她忍住想要哭的冲动,却无法忍住眼眶里的泪水。
范母大声训斥着范晓星,赶忙上前揉开范皊的头发,查看脑袋被砸的重不重,好在只是起了个大包。涂点消炎药应该问题不大。
“范晓星,你就是我们家的小霸王,就知道窝里横。”范晓月站在厨房门口边上骂道:“从小到大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为你让步。”
范晓星起先是因范母的训斥在哭,这下听了越发哭的大声,范母被这一团乱麻搅得有些心烦意乱,又连忙训斥了范晓月的挑事,又从屋里拿出一瓶药水倒在伤口上为范皊揉擦一翻。范皊当天下午便要返校上课,几人又快速地吃过早饭, 去田里忙活了一上午,下午范皊才返回学校。
由于晚上要上晚自习,学生大多数都是下午才返校的,广播站舒缓而轻慢的音乐早已充满整个校园,只有即将升入初三年级的几个班级提前上课,一时间人数倒比平常少了一半多,校园也失去了以往的喧嚣与热闹。范皊进入大门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升旗台上正有一伙人围观在一起,时不时不断爆发出一阵笑声。
“看,皮球又在那处罚学生呢?”旁边和她同时入校门的两个男生正指着那边笑嘻嘻。
“皮球”是学校的教导处主任,带的是上届的再毕业班,他原名叫陈学礼,个子很矮,肥脸颈缩的,经常戴着一副透明眼镜,配上他那又圆又大的啤酒肚,显得异常滑稽。彼时有学生唤他为河豚,又因河豚不是常见之物,不知道的根本就不明白河豚为何物,后来为了通俗易懂大家便开始唤他为“皮球。”
陈学礼是一个严谨治学而又一本正经的老教师,只有当他在背后听到有学生偷偷唤他“皮球”的时候,他则会变成一副非常不正经的另类模样。而他的不正经则会表现在揪着那个学生的耳朵让他站在红旗下,面朝着教学楼那边不停地大声喊上一节课的“皮球”。
学生们当然不会按他所说的去喊,学生其实是非常识趣的一类群体,他们知道哪些可以说,哪些打死都不能开口的。见学生久久都闭上嘴巴,陈学礼则会换上另一副不正经的模样,让那学生学猴一样去爬旗杆,旗杆又细又滑的,往往学生爬了大半天还是在原地一两米处上窜下跳的,而他像一个站在旁边的耍猴人。当然大多数学生是情愿在操场上从早上站到晚上也不情愿自己像只猴一样任别人观摩。这天下午则遇到了那么一只“猴精”。
那“猴精”爬到大概有四五米处的时候,陈学礼在旗台下则会忍不住和其它学生一齐鼓掌喝彩,他让那学生下来并笑眯眯问道:“看来阁下还是有两把刷子,不知可会翻跟头?”那学生听了毫不掩饰自己的才能,当下起起把式,翻了好几个跟头后,拍了拍手上的灰尘,依然直挺挺地站立不倒。陈学礼不住点头赞叹,将那学生又引至学校一旁的公告栏旁边,令他在那里一直倒立。
夏日天气炎热,虽上有树荫遮蔽,那学生倒立不过两分钟,早已汗湿颊背,豆大的汗珠不住地流向颈项脸颊再顺着发尾滴落在地。陈学礼却是皮笑肉不笑地一面询问他的名字班级,一面和他闲谈起这一身本事是如何练来的。那学生一面咬牙回答,一面双手奋力地支撑着身体。在坚持到五分钟之后身体不受控制地开始摇摆起来。
“哎哎哎,稳住了,稳住了。”陈学礼连忙焦急唤道。
“对对,要稳住,别倒下来。”旁边围着一伙看热闹的同学。
那学生脸色明显已经涨的通红,陈学礼的声音在他耳边开始有些听得不大清晰,他只觉得耳鸣脑涨,两眼开始变得昏花,终于撑到大概十分钟左右,他开始向陈学礼求饶:“陈老师,对不起,我错了。”
陈学礼不为所动,依然和他讨论着倒立的好处,并问他是否知道倒立是五禽戏中猴戏的一种。那学生以前只是好玩学的这些,哪里知道什么猴戏,此刻却很肯定自己就是一只被耍弄的猴子,终于在承受了自己身体的极限之后,从墙上面倒了下来回正身体后瘫坐靠在墙上大口喘着粗气,一副任君宰割的模样。陈学礼抬起手腕看了看表道:“才几分钟你就受不了了?”
那学生生无可恋气喘嘘嘘地看了陈学礼一眼,此刻的陈学礼又恢复了他平日严肃而一本正经的模样,他眼神冷厉地盯着他。
范皊只远远地瞥了一眼,只是一眼也令她觉得这样的场景熟悉的有些令她心惊。不远处传来学生求饶的声音:“陈老师,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您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原谅?你说怎么原谅你?”
“要杀要剐随便处置?只求给个痛快。”
“那你说是杀了你还是剐了你?我给你选择。”
……
范皊从旁边的走道穿过,略微低着头看脚下的路,尽量不让那些声音影响到自己的心神。广播站播放的是一首她最喜欢的英文歌曲《斯卡布罗集市》,莎拉布莱蔓空灵天籁般的嗓音将曲调的凄美婉转,韵律的悠远演唱的淋漓尽致。歌曲唱到一半就中断了,接着传来广播站播音员的声音:下面请欣赏二年级六班的严英英同学为二年级二班的范皊同学点的一首《朋友》。
范皊顿了顿脚下的步子,有一瞬间她觉得自己肯定是听错了,她有些茫然无措地看了看四周。周围只有三三两两和她一齐进教室的同学。很快回荡在校园里的是一个女歌手声情并茂的歌声,不知道是不是碟片老旧的原因,范皊并没有听得很清楚里面的歌词,只听得旋律是欢快轻松的。
“嗨,范皊!”有人在身后拍了她一下。
范皊回头,面前出现的是朱紫琳一张笑靥如花的脸。
“你怎么变得这么黑?暑假挖煤去了?”朱紫琳一脸吃惊地看着皮肤有些黝黑的范皊。
“煤倒是没挖,天天享受着日光浴呢。”
“真的假的?改天也带我去”
范皊微笑着答应。朱紫琳面如银盘,唇红齿白的,一看就是家境较好,从小养尊处优惯了,她想像不出朱紫琳拿着一把禾刀,撩起两只裤脚,露着两截白花花的小腿站在水田里会是一副什么模样,会不会连头发也凌乱地粘上一些稻杆草叶,还有那白嫩嫩的胳膊细腿上被敷上一片片淤泥或者有一道道被稻草划伤的红痕?
朱紫琳哪知道范皊此刻在想像着她一副干农活的模样。大大咧咧地将手揽过她的肩头道:“严英英为你点的这首歌怎么样?好听吧,那可是我鼓励她为你倾情奉献的。”
“谢谢,这歌很好听。”
朱紫琳兴奋道:“我就说你是一个有品味的人嘛,那可是毛大姐唱的歌,就严丫头还一脸不乐意,叽叽歪歪说这歌老土。”
“你们今天没在一起?”
朱紫琳收了收脸上的笑容问道:“范皊,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不回严丫头的信吗?”
范皊微垂着视线道:“我只是代人过问一些事情,可能是人家觉得想问的问题已经有答案了吧。”
“那个人是你吗?”
范皊先是一愣,随即抬头凝视朱紫琳:“为什么你会这么认为?”
朱紫琳笑了笑,但那笑容却不达眼底:“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不是我。”范皊略思索了一下道:“信中已经写明了那是一个已故的人。”
“你以为你这样说我就会信吗?”朱紫琳道:“就算我信了你觉得严丫头会不知道吗?严丫头已经为自己想不起的这个朋友而自责不已,她让我告诉你明天下午放学后在学校背面的那片树林里约你见面想当面问清楚。”
范皊抿了抿唇,没有回答朱紫琳,而是快步地往教室走去。身后传来朱紫琳有些着急的声音:“范皊,你不回严丫头的信她已经很难过了,事情是你挑起的,你有义务给她一个合理的解释。”
坐在教室里,心绪有些烦躁,眼前的书怎么也看不进去,满脑子都是朱紫琳最后说的那句话,范皊草草收拾了一翻课桌上的书本后,拿出几本假期前在落庭那借的书去还,顺便再和大姑姑父他们打个招呼。教师宿舍楼处落庭的房门紧锁着,姑姑那边书房的门却开着,她进到里面,看见姑父正坐在向着门口的那一面沙发上,旁边是一个和自己一般大小的女孩正坐在实木沙发上,带着一副透明眼镜,留着一头细软的短发,也正打量着她这个突然闯进来的陌生人。
“姐……姐姐?”范皊的视线落在那个女孩身上,不大确定地叫了一声,又询问似地看了看坐在首坐上的姑父。她有些不确定眼前的女孩是不是表姐落琴,虽然很久没见过表姐,但眼前的人和她长得太像了,仔细看又不像是表姐。她除了脸颊两侧没有如表姐般两个的深深的酒窝,五官和表姐落琴长得简直太像了,但是眉眼间的神情又像极了表妺落庭不笑时的模样。
那女孩没有回答,扶了扶眼镜依旧抬头凝视着范皊,然后又看了看另一边的姑父,李田熙笑了笑,向她介绍道:“这是你大舅舅的大女儿,范皊,比你小一岁。”他又看向范皊:“你没有叫错,这也是你姐姐,明明。”
听到姑父这一番话范皊大概已经猜到了眼前这个叫明明的女孩应该就是大姑被抱养出去的二女儿。她有些羞涩地向她点了点头并唤了一声姐姐,明明也站了起来,她穿着一身白色的绣花连衣裙。中等个子,但身子纤细显得整个人比较单薄。向范皊打招呼:“你好,我叫罗招娣,小名叫明明。”
招娣,范皊有些意外她的名字,她对取这个名字的意义太熟悉不过了,她自己的外婆就叫招娣,旧社会有太多人家的女儿叫招娣,盼娣之类的,大多叫这个名字的女孩要么就是家里生了太多的女孩盼望着要生一个儿子,要么就是家里重男轻女思想极重。范皊曾听母亲说过大姑的这个二女儿,以前抱养的时候好像那户人家夫妻俩结婚好几年都没生到小孩,她抱过去一年之后才生了一个男孩的。范皊有些同情这个她第一次见面的表姐,不管如何在现代看来取这类名字的父母是简单粗暴的,多少带着点性别歧视色彩。书房里只有李田熙和罗招娣坐在那里闲聊,并未见大姑和表妺,听大姑说表姐落琴这个暑假去了实行并未回来。范皊和他们寒喧几句简单打过招呼后,将手中的书本放在李田熙身后的书柜里就回教室了。
毕业班的课程很紧凑,但是因为分尖子班和普通班要到九月初正式开学学校才会出通告,所以初二的学生暂时还是在各自班内学习复习初一初二的基础课程直到正式开学分班之后再学习初三的课程,复习的方式也基本上都是以考试为主,刚开始几天学生们为着能考个好分数还兴致盎然提笔奋写,然而面对每天几张几张的考试试卷,有些学生便开始有些吃不消,或许老师们也知道这种复习方式压力大了点,对于一些没做完作业的学生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了平时的考试,上课的时候老师会拿出初一初二的课本挑里面的重点难点再讲解一番。对于已经学过的内容,很多同学都表现出不大的兴趣,都是以一种懒散的态度面对。也有部分同学会借来初三年级的课本开启自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