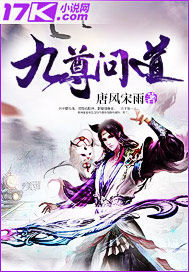范皊进教室时没有看见英语老师正从她身旁经过。她们的谈话全都钻进了英语老师的耳朵里,英语老师一言不发地看着范皊进教室。
一直以来褚晴丽在老师面前都是一个文文静静的三好学生,所以维护三好学生似乎成为了老师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情。而那天上英语课时,英语在讲解试卷的中途特意停了下来,特意表扬了褚晴丽这次的成绩只差一分仅次于第一名。他又往教室的某个方向望去过,讥讽地说道:“某些人本事没事,整天就知知道背后议人长短,妒忌心又强,有本事就比人家考的更好来,自己又没用,有什么资格说人家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
范皊惊惶地看着老师轻蔑的眼神,不,不止一双,而是全班几乎一半的同学都在看着她,大多数都是女生。她想不明白她只在几个女生面前说的一句话竟然会在第二天全班都知晓。那一刻她觉得她又回到了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她将头低的老下,故意用书本挡着,她不明白老师是怎么样看待她,以至于会如此地在课堂上羞辱自己,她全身微微颤抖着,像是一只鸵鸟,只想到要藏起自己的头颅,管它外面如何的翻天覆地都与她无关,她要逃避,只要能离开这里,做什么都好,还好褚晴丽没有看向她这边,不然她会真的无地自容。
可老师的那番话确确实实在她和褚晴丽之间横划了一条宽阔的河流。是的,褚晴丽是三好学生,而她范皊不是,甚至于她范皊的学习成绩在班下还是中下水平,范皊从来就不是一个喜欢将人的好差用成绩来区别,就像是一个人的品德与贫富差距没有关系一样,可她不懂得象牙塔之外的社会险恶,所有的一切美好其实都是用外在的事物所堆彻的。学生是属于象牙塔里的,而老师却是属于社会的,所以他们难免会带着社会的眼光来看待在象牙塔里的学生。
老师的那一翻话一度成为了她午夜恶梦中的一幕,她时常会做同一个梦,梦里她一个人走在一条狭窄的巷子里,周围是灰蒙蒙的一片,没有阳光,也没有风,是死一样的沉寂。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而身边到处都是胡同小巷,像一个巨大的迷宫,她迷路了,她在迷宫里漫无目的地走着,她心里很恐惧,她觉得她将会被吞噬在这里面,然后她又开始奋力地往前跑,打开一扇扇厚重的大门,又进入另一条条相同的巷子,她在雾一样的巷子里忙乱而无助地奔跑着,周围没有一个人,她看不见一样活着的事物,终于她跑累了,推开了巷子里面的一扇大门,那古老而厚重的大门吱呀地一声被她推开,然后她整个人便开始恐惧地抖了起来。那里面是一个祠堂,祠堂的神案上点着一对蜡烛,地面上是一堆早已被烧为灰白色的冥纸,那堆灰迹旁边却躺着一个人,而此时她的双腿却不由自主地往那个人走去,恐惧在一点一点地蚕食着她,突然间,她便惊醒过来,一头冷汗,全身酸痛,她捂着双眼在被窝里呜咽地哭起来。
从那以后范皊开始变得特别安静。她就像一个被遗弃的人,再也没有主动找过褚晴丽。她时常会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安静地翻看着书本。褚晴丽明显感觉到范皊似一夕之间就消瘦了。她经常能够看见她的眼睛下面时常会泛起一股乌青。可她明显感觉到在范皊身上似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有些后悔之前对范皊使小性子。那时她故意冷落她,对她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其实就是想要她难受,想让她后悔。她一直觉得真正的好朋友是风吹不烂,雨打不散的。
范皊真是笨,难道她看不出她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故意气她的。她不喜欢范皊和卜俐走的太近。自从卜俐开始喜欢做和事佬的时候她就越来越觉得卜俐跟她们不是一伙人。每次卜俐来找她们说话时褚晴丽就觉得浑身都不自在,她便找借口离开,可范皊却像个没事人一样根本就不知道她内心的小别扭。开始的时候范皊依然会傻呵呵地扯扯她的衣服,牵起她的手,而她却故意掉过头去,将手从她手中抽开,然后慢慢地远离她。甚至有时候她会将正和范皊说话的卜俐叫走,就是为了孤立范皊,好让她知道只有她褚晴丽才是她真正的朋友。后来慢慢地范皊终于不再和任何人说话,她的目的似乎达到了,可是范皊也没有再主动和她说过话。
这天褚晴丽依旧任凭班里其它的女生围在她身旁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没一会她便觉得没意思起来。然后她从她们口中得知那天英语老师课堂上说的某些人就是指范皊。褚晴丽震惊地看着斜斜地倚靠在教室后门边的那个人。范皊望着门口来来往往的学生在追逐打闹着,她觉得那一刻所有的热闹都不属于她,尽管她是站在人群之中的一份子,可是孤独的感觉却是那么地强烈地吞噬着她的内心。
这时身上的衣袖却被人轻轻地扯了扯,范皊微微侧过头,褚晴丽正担忧地看着她,她身边陪伴她的那些女生不在。尽管前一秒钟她们还在嘻嘻哈哈地说笑着。
“阿皊,你怎么了?是不高兴吗?”褚晴丽轻声问道。
“没有”她别过脸。
“对不起,我不知道上次课堂上老师说的那个人就是你,你别生我的气了好不好?都是我不好。”她可怜兮兮地看着她。
范皊只觉得眼中雾朦朦,她忙将眼中的泪水擦去:“我没怪你,这件事本就和你没关系。”
她不是没有想过褚晴丽知道她在背后这样说她时会是什么表情,但她有自信褚晴丽心里必定知道那是她的口是心非说出的气话。所以她并不担心别人将这话传到她耳中。可是她没想到老师会插足这件事情并在课堂上当众打她的脸面。她更不知道褚晴丽会后知后觉在这种情况下以这种方式知道。她只是突然觉得自己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褚晴丽。
褚晴丽此刻即悔又恨,要不是自己弄出那么多事情也不至于让两人产生那么多误会。她有些哀伤地伸手去抓范皊的衣服,就像许多次范皊哄她一样。范皊将头低了下去,她不想加重褚晴丽的思想包袱,于是擦干眼角的眼泪转移话题:“我没事,就是最近我爸住院了,家里凑不够钱给他治病。”
“你爸爸怎么了?生什么病了?”褚晴丽紧紧地握住她的手。
“说是结石,这两天要手术。”范皊哽咽道,想到前段时间中午回家吃午饭时,父亲那痛苦的声音和额头上那大滴大滴往下落的汗水,她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痛的死去活来,自己在旁边干着急。后来去了医院,母亲回来说要准备一万块钱的手术费用,可是家里养活她们三姐弟读书已经很吃力了,哪里来的钱凑那个手术费?
对于贫穷母亲似乎已经变得麻木,那天奶奶当着范皊三姐弟的面责怪母亲不肯去问亲戚朋友借钱时,她只想大声地告诉她不是妈妈不肯去借,而是根本就借不到,当年她小学三年级留级的时候,母亲曾牵着她走到所有的亲戚家里问他们借三百块钱交学费,结果走了一天,没有一个人愿意借给她们。那是她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人情冷暖。而奶奶那个时候明明有钱,却情愿借给别人也不愿意先拿出来给自己的亲孙女交一下学费,因为她怕妈妈不会还她的钱。最后却是远在别处的大姑听说了主动送过钱来替她交了学费。而现在面对的却是比那个时候三百多块钱学费还要多几倍的一万多块钱的手术费,叫那个早已经被生活磨励的沧桑又悲凉的女人去问何人借呢?
当褚晴丽拿着二百多块钱交到范皊手中的时候,范皊有些吃惊,二百多块钱对于那个时候的她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褚晴丽怕伤到她敏感的自尊,小心翼翼地说道:“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希望能够帮到你,哪怕一点点也好。”
范皊苦笑道:“这些怕是你所有的零花钱和压岁钱吧。”
“我爸每个星期都会给我零用钱的。”是的,褚晴丽家里是开工厂的,家里的经济条件比一般人家里要好上许多,尤其是她妈妈远在湖北上班,而父亲带着她和一个哥哥在家乡,给她的零花钱从来都是比别的同学多了很多。
范皊没有接受褚晴丽的钱,但她的心意却足足地填满了她的内心,她将钱整齐地叠好放入褚晴丽的口袋里:“不用了,钱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真的吗?”
范皊苦涩地点了点头。因为就在昨天当 母亲只是面目麻木地跟奶奶说:“我没有办法,我借不到钱。”
奶奶闻言直大骂她狠心,竟然想看着父亲痛死。母亲不再说话,默默地看了她们三姐弟一眼,他们一个个面黄饥廋,个子小小的,单薄的衣裤上到处都是破烂的补丁,她推了门出去。
奶奶见她如此狠心决情地走开,嘴里直叨骂个不停,最终自己被逼的咬了咬牙,打了个电话给两个姑姑,叫她们先垫出手术费,到以后再让父亲和母亲凑够还给她们。而经此事之后,奶奶逢人便说母亲狠心,要不是她去帮忙借钱,就只能看见父亲死去。
她从来不怀疑是褚晴丽填补了她童年时所缺失的所有的温情与快乐。只是那温情,来得快,去的也快,而留下的却是两个人默默地在回忆里舔舐着各自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