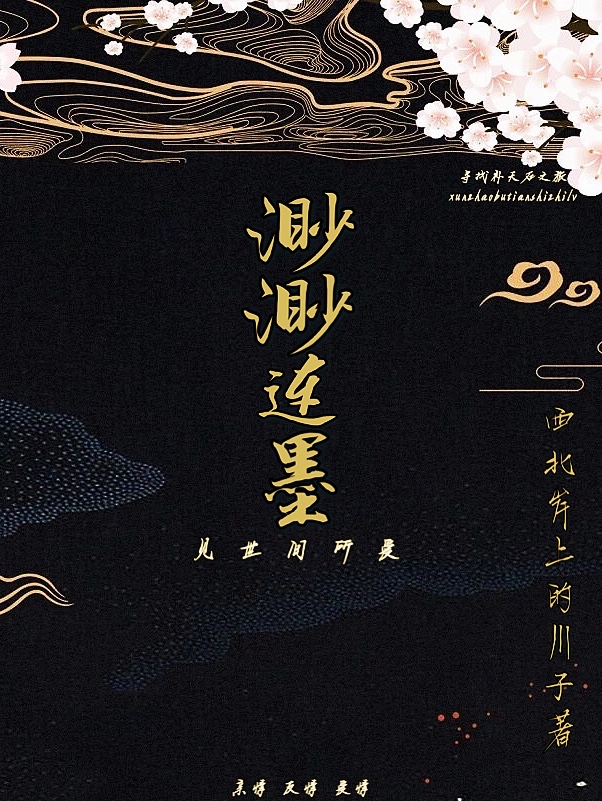很显然,对于我在杏花林中遇到沈凌这一点,阿桃很是振奋。
我领着沈凌走回系马车之处时,阿桃的瞳仁里瞬间开满了桃花:“公子!”旋即又相当自豪地拍了拍胸脯,朝我扮了个鬼脸:“姑娘你看,听我的在这杏林看一看花没错吧!若是我们径直赶路,就要绕过这片杏林,也就遇不到公子了呢!”
我但笑不语,翻身到了沈凌的马上。阿桃不解地看着我:“姑娘是让公子和我一起乘马车?这这这,有些不妥吧!”
我递过一个白眼:“阿桃,你家公子累了。”
她这又回过头去打量沈凌,半晌,惊叫了一声:“呀,公子的脸色怎么差成了这样?”
这一声惊叫让我有些歉疚,却同时让我觉得颇为欢喜,如雪杏林中他倦着身子,看我的目光却是不舍得失了半分精神:“我一听到老爷子来了离城,便知道会有些麻烦事儿。”
“所以呢?你不眠不休的赶了过来?”
“哪有什么所以?我急急忙忙地过来,不过是因为,你在这里。”
介于阿桃不会驾车,局面仍是有些难以调整,于是无法,只得退回离城之内。沈凌却不打算回沈府,只随意指了一家客栈,便歇下了。
我体贴他连日的疲累,第二日叫店里小二烧好了热水,又将他包袱里面的衣物理了个整齐。
理到最后,理出了一只白玉雕做的小兔子。这兔子明显是我在柏城时雕的那一只,好像又抛过光了,在熹微晨光之下,莹润顺滑。
舒心一笑,将小兔子放回原处。门被敲了敲,阿桃的声音清脆:“姑娘,今晨我们还要离开么?”
我打开房门,做了个噤声的动作:“公子还在隔壁房睡着,声音小些。”
她领会了我的意思,走进屋来,半掩了门,看向我铺开来的衣物。待看到白色里衣之时,脸便腾地红了:“姑娘……姑娘怎么可以,咳咳,怎么可以随着翻动公子的东西呢?”
我被她一惊一乍的反应唬住:“为什么不能呢?”
“这个……”她脸上的红晕越发浓重:“男女大防,不可置之不理。”
我愣了愣,走回衣服旁边叠了起来:“修仙人不拘小节。”
阿桃:“……”
手中衣服颜色从浅紫到深紫不等,都散着淡淡杜若香。思及此前并未在沈凌的衣裳上面闻到过这样的味道,我问阿桃:“他很喜欢杜若?”
阿桃大概是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所谓的“他”是指哪一位,过了许久才接口道:“你是说公子?”
我点点头,手中动作并不落下分毫。阿桃点点头,又摇了摇头:“大抵因为夫人爱杜若清雅,总给公子的衣裳上薰上这样的味道,公子习惯了罢。”
想了想,又补充道:“去年恰是夫人离世十年,公子将所有带香的衣裳都换下去了。”
脑海里便现出初见那日沈凌白衣清俊面目舒朗,当时还奇怪,觉得白衣并不该是可以随意套上身的颜色,却不想,还有这样的一段渊源。
十年。难怪他从不提起自己的从前。
阿桃忽又不怀好意地将我的包袱提到了桌上:“姑娘姑娘,你给公子绣的香囊可有带在身上?趁着现在把它送给公子,岂不正好?”
我忙忙捂住那包袱:“又胡闹!你且先下去将早点买过来再说。”
“长安准备了东西要送我?”沈凌径自推了门进来,脸上倦色虽是仍未消减,精神却比昨日好了很多。
阿桃识趣地退下身去,我把包袱提到一边,点了点头,将别在腰间的香囊递了出去。
沈凌盯着香囊打量了一阵,悠悠说道:“这是绣的杜若?”
我点点头,却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于是把头埋着,去看那茶盏上的瓷画。
“这杜若绣得有些不成比例。”沈凌将那小小的香囊几番翻转看了许久,终于开口点评:“叶子太宽了些,看着不那么协调。”
我站起身来,伸手示意他将香囊交还于我,他却盈盈一笑:“不协调有不协调的美感,我就是这么的口味独特。”
我:“……”
对于接下来的行程我很是迷茫,不知道该将马车驾往何处。沈凌见我牵了马车过来,拍了拍驾车白马的头:“昨儿个神思恍惚,脑袋没怎么想事情。长安,你不是说过你不会骑马吗?”
我自豪笑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更何况我们别了月余?”
又被他探询的眼光看得不自在,我挥了挥手:“好吧,我从前不骑马,只是因为骑术不精。”
墟空之境中隐有晃动,我敛了眉间笑意看向沈凌:“林月见醒了。”
“林月见?”
我点点头:“她现在是一只形魅,有了自己的形体。前些日子因为得罪了一位仙人,便被抓了去。”
“那现在呢?”
“现在,”我拉着他的手又绕回屋中,小心翼翼打开墟空之境,缩小版的林月见正在里面漫无目的地游荡。
墟空之境是得道之人心中的一方虚拟空间,无限大,却也无限小。我早已将墟空之境给密封了。是以,我和沈凌能看见境中的种种状况,境中人物却无法感知镜外的世界。
“长安是决定了要管这件事?”沈凌问道。
我摇了摇头,无精打采回道:“你看我先前管过的两桩事,哪一桩圆满了?”
“世间事从来就没有圆满的,长安不用自责。”
我却略过他的好心宽慰,埋头看那林月见在墟空之境中茫然无措地行走,抬眸问他:“你可知道苏以归在哪儿?”
他思量许久,悠悠一声叹:“据闻二十九年前林月见被判斩首示众,是苏以归敛了她的尸骨。自那以后,便再也没了这诗书大家的消息了。”
“而今他虽垂垂老矣,却仍旧活着。”我将墟空之境收起,重放回体内:“他现在还有一个身份,清凉寺主持,弥远。”
沈凌果然没有料到我会告诉他这样的一个事实,难得地怔了许久,再开口却又释然:“难怪师父在诗文书法上造诣那么高,却又对往事只字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