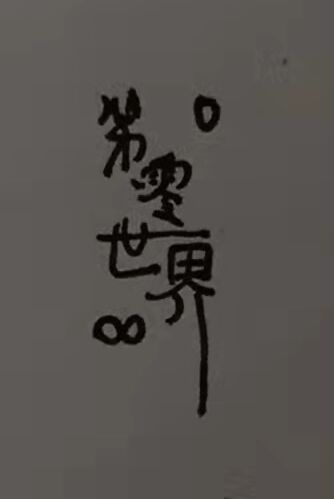他想将她拥在怀里,从此再不放开。
许是李君同的脚步声在寂寥雨夜里出奇的响亮,林月见缓缓偏头过来。只是在林月见将目光投向后方之时,李君同已被人拉到了小巷的转角处。
“你做什么?!”李君同忿忿然擦了擦脸上的雨水,将雨伞往怀里收了收。雨夜无星无月,他看不清来人面容:“府衙边上也敢造次,你胆子还真不小!”
那人却将伞向李君同那边偏了偏,抬起脸来,压低声音道:“是我,苏以归。”
“你已经来了。”李君同松了紧握着雨伞的手,伞尖向下,缓缓滴着水:“你早就到了这儿,却看着她这样作践自己?!”
苏以归做了个噤声的动作:“我们换个地方谈谈。”
“换地方?”李君同定定看着苏以归在夜色里模糊不明的脸,忽然低声笑了起来:“你的意思是,我们去一方屋檐底下把酒言欢,任由月见在雨中淋着?”
“不然呢?”苏以归将身子凑近了些:“由着你给她送上伞然后她守着你的灵位过一辈子?或者,我从这门前将她强行带走然后她恨我一辈子?”
李君同眼中映着雨幕苍苍,正中是苏以归一本正经的脸庞。他轻挪脚步,走到小巷边上探出半个头,恰好看见林月见孱弱的身影在雨中自顾冷清:“有些时候我真挺讨厌你的。”
“我也一样。”苏以归回答:“若是她在这里跪上一整夜而你不出现,再怎么着也该死心了。你若是真为她好,便别让她对你念念不忘。”
李君同唇边笑容凄凉:“然后你再去带走她,又一次成为她的救赎?以归,你看这些事,就像注定一样。若是注定,又为什么要横生那么多枝节。假若她命定的人是你,当初你又如何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将她推到我身边?”
苏以归嘴边三四寸长的胡须被风吹得散乱,他动了动唇,却什么话也没能说出来。
“算了,只要你以后不要重蹈当初的覆辙……也别重蹈我的覆辙。”李君同愣愣倚在墙边,抬头望向黑漆漆的夜空,豆大的雨点打在脸上,刺刺的疼:“又不是夏天,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雨?”
苏以归却也松开手中的伞,雨水很快浸透了他的衣衫。他同样仰起头,夜空黑得像墨一样:“还记得当时你用举荐我入京作为娶月见的筹码,我当时答应了,因为我没得选。就像现在,你也没得选。苏家在这几年间已经慢慢振兴了,用不着我继续步步为营小心谨慎。”
“我负了她一次,不会负她第二次。”苏以归低下头来,看着李君同瘦弱的身子:“倒是你……你这病来得奇怪,真的没法子治么?”
见李君同不说话,苏以归捡起一旁的伞:“总之,你若是去了,我会挑一个合适的时机将真相说给她听。到时候,我会带她去看你。”
“多久以后?”李君同问。
“十年,二十年,确定她不会为你难过的时候。”苏以归静静地答。
李君同偏过头去,径直走向小巷中间。雨大,天黑,这巷子里没有灯,想来就算林月见回过头来,也看不见什么。
“你打算就这样淋一夜?”苏以归擎着伞问。
“我想再陪一陪她。”李君同声色喑哑,又提醒道:“你可不能像我这样发狂,一会儿你还得抱她回去,不能淋坏了。”
一夜风雨大作,淋淋漓漓淅淅沥沥,将柏城灰蒙蒙的天地冲洗得干干净净,却又带来隔夜的春寒。
李君同是在天亮之前便躲进了角落里,那个角落恰好能看见州刺史府前的一切,却是其他人难以寻找得到的。
清晨有昨夜的官差牵着马从州刺史府门前经过,看见仍在跪着的林月见,惊了一惊,四方打量了一番,又默然离去。
雨已经歇了,苏以归早先回去换了身干净衣裳,抱了前长袍回来。他绕过小巷,走到刺史府的石狮边上。
“师傅。”却是林月见呆滞的眼率先灵动起来,她转了转眼珠,许是太过虚弱,说话明显底气不足:“师傅,这就是你为月见择的良人。”
李君同缩在角落里一派落寞。他看见苏以归慢慢靠近林月见,慢慢地抱起她,朝着与他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去。而他只能从角落里站出来看着两个人的身影,渐行渐远。
有句诗怎么说来着?离恨恰如春草,渐行渐远还生。
自此以后,李君同再未见过林月见。相传他入京的第二年犯了大错触怒龙颜,被贬至西南小城泗洪。拔高踩低是人之常情,自此无人在意这位曾经风光无两的状元郎今时今日在何方。
泗洪离柏城隔着山高水远,要探一探消息也属为难。即便如此,李君同还是从自己一早便安排到苏府的人口中得知,林月见被张玉琬赶出了府。
他初听着消息时皱了眉:“苏以归没有阻拦?”
“拦了。”那人如实回答:“可是苏夫人用孩子和官位威胁苏大人,要苏大人在这些东西与林姑娘之间选一个……”
“混账!”隔着斗笠外飘着的层层黑纱,李君同原本俊俏的脸无尽沧桑:“那月见如今在何处?”
“林姑娘……林姑娘好像剃了头发出家了。”传信人扭扭捏捏:“只是林姑娘在那寺中制了桃花笺作请柬,顺水流下,落在柏城不少少年公子手里。”
“如此?”李君同的手紧握成拳,半晌,吩咐传信的人下去,扔开斗笠支着头冥想良久。
他仍旧觉得是自己的错,明明知道苏以归怯懦,却还是将她交到他手中。
这下可好,苏以归终是背弃了承诺,又一次辜负了她。
“月见。”李君同口中逸出轻轻浅浅的两个字。一行清泪缓缓流下,他自言自语道:“月见,你何必这样作践自己!”
他不懂林月见的所作所为是何意义,便是苦苦思考,也只觉得她可能是在报复,报复他和苏以归一而再再而三的抛弃。
其实他这样想也没什么错,只是忽略了林月见是个姑娘,而且还是个敏感的姑娘。这世上大多数敏感的姑娘一辈子什么事都不做就喜欢玩猜心游戏。你猜猜我猜猜,能猜出无数的故事事故来。
这些姑娘爱猜心,左不过是因为不敢相信别人说的是事实。而不相信的原因,不过是没有归属感。林月见亦如是。
我这样推断,乃是因为在柏城的那一夜,林月见黑衣黑发坐在我身旁:“爱不爱一个人是天命。琼落,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看,有没有人曾将我看作天命。”
多卑微的一个问。
“君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房门被推开,他的夫人快步走进屋内,脸上笑意盈盈。
李君同支着头,并不说话。李夫人见状缓了步子,走到李君同跟前,递出一封被拆开了的信。
“这是父亲在西疆打探消息时得到的。”见李君同仍旧不说话,她脸上的笑也浅了些,拿出信里的纸展开:“这是晋国的记载,你先看看。”
李君同回过神来,接过那张纸,纸张破旧,边角泛黄,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碎成渣似的。
“广清山。”李君同的眼里泛出异样的光芒:“那个修仙盛地?”
纸上记的是百年前的旧事,说晋国曾有一个人,二十五六岁时开始迅速衰老两年后已变为花甲老人。一日,这人上山种菜,救回一个白衣飘飘满身是血的少年。
这少年康复后赠了一粒丹丸给老人。老人服回,重新变为二十五六模样,之后像平常人一般终老一生。
那个白衣飘飘的少年,自称广清弟子。
“找了一年,终于还是有结果了!”李君同攥着纸张,紧抿的唇也不知是哭是笑:“我还有机会,我还能活,我还能去找她。”
他转过头,瞳孔里难得地映出李夫人袅娜的身影:“我还能去找她!”
李夫人笑了笑,一半欢喜一半忧愁地叹:“是啊,你还能去找她。”
其后种种一如李君同那日拦住我时在小木屋中所说,他用了一年方才在大陆的另一端寻到广清仙迹。只是广清山门重重仙障,哪是寻常人可以进得的?
兜转一番尚无结果,李夫人千里加急的书信中便写上了林月见摊上人命官司判了年后问斩的消息。
于是再顾不得什么广清什么病,李君同昼夜不休赶回柏城。自然,路上捡了卿尧,也是真的。
柏城菜市口仍是人来人往,斩过人头的地方血迹都被洗得干干净净。李君同双腿一软,跪了下去。
此时他鹤发鸡皮,一如六十岁的老儿,纵是人流涌动,也无人认出面前人便是两年前风流倜傥的状元刺史李君同。
卿尧提着铜炉过来,面上桃花面具精致优雅,他伸出纤长细腻骨节分明的一只手:“我到那寺庙里转了一圈,找到了个面具。”
见李君同仍然呆愣,卿尧低下头来,压低声音在李君同耳边说道:“我这里有一个办法能让她重生,只是代价有点儿大,你看……”
“什么代价?”李君同赶忙问道。
“你的命!”
“我的命?”李君同重复,片刻抬起头,坚定答道:“左右我活不了几时了,这条命不要也罢。”
“这么爽快?”卿尧轻巧笑道:“你不该害怕吗?我若真的会做那样的事,定然不是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