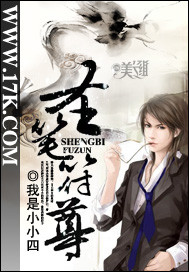李君同看着林月见飘忽不定的神色,忽然觉得有些害怕,像是许多年前府里添了小弟弟,自己想亲近,又担心那小弟弟活不过几日。
林月见将杯中桃花酿尽数饮下,朱唇微启,声调凉得惊人:“师傅从来不曾说过这般轻佻的话,月见听着,倒也觉得师傅勇气可嘉。可是师傅,如今已不是两年前了。就好比我从前很喜欢吃这一道水晶肴肉,现在却觉得它不如文山豆腐美味。”
“月见……”他还欲说些什么,话语却被林月见冷冷打断:“师傅,你缺席的这两年时光,已经让月见同以前不一样了。”
她就这样起身离去,转身片刻又停下步子,取下腰间镂了桃花的黑玉环放在桌面上,嘴角笑意半真半假:“师傅对月见算是恩重如山,若是有朝一日师傅遇上麻烦需要月见还报这份恩情,便差人将这黑玉环送上李府吧。”
李君同在实木雕花屏风后笑得眉眼温软。
夜空亮起繁星,落在城边潺潺的溪流之中,像是凭空开出的芙蓉花盏。李君同不远不近地跟在林月见身后,一声土气的衣裳再加上故意佝偻的身子,活像传奇里那些专为恶霸跟踪美人的小喽啰。
林月见回过头,在夜里笑得活泼:“你的步子怎么这么慢?”
李君同晃了晃,慢慢从阴影里出来,站直了身子走到林月见身边,痞痞的笑掩住发红的耳根:“这么快就被娘子发现了么?”又将自己先前换下的衣裳披在林月见肩上:“你可怪我?”
林月见摇头:“你都能这么大度地让我与他私下相见,我又怎能怪你偷听那三两句谈话。”
“又快到清秋节了。”林月见忽然转了话题:“清秋节的时候,我们去归元寺还愿吧?”
“还愿?”李君同皱起眉头:“我们何时在归元寺许过愿?”
“是我自己去的。”林月见面上亮起一丝羞色:“上月母亲唤我去归元寺求子,那时你在澧县看查民情,我便没有知会你。”
“我同你一起去。”李君同暖暖回答。
然而清秋节的时候,李君同并没能陪林月见上归元寺还愿。那一夜软语温存后不过三日,苏以归离开柏城,连绵秋雨飘零如丝。
若这雨只是应应苏以归的离情也就罢了。偏偏它一下不止,使得以柏城为中心的整个柏州在雨丝的看顾之下变成泥泞沼地。
原本盼望得一年好收成的柏州农民怨声载道,这埋怨堆积日久,慢慢就演化出了国君不仁使得天降奇灾之类的昏话。李君同身为一州刺史,自然要担负起一方的安宁。
李君同一连近两个月奔波于柏州的大小集镇山村,指挥减灾措施的同时还得注意稳住民心。躺着一个人自然是不够用的,于是夜下批阅公文上传下达也就成了常事儿。眼底日益浓重的黑眼圈儿使得李君同怎么看都是一副精神不济的模样,原本俊秀的脸庞也迅速瘦削下去,凸显出高高的鹳骨。
清秋节那一日,他已经二十余日不曾与林月见相见。澧县也有一座小小的归元寺,他抽着午休的时间换了便服赶去寺中对着高高厅堂中央的巨大镀金佛像一跪二拜三叩首,仿佛这样,他便与林月见同在。
临出门时,寺里的小沙弥将他拦下:“施主,寺中的东西都是开了光的,受佛祖庇佑,您要不要带些回家去?”
李君同本能的摇头,又看见小沙弥饥渴的眼神,于是扯出一个生硬的笑:“都有些什么?”
小沙弥见他进一步问了话,立即跑去搬了个小箩筐过来。箩筐里各种杂碎物品堆得凌乱,李君同随手翻了翻,翻出一条颜色还算鲜艳的同心结。且那结上,还恰恰有个“见”字。
于是他用三个铜缁换了那同心结。
楚国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传说:五百年前反了大庆建立天元国的藩王参日最爱为他那夫人绾发。而到参日揭竿而起的时候,他将王妃锁在冀东行宫之中,留下一个血红血红的同心结。寓意他要夺了天下,才肯归来见她。
李君同对着些野史段子向来是将信将疑,只是大众当中善良人居多,大家都爱把故事往美好的方面想。一来二去,当年的事实没人追究,倒是那一段烽火岁月中参日对方静秋的缱绻深情成了数百脸来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楚国还有个奇怪的传言,便是国君代代不长命。而参日在清楚知道这样的谗言的存在之时,仍旧不顾一切地想要爬上君王宝座,绝不该是一个方静秋可以决定的。
就好比遍布楚国大小集镇的归元寺,一定不只是因为寺内高僧云集能将佛法讲的通透无比。
李君同面上的憔悴之意一日胜过一日,就连他自己在洗漱是看见水中倒映着的憔悴面孔,都不太敢确定的说那人就是他自己。
好在一路追随的小属官数月如一日的精心调理。一月之后,柏州最艰难的时刻终于过去,李君同收拾大小零碎回家。路上遇见浑身上下挂满各种各样吉祥物的小道,那小道士原本只是匆走过李君同的身边,走了两步,又退回去:“施主请留步!”
李君同袖中红线猛地跳动起来,那小道士仰起头问他:“施主值不值得藩王参日的传说?”
他点了点头,有些不明所以:“藩王留下的传说有许多,不知道小师傅说的是哪一桩?”
小道士诡秘一笑,从自己身上拿出一个坠了“月”字玉珠的同心结:“传说参日急急起兵,乃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李君同猛地抬头,还没能问出什么话来。那小道士已经没了踪影:“天命这个东西可违抗不得,施主切记莫要大悲大喜,像参日一样把自己逼到悬崖边上,只能毫无章法地赌一把。施主,万世皆空,该放手时不能再强求。”
李君同忙忙掏出同心结,红色丝线之下坠着的玉珠变作了两颗。该放手时莫强求,那小道士说的话叫李君同觉得十分晦涩,正百思不得其解,脑袋忽然沉沉钝钝,一个趔趄便栽在了路边上。
何为虚妄,何为歉疚,何为放手,何为强求?
再次清醒过来的李君同并未被送回柏城,记得他恩情的几名老百姓将他带回了自己的家中。也就是说,直到现在,李君同还没有回过柏城。
大大小小的归元寺因着灾荒,并不能像从前一样拿出了足够的银钱去养活一干光吃饭不做事的小沙弥。于是柏州数座归元寺钟鼓长鸣,将寺中过多的弟子送出门外做游放僧。
归元寺暮鼓晨钟,在天色将将泛白之时开始长鸣,钟声低沉醇厚,从山上传到山脚,又扩及全城,使得一座城都在袅袅佛音之中兀自庄严。
李君同便是在这佛音之中把一切的前因后果理了个清楚。
铜镜摆在面前,他再也不能对这镜子里满面倦容略显苍老之态的人挤眉弄眼。甚至,便是他回到了柏城,还要装出一副冷面郎君的模样,从此与林月见天各一方。
一切不过因为他的苍老并非来自这数月的操劳,而是因为他的身体正以一种诡异的速度生长,迅速长大,又迅速老去,就像旧时神话传说里那些奇怪的幻术上了身一般。
他还有三年的时间。三年后,他的皮囊便会老去,从此再也撑不下任何灵魂。
他思来想去,在身子养得差不多完好的时候托人联系了一直在柏城附近晃悠的母亲。他看见她的第一句话,说的急切而肯定。他说:“母亲,我想要有一个孩儿,我想要同别的女子成亲。”
李母自然是万分诧异,一时明白不了半年前信誓旦旦说要与林月见相伴一生的儿子为何会突然改了主意。尽管,这主意让她觉得挺高兴。
事情变慢慢筹备了起来。从始至终,李君同都是在李母另买的别院里面居住,待到嘹亮而喜庆的唢呐身渐渐在柏城东北角想起,近冬的太阳暖暖的,刚好落在林月见描得精致华美的花了妆的面颊上。
她又一次穿戴得整齐漂亮,细致的妆容大红的衣裙,分明是美极,桃花眼却微微上挑,脸上挂的笑更是虚虚实实,一般轻浮一半真心:“原来李公子也会有这一天,终究是我看花了眼,还以为李公子会是个与众不同的人。”
李君同抿着唇,冬日的暖阳落在眼角,成就一派妖佻风骚:“终究我需要一个孩子来继承李家的香火,你做不到,我自然要让别人帮忙。”
“是么?”林月见笑中更掺一半真假:“那从前怎么没听你说过?我虽然一贯不喜欢小孩的闹腾,但也曾经告诉过你。为了你,我愿意养一个闹腾的小孩。”
“月见。”李君同无奈叹气:“你还不明白么?”他原本想问她,为何她看不见他月见苍老的容颜,为何她看不见他眼底的一片阴霾。可是开口,他也只能淡淡说一句:你还不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