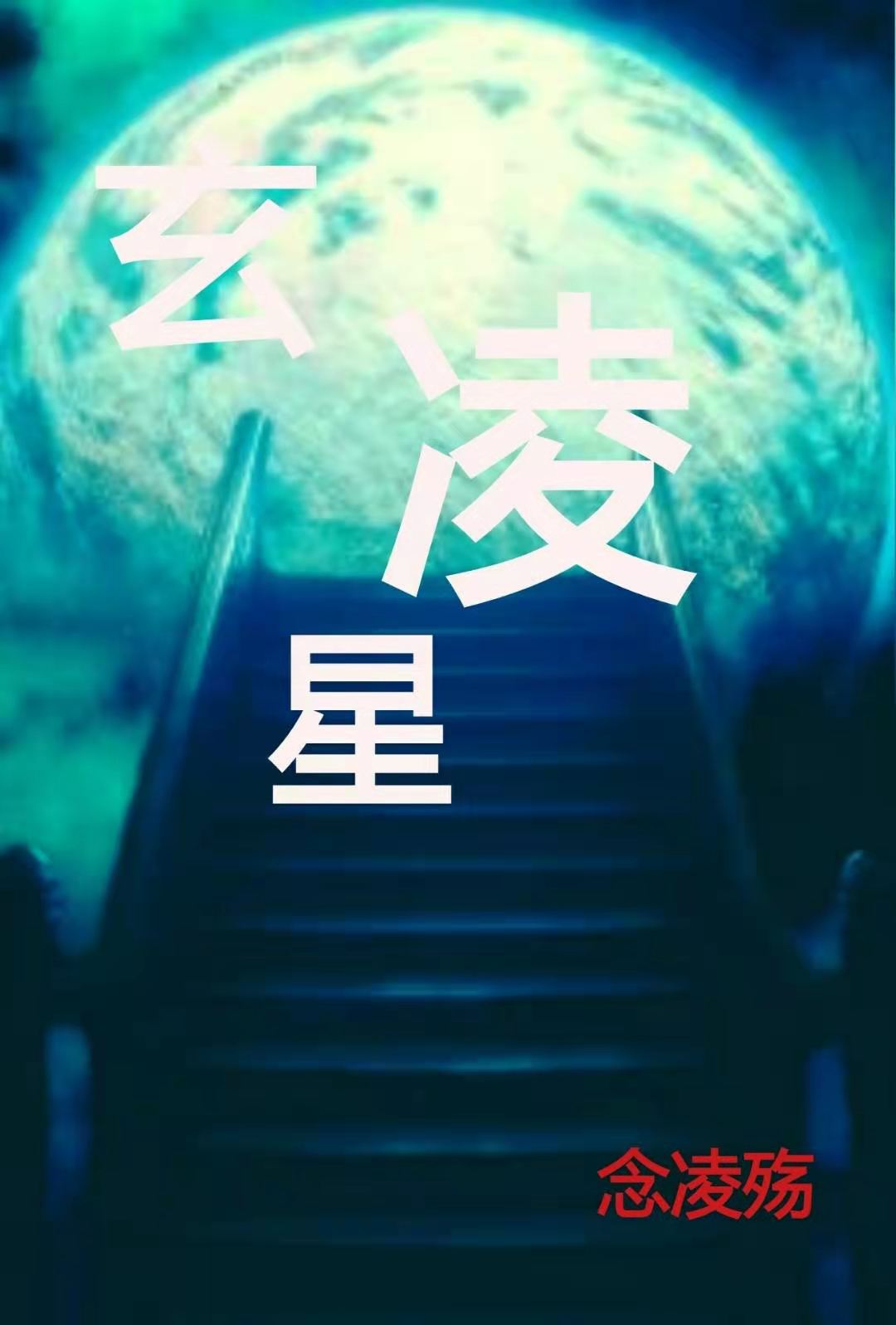牧区开始打草了,我在草原上过了第一个中秋节。
中秋节的前一天,矿山与嘎查搞了一个联欢。联欢的地点距离巴图的蒙古包很近,晾干了的草一捆一捆摆放在草场上,在黄黄一眼瞅不到边的牧场上,像长城上一个一个的方形的砖垛子。
这是我到草原第一次骑马。跨上了马后抓紧了缰绳,两脚插在脚蹬里,腿肚子紧紧夹在马肚子上,马受惊了一劲儿快跑。前蹄踏进了鼠洞,前腿突然卧倒在草原上,惊慌失措的我毫无准备,顺着惯性向前甩出老远,躺在草原上不省人事。
额日敦巴日喊来岱钦快去找哈斯其其格,他和几个牧民在身边一个劲的喊:“林矿,快醒醒,快醒醒!”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隐隐约约听到了哈斯其其格的声音:“醒过来没有?醒过来没有!”
岱钦和几个牧民把我的身子翻了过来,慢慢摆正放平,哈斯其其格从怀中掏出一个木碗扣在我头上,又在我的脚后跟下垫上一根胳膊粗的木棍,用锤子不重不轻的一下一下敲击着木棍,慢慢地把我震醒了。
我在宿舍里躺了5天,才能下床慢慢溜达。每天上午下午,让我摇晃十几次头,回想前段时间做过的事情。事情的经过和来龙去脉一清二楚,确信自己没有因脑震荡而留下后遗症。我十分感谢哈斯其其格用蒙古族传统的方法救了自己一命。
阿来夫在嘎查长面前告巴雅尔的状:他故意让我骑他那不听话的马,才会从马身上摔下来。
我摇着头为巴雅尔辩解:“可不能误解人家,我上马前,他给我说了4条注意事项:一条是上下马时,不要走马屁股的后面,免得被马后脚踢伤。第二条是上马和下马,要慢慢缩短缰绳,抓紧不要松手,避免马脱缰而跑。第三条是下马两脚先从脚蹬中拿出来再下马,左脚千万不要放在脚蹬里,防止马拖着人跑了。第四条是马受惊了,要抓住缰绳慢慢的收紧,不要大声叫喊,更不要跳下马,要长长的喊着吁……吁……的声音,马会逐渐停下来,两脚先从脚蹬中拿出来再下马,左脚千万不要放在脚蹬里,马不会拖着跑伤着人。”
巴雅尔高兴地笑着说:“就是嘛,林矿记得清楚呐,巴结林矿都巴结不上。”
20年前草场里有好多狼、黄羊、狐狸、老鹰和蛇,现在很少看到到这些动物。老鼠没有了天敌,繁殖就更快了。牧户拿着嘎查发放的灭鼠药,胡乱扔到草场里,有些鼠药毒性大,狐狸、老鹰和蛇吃了毒死的老鼠也死掉了。
巴图看到旱獭洞和鼠洞一片一片的,脸色忧伤地说:“好在腿和胳膊没有摔坏,是不幸中的万幸。我在草原生活了60多年,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鼠洞。”
岱钦看到巴图郁郁的脸色,想起了叔叔30多年前给自己和俄日敦达说的鹰和老鼠的故事:鹰带着老婆孩子到大树上要筑窝棚,老鼠仰着头对树上的鹰说,树根已经腐朽了,在这里安家不安全。鹰听不进老鼠的建议,窝棚建成后,雄鹰带来了食物,大树倒在了地上,老婆孩子都摔死了。雄鹰伤心的落泪了,口口声声地说:这是对高傲的惩罚。老鼠清楚树根的情况,恨自己没听话。老鼠跑出洞来回答:骄傲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我在地下打洞,树根坏掉了。
岱钦从故事里跑出来,说:“小时候闹不机密是啥意思。我说哥哥是大鹰,哥哥说我是老鼠,陶格斯扯着羔子的耳朵不说话。”他一会指向天,一会指向地:“毁坏草场的人,下场肯定会和大鹰一样。”
巴图想到了儿子,怕岱钦顺嘴说到了苏木,不高兴地说:“胡说些啥,这事不能怪罪那一个人,临近的苏木和嘎查又能好到哪里去?”
这几年盟里大的环境是推行工牧互补,组织了多次旗县苏木嘎查三级干部会。盟长说:要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减牛减羊更好地保护草原。,牧民要靠天吃饭,天旱牧民贫穷的例子太多了。干旱了,羊草五花草啥的不长了,牲畜多了,牧草少了,为填饱肚子把草根都啃出来了。要从根本上改变靠天吃饭的状况,引进了工业项目,才能促进牧民养草增收。在这样的背景下,有色黑色金属业、煤炭和石油才进了牧区。
巴雅尔指着煤矿的方向说:“把煤矿油田引进来,为啥不引进皮革加工厂?白条羊进了库房,羊皮多的去了,一张不到一块钱,白白扔掉了。”
嘎查长高声压过他的话:“脑瓜子是用来想事情的,有多少羊皮可以加工?羔子买完了,还有皮吗?总不能把加工厂建起来了,干2个月,闲10个月吧。”
巴雅尔盯住嘎查长说:“羊皮多的去了,皮革厂建成了,还愁别的旗县和盟市不来送羊皮!咋会停工10个月呐。不光油田煤矿有GDP,皮革厂也照样会有GDP的。有些人的眼光跑偏了,让煤矿油田之类的迷惑住了,认了个死理儿。企业不断的扩大,和牲畜抢草场,凭啥来牧区祸害草场?”
额日敦巴日听不下去了,这不是让老嘎查长骂苏木长吗?小时候,牧草绿油油密密麻麻,风一吹一个波浪一个波浪的。牛羊不用选择的撒着欢儿吃,一会儿肚儿就滚圆滚圆的。
现在一眼能见到地皮,矿山油田煤矿来了那么多人,下了班就在草场上瞎溜达,手里拿个铁铲子,见了药材就挖,一扣就是一个坑,一撮一撮的牧草就白白的死掉了。
鼠洞多去了,不到20年,就退化沙化成这个样子。
再过20年,草原会变成啥样子。这老鼠惹的祸真不小。
前两天嘎查长和满都拉粗略算了算,嘎查牧草的产量比80年代初下降30-50%,平均每亩的出草量由96公斤跌到57公斤。最糟糕的个别草场,鼠洞多达每亩370多个以上,每年减少的牧草接近16923公斤,牧区刮大风天数和沙尘暴的次数,也是一年比一年多。
畜牧站的人说,猫头鹰一年能吃掉1000多只老鼠,1000多个老鼠洞是多大的一片牧草呀。10个猫头鹰能吃掉1万只老鼠,100个猫头鹰能吃掉10万只老鼠,10万个老鼠洞又是多大的一片牧草呀。猫头鹰可是牧民的好朋友,应该保护它才对呀。
他对巴雅尔说:“天天唠叨这些废话有啥用?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改变不了就得服从。有尿,你去找旗长,不要像牛腚后面的苍蝇嗡嗡乱飞,没个方向。”
远处撒落的10多头牛,悠闲地甩着尾巴,东摇西幌的吃着草。
嘎查长说的在理儿。他白了白眼瞅着阿来夫,告瞎状都告不到点子上,气愤地说:“这10万多只老鼠成群在牧场窜动,那成啥啦。林矿从马上摔下来,骑马的技术不是主要的,我那匹马有灵性的,我喝多了,两脚插在马镫里,身子骗着耷拉着头,能把我驮回家。遍地的鼠洞,牧民从马背上摔下来的也不少呀,有的鼠洞深,折断马腿的也有呀。灭鼠的方法不对头,牧民的建议谁会听?不如放个臭屁,能闻到臭味,有些人还会斜眼聚眉瞅你一眼。”
嘎查长说:“不要乱说好不好?折断马腿的是獭子洞。獭子对草原祸害最厉害,掏出一堆一堆的‘獭丘’,咬断了草根,马蹄子就陷进去了。一个一个长长的洞,夏天挤满了雨水,草根飘在水里,水干了,羊草也就枯死了。獭子能传播鼠疫,祸害羊群。”
巴雅尔不服气地说:“祸害草场的是老鼠。满地的鼠洞,咬伤了多少的小羔子,那才传播鼠疫呐。”
额日敦巴日的目光掠过巴图的脸,扑到了巴雅尔那得意的眼上:“老嘎查长是个证人,说假话一点不脸红。獭子和老鼠哪个祸害的草多?你家的羔子让老鼠咬了吗?我的羔子可是让獭子咬死了,我亲眼看见的。”
牧区这几年出现了怪事,獭子咬死了小羔子,老鼠也能咬伤小羔子腿的,他俩说的都对。巴图开始拿猫头鹰说话:“不要争吵了。猫头鹰多了,老鼠自然会少,鼠洞也跟着少了。狼和狐狸多了,獭子有机会咬羔子吗?”
嘎查长和巴雅尔都半阴干着脸等待巴图点头随着自己的话往下说。巴雅尔拿猫头鹰来打压嘎查长,他习惯把煤矿矿山和油田的人叫“外来户”。
他抬高嗓门说:“‘外来户’跟牧民唱反调,听到猫头鹰叫是凶多吉少。有个工区长嘴巴对着我的耳朵说,夜里老有猫头鹰叫,井下死了3个人。给巡逻队每人发一个强光手电和一只气枪,专打猫头鹰。还规定打一只奖励200元,当月兑现。职工下班到草场练习枪法,一年打死了102只,这不等于白白放过了1万多只老鼠嘛。”
他说的102只,远远少于奖励的数,那一年发放了30000多的奖励,应该是150多只。
巴图接着说:“有人打猫头鹰,嘎查要管呀。扣煤挖矿是地底下的事,不要管空中的事,来了要守这里的规矩。猫头鹰没惹他们,也没伤害他们,叫几声就死人了。牧点没有这规矩,汉人的规矩,在牧区不好使。”
巴雅尔这把火真是烧到了点子上了。额日敦巴日知道巴雅尔是冲着嘎查来的,更是冲着苏木去的。在老人家面前,能哨一哨自己,哪能说俄日敦达来呐,那不直接打了巴图的脸嘛。他伸手拖着巴雅尔的胳膊要去矿山,走了一两步又住下了脚,这是做给巴图看的。
嘎查长心里也没底儿,依然做出有数的样子:“话有假话,发钱的帐,不会有假。我陪你去矿山,这102只可不是随口喊的。是真是假,去财务账上瞅一眼不就清楚了吗?一只奖励200元,看看领走的钱是不是2.04万元。要是没有,多出的你要张着口吃掉。嘴,是张着吃饭的,不是胡说乱道的。”
巴雅尔嘴上不说,身子往后仰着不肯挪步。
额日敦巴日装着拖着走的样子,脚步也不想挪动,他担心账面上会不会有2.06万,或者是2.08万。
巴雅尔感觉到胳膊上的拉力小了,向前跨了一大步,额日敦巴日腿脚晃悠两下倒在了地上。巴雅尔本来是能控制住自己不倒下的,就算愿意倒下,也可以倒在一侧,可他后退挪动了半小步,不偏不歪压在了额日敦巴日的身上。
巴雅尔却说:“咋的啦,拖着人又不走,心里有鬼啊。认个怂得了,不愿丢脸,愿意跌倒,哎呀,我的腰扭伤啊。”
额日敦巴日紧绷着脸半说半骂的:“害人啊,你心里才有鬼呐,往后仰着不动脚,拖着你不走,我用力拉,你故意向前跨大一步……”
巴雅尔在倒下之前,就看透了额日敦巴日的心虚了,爬起来瞪着眼说:“我跌
倒了,要找个垫背的,多出了102只,多几只,你吃掉几只。”为唠回面子,反过头来拖着额日敦巴日的手往矿山走。
额日敦巴日甩掉他的手说:“松开,我自己能走。”心里比水泡子里的水还清,财务账本是你想看就能随便看的嘛,非要他在巴图眼前丢人。他越走步子迈的越大,巴雅尔在兜里拨打了“土律师”的电话,接着又拨出了任钦的电话。离矿山办公楼门口100多米,任钦回过来了电话。
他笑呵呵大声说:“任主任啊,上次答应你的事,有事拖了几天,我这就给你送过去。”过了两天,给了任钦一只两岁的羯羊,圆了自己的谎。嘴贱钱出齐,关键时刻总比扇脸好多了。
额日敦巴日催着说:“走呀,巴图看不见了,就歇脚啦。装怂也不能在这里装,这不等于在巴图眼前我怂了吗?不行,说啥要去查清楚了。”
“送谁来也晚啦,电话里催了,我立马要到旗里去,有要紧的事。”他掉头跨着黄羊一样的大步,离开了嘎查长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