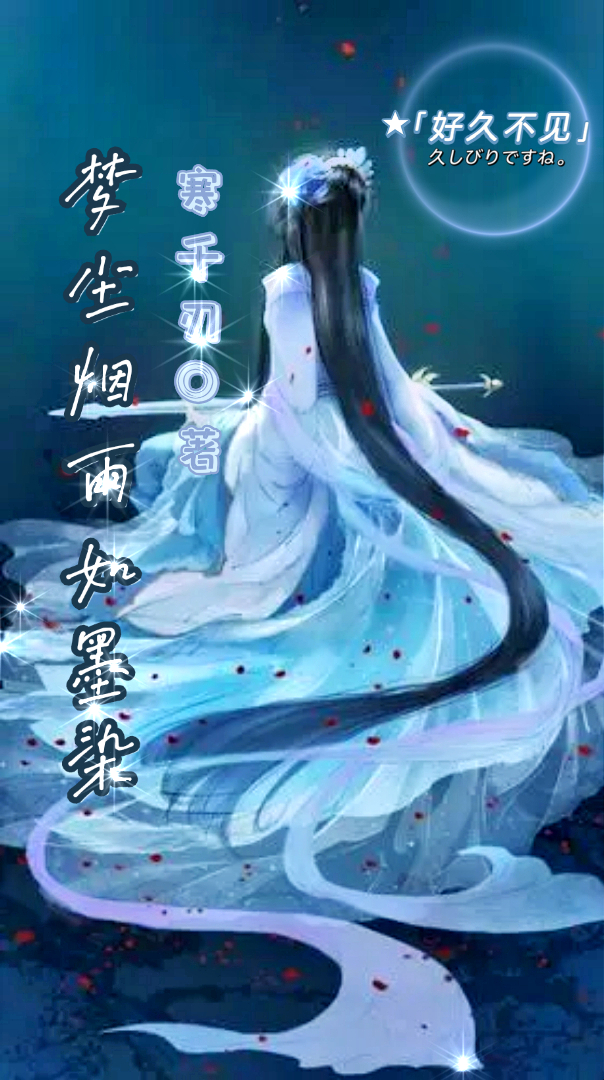眼前,某人的手大刺刺搭在某人的平原上,位置还很微妙。而某人的腿则肆无忌惮地斜压在某人的腰上,位置也挺奇妙。
“啊!”
“啊!”
两声尖叫同时响起,两人迅速拉开距离,都一脸震惊又嫌弃地看向对方。
“你怎么在这里?”郝瑟一脚踹过去,却扯得背心伤口疼了起来,又是一声惨叫:“啊嗷……”
景翊猝不及防被踢了一脚,一下捂住某处,也是一声惨叫:“啊嗷……”
“这是我的床,我不在这里在哪里??”景翊一脸痛苦地反问,又嘶嘶了两声,“狗子,你是要我断子绝孙吗?”
“那你为啥和我睡在一起?”郝瑟气鼓鼓的。
就是吧,再气,那胸也是鼓不起来的。哪像人家秀儿,每次怼夏风,气鼓鼓得充满视觉冲击。
“小爷我几天没睡好了,昨夜急巴巴跑去救你,折腾大半夜,太困了,所以就就地凑合了。有问题吗?再说,你一个男人,又不是女人。我还能占你便宜不成?”景翊也气鼓鼓的。
当然,那胸也是鼓不起来的。
郝瑟瞅了瞅那床,有些理亏。
这好像确实是人家救了自己,还给自己用了床,这么踢人家貌似有点不厚道。再说,大家都是“男人”,这估计也是困极了,倒头就睡,也没多大个事。
“不好意思啊。”郝瑟摸了摸头,有些不好意思,拍了拍床,“那你继续睡吧。”
“疼死小爷了,哎哟。”景翊还捂住不放。
他踢哪里不好啊,要踢那里。
最毒妇人心啊!
啊不,最毒狗子心啊!
“啊?”郝瑟有些慌了,习惯成自然地开口:“那我给你呼呼,呼呼就不痛了。”
“那赶紧啊!”景翊瞪她一眼,又嘶了一声,“多呼呼几下啊。”
上次狗子给他呼呼腰,他感觉好像真的没那么痛了。
郝瑟刚想凑过去,猛地顿住,一下惊醒。
呼呼?呼啥呼,那里能呼吗?
眼睛不由自主在某人捂住的位置掠过,神色古怪地看着景翊。
景翊一开始有些奇怪狗子怎么突然不动了,眸光跟着她的视线落向某处,也一下停止了惨呼,脸色比郝瑟还古怪。
一瞬诡异宁静。
窒息般的静音。
只剩两个有些刻意压低的呼吸声。
“啊呸,流氓!”郝瑟呸了一口,再次拉开和景翊的距离,如避蛇蝎。
“啊呸,死断袖!”景翊啐了一口,一下弹开,像被马蜂蛰了似的。
“喂,美人灯儿,你说谁是断袖?”郝瑟怒了,又一把掐了过去。
“当然是你,难道还是小爷我?”景翊更怒,这次闪的快,没被掐住,有些恼羞成怒地吼道:“小狗子,小爷我喜欢的是女人,听清楚了!女人!”
郝瑟也怒,把一马平川拍得砰砰响:“老子才不是断袖,老子喜欢的是男人,听清楚了。”
又是一瞬诡异宁静。
仙人板板!
郝瑟差点咬了自己舌头。
“啊,不不不,口误,口误。老子喜欢女人。”郝瑟连忙纠正,欲哭无泪。
这一激动,就忘记现在的性别定位了,喜欢男人脱口而出,这下简直跳黄河了,不晓得还洗的清不。
话说,喜欢女人的话,她不成蕾丝了嘛,不要啊。
景翊神色复杂地看了她半天,突然笑了起来,玉树生花一般,似乎心情挺好。
景翊凑近她,故意勾起她下巴,语调挑逗:“狗狗,你真喜欢男人?”
郝瑟心里一颤,这家伙声音太好听了,低沉磁性,攻音满格,撩得人心底波澜起伏。
这家伙难道真是断袖,想掰弯她?
想得美!
“滚!”心里一慌的郝瑟,一巴掌拍开他的手,再次强调:“老子是男人。刚才口误。”
景翊似笑非笑地看着她,来了句:“其实,男人也是可以的。”
郝瑟:“……”
这狗主子脑子有病,他究竟在说啥?
看着郝瑟吃瘪的样子,景翊愈加乐呵了起来,笑得胸腔回音轻鸣:“狗狗,想和本王斗,再修炼修炼。”
比无耻,从来没人赢过他。
看着景翊得意猖狂的样子,郝瑟的尿性又激发了,奶奶的,姐不打垮你,姐就不是现代人。
郝瑟也冲景翊风情万种地一笑,微微偏头,单眼一眨,桃眸水光流转,极其魅惑勾搭的一个眼神。
双手随后搭上他的肩,凑近他,嘟起红唇,吐气如兰,轻若蚊蚁地道:“王爷,男人也是可以的,要不试试?”
郝瑟笑得张扬,齿若编贝,闪着晶亮的光。桃花眼瞥来如流水,长发梦一般撒在他肩上。
在刚才的拉扯中,领口也微微散落开来,露出一抹玉白的颈项,闪着诱人的光泽。
而那锁骨流畅优美,延伸出一段紧凑的弧线。
景翊脊背瞬间绷直,眼光从那丰满红润的唇珠上掠过,再从那抹洁白流过,呼吸微微发紧。
要命!
狗子这家伙明明一个男人,却让人忍不住想入非非,他感觉,要再这样被他撩下去,迟早要弯。
“哟,脸红了哟。”郝瑟放开他,一脸得逞的笑意。
笑声轻俏而得意,如精灵惊破迷雾丛林。
灯光下,那双眼角斜飞的蝴蝶眼,似飞出了无数朵惑人的桃花来,一朵一朵开在景翊眼底,满眼春色葳蕤。
她赢了。
才怪!
红了脸的某人,恼羞成怒,一个翻身,将她压住,也凑近她,声音磁性又魅惑,低低的,声声入耳,能勾起人心底最深最隐秘的渴望:“好呀,那就试试呀。”
景翊身子沉了沉,那花木般的香味笼罩了她。
郝瑟瞬间呆住,有些愣愣地看着他,他身上热热的体温透过衣料毫无障碍地传递过来,让她本能地感受出一种天然危险感。
看着郝瑟呆住,景翊觉得,他赢了。
才怪!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郝瑟笑了,笑得又魅又坏,手指往他胸前一戳一点,一翻身,也压住某人,“哎呀王爷,那就试试呗,我上你下哦。”
景翊笑容一窒,太阳穴扑扑乱跳,也一个翻身,手却托住她的背,防止她背部撞疼。
郝瑟再翻身。
景翊再翻身。
两人都将谁上谁下的主权争夺战进行到底。
上上下下,下下上上。
滚来滚去,翻来覆去。
斗法中的两人,都没注意到,有人轻轻扣了扣房门。
吱呀一声。
门被推开,容绥走了进来,边走边说:“该给郝瑟换……”
容绥说到一半的话哑在喉咙里,目瞪口呆地看着两人,身子微微僵住,脸色都似微微发白。
此刻,她在下,他在上,两人凑得很近,鼻尖都快贴着鼻尖了,从容绥的角度看去,那唇也似乎贴在了一起,目光也胶在一起。
两人还似乎都“香汗淋漓”的即视感。除了衣衫完整,但……却有些凌乱。
房间里第三次诡异宁静。
针落可闻。
尴尬满门。
狗血横流。
容绥眨了眨眼,再眨了眨眼。
“打扰了,你们继续,继续。”容绥总算从石化状态活了过来,脸上泛起红晕,转身就往外走,却不知怎么绊了一下,差点跌在门槛上。
郝瑟:“……”
景翊:“……”
“喂,回来啊,你误会了。”郝瑟眼角抽了抽,求生欲般地想喊住容绥,她觉得应该可以抢救一下。
她就是和无良狗主子打了一架啊。
怎么容绥一副“抓什么现场”的样子啊。
景翊脸皮隐抽,一下放开她,“赶紧起来换药了。我让人给你打水来,你先洗漱,我再叫容绥来换药。”
这种事,没必要解释,越解释越乱。
他是男人,鸟朝天的男人,只对女人有兴趣。他不是断袖,他清楚得很。
他刚才就是和目无尊上的无良小狗子打了一架而已。
“哦。”郝瑟也不尴尬了,误会就误会呗,又不是真的。
她现在最大的保护色就是男人身份。
景翊出去后,下人没一会就打了热水和洗漱用品来,郝瑟意外发现,这刚才滚来滚去的,背上的伤口居然没被床摩擦痛,好生奇怪。
匆匆洗漱了一翻,景翊就把一脸怪异神色的容绥重新找回来了。
换药过程,容绥有些沉默,薄唇微微抿着,垂着眼皮,浓密睫毛轻颤,投射下一大片阴影,让人看不清那眸底的神色。
换了药后,郝瑟又开始问起了盛都府的情况。
“你那些属下,大部分活下来了,就地牢里审讯的,死了一个,不过都受了伤,夏风昨夜就安排了人过去诊治,问题不大……”景翊开始给她简单讲了下昨夜的情况。
郝瑟听得目瞪口呆,却又深感安慰。
这种情况,已经算是很幸运了,她一直担心这些兄弟都被灭了口。还好,这些下属脑子还算灵活,没来个无谓的血拼,否则得全军阵亡了,真那样,她心里就很煎熬的。
还有幸好她平时也有给整个盛都府官员培训过类似遇到地震啥的该如何处理等。所以地牢里的衙役,也很幸运的,虽伤却到底活了下来。
“只不过,地牢里的犯人,全都死了。”景翊补充。
郝瑟沉默了一下。
“那些杀手呢?”
“我杀了。”景翊声音有些狠厉。
“没留活口吗?”郝瑟有些失望,抓点活的,或许能审问点啥出来。
“一个不留。”景翊浑身冒出冷意,眼里又隐隐有些疯。
他知道应该留活口,可当时还是没忍住都给杀了。主要看到他家狗狗的伤,那怒气就怎么也压不下来。
郝瑟突然就想起昨夜地牢里那有点疯的景翊,那盏黑色美人灯。
像地狱里走出来的杀神,疯狂狠辣。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眼里没有人间烟火。
心里微微有些涩,她知道,人的性格和行为,除了先天,后天经历也在不断修改着人的性格。
这人,得经历过什么,才会偶尔出现疯批属性啊。平日里看起来,挺正常的,除了不羁一点,无耻一点。
“杀光好。”郝瑟拍拍景翊,“你喜欢就好。”
景翊眼里的冷和疯,一下就散了去,唇角牵起,笑了。
这一次,没有邪魅,没有坏笑,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就只是单纯的,浅浅的笑,似乎心情很愉悦。
郝瑟脑子又晃了晃。
美人灯又来了,别动不动就笑啊。
他一笑,就好像暮沉的天空炸开了一道道璀璨的烟花,刹那星月漫天,绚烂异常。
又如春风解冻万里冰河,河岸忽然葳蕤蔓延,每一寸都是花开的天堂。
在这能让天地万物黯然失色的笑容下,郝瑟有些心惊地发现,心跳都似乎快了起来。
“可惜地牢的人证也都死了。”郝瑟移开视线,忽略掉被美人灯弄得有些快的心跳,转移话题。
人证没了,她要如何给幕后人定罪。
景翊突然凑近郝瑟,在她耳边低语了几句。
郝瑟猛然睁大眼,极度震惊地看着景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