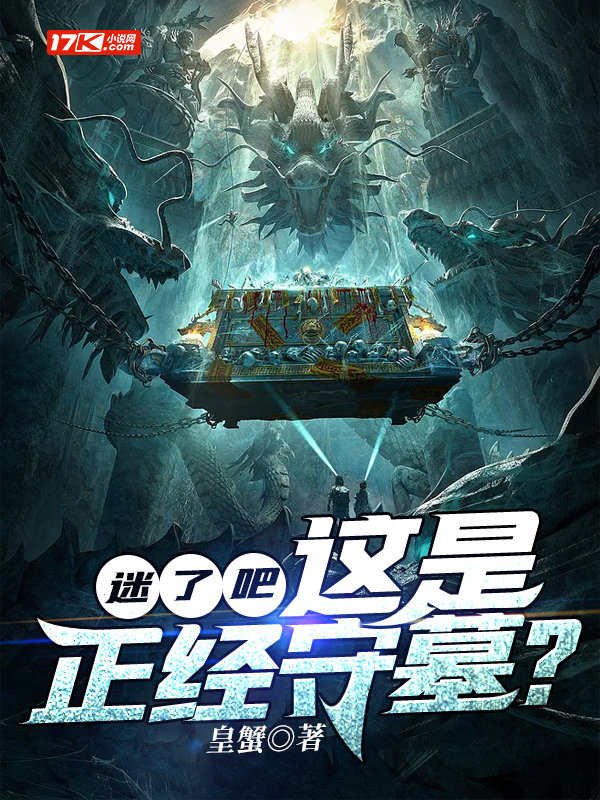五十四
再说白圣寒山内,千允从踏上这片白色土地开始,就觉得有股莫名的熟悉感。
四下无人,唯风萧瑟。一路向前,乱石无阻。
黑衣红伞,在这片苍茫中尤为显眼,漫天鹅毛也挡不住前进的步伐。
千允左手的白卫一如既往的安静,小长耳朵不时地砸吧两下吹到头顶的冰凉。
前方,是一个石洞,一旁,有一个水池,水面漂着些许殷红的花瓣,四周,去不见一颗梅树。奇了怪了,千允将伞往后斜靠,半仰着头看向山顶,穿过漫天飞雪,崖边,有一枝腊梅在迎风摇曳。
千允左手捏了捏白卫的小前爪子:“这梅花倒像是成了精,只往小水池子飘,周边的雪地里愣是没看到一片儿。”轻笑一声,往石洞里走去。
刚到门口,手中的白卫突然惊跳而起,带头往山洞里奔去,千允山都来不及手,就急忙跟上去。
因四下无灯,仅能凭借白卫散发出来的白光来看清前方,她跟着白卫跑过漫长而曲折的狭小密道,最后进入了一间空荡的房间,白卫还在向前跑,千允想要伸手将它抓回来,眼前却突然一黑。
她下意识的闭眼,忽然感觉耳畔有疾风,不对,那风在往下压她的伞,睁眼,往四周探索一番,还是一片漆黑,正当她准备呼喊白卫时,感觉有东西抓住了她的裙角。
她缓缓躬身,将那团东西抓在左手:“哟!饿了?那就是不能发光了,睡吧,我现在没吃的。”说着将小东西往衣袖里塞去。
原地转了两圈,伸出左手捏了个诀:“火明。”
房间亮了起来,在千允身旁站着一个半人高的红衣小孩儿,光芒就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你如今堂堂一个铷周期的修士,是不会自己用燃灯术吗!”每次照明都要把它提出来,烦不烦!
千允伸手给了它脑袋一巴掌,右手的红伞递给它:“愿赌服输,拿着。”
许多年前这个初生的天火胆大地烧到了青山寺,结果被困在青山寺的后山痴情湖中,日日受佛光沐浴,竟然成了精,三年前逃出青山寺,结果很是不幸地遇到了本该在晴央庄养病的千允,被礼貌的坑了一把,签了很平等的条约,真的,一点也不偏,这个条约很公平。
电离拿过伞:“说了多少次,我是典离,不叫火明,怎么……”它一边打量着这把红伞一边吐槽着千允,吐槽到一半,就被化成一把红扇子的伞惊得说不出话来。
千允上前观察着四根石柱,对它的声音不轻不重地嗯了一声,双手负立,头顶的风还在跳跃,扬起了她的青丝几缕。
典离抬头看了看前方全神贯注的黑衣女子,又低头看了看手中的黑骨红面扇,打开一看,龙飞凤舞的一个‘井’字:“你……”不会是四大拊掌之一吧?年纪轻轻,倒是没看出来啊!可是这些天那些人不都喊她圣尊吗?人类真是个复杂的玩意儿。
千允没注意它说的什么:“火明。”
典离上前:“怎么?”虽然它被剥夺了原本的名字,但是大佬说什么都是对的。
千允抓住它的肩膀往前送了送,更清楚地看见了石柱上面刻的东西,也看见了缠在石柱上的手臂粗的铁链上有暗沉色,有些像是干涸的血迹。
典离的脸距离石柱很近,它不明所以地瞪大了眼睛瞧:“那个,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凭着它当妖怪多年的直觉,这地儿不是到地方,不宜妖怪呆,当然,人也不适合。
千允收回推它的手:“自己掂量着来吧。”
典离:“咱还是先离开吧,这个地牢没什么好看的。”
千允皱眉,她总觉得这里不像是地牢,伸出手拉了拉铁锁链,丝毫不动:“这儿……”好像不是地牢,那铁锁链看似禁锢着石柱里面的东西,可仅是石柱表面的符箓封印就足以挡住一切了,根本无需再加上这个。
典离拉了拉她的衣袖:“怎么了?”
千允摇头,在房间里探索一番,确定并无其他出入口后,便原路返回了。
…………听楼阁
松然敲了敲青松房门:“主上。”
“进。”
青松坐在案桌之前:“如何了。”
“属下将圣尊送到闻楼山谷后便回了,据探子汇报,圣尊已孤身前往白圣寒山了,此外典狱楼方采在圣尊走后现身,并赠与杨少主一把折扇,程仁也在边境与不聊生对上……”
青松放下狼毫,将所写之信装入几个信封:“将信送到各个司主手上,今夜行动。”
“是!”
一阵风吹过,桌前已无写信之人的身影。
青柏最近心情不怎么好,虽然奏章都是些无足轻重的问题,很少有关于江湖组织挑衅皇权的事情发生,但他总觉得过于平静了,就像是暴风雨前来的宁静。
今夜早早处理完了公文,便想着独自走一走,这一走,就到了西山林院,他记得这里是给那位国师安排的居所,想来这么多天也没有见到这位没什么存在感却似乎很受那位少主尊敬的质子国师,好像叫什么萧琛来着?
这般想着,便踏进了西山林院,这本是一个茶花培养院,里面最多的植物就是各类茶树了,走廊七七八八,沿着弯弯曲曲的小道走到尽头,看到在那棵不知几百年的茶树下,有一人正对月独酌。
还是一袭深紫色长跑,长发被一根同色系的发带束缚住,桌子上摆着一个棋盘,却不见棋子。
青柏走近了问道:“国师可是念家了?”
萧琛没有抬头,眼睛像是浓稠的浆糊黏在手中的酒壶上:“不曾。”
青柏倒是习惯了别人对他无礼,毕竟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当傀儡皇帝还当得引以为傲的:“那想来国师是爱上了经年酒了。”
萧琛仰头一大口:“不及北拉赞的烈酒纯粹。”
青柏自顾自地坐下,硬是不让国师将天儿聊死:“那国师为何饮如此多的酒?莫非对国师来说,今日是个特殊的日子?”他瞟了一眼地上的小酒壶,怎么滴也有五六个了。
萧琛望向远方,而后叹了口气:“对我来说,并无什么特殊意义,只是七日后,适合回魂。”
青柏有种强烈的不安感:“何出此言?”
萧琛放下已经空了的酒壶,摸了摸放在桌上的棋盘,这是她这几天刚刻完的:“昨日月圆,我观星象有异,又卜了一卦。”
青柏眼皮猛地跳了几下:“如何?”
萧琛望着他的眼睛,缓缓道:“血雨万千,不渡人间。”
青柏:“什、么意思?”
萧琛抬头:“皇上,这可茶树许多年了罢?”
青柏闻言不解她为何转移话题,但还是点头道:“不错,先祖建国之初时,它便在此处了。”
萧琛放在棋盘上的手蜷了起来:“最近,它有枯萎的迹象。”
青柏不知是否该信萧琛所言:“可有挽救之法?”
萧琛低头敲了敲棋盘:“空有棋盘,不见棋子,如何操纵?”
青柏望着棋盘良久不语,寒风入夜,吹落了茶树的黄叶,枯叶飘荡旋转,仿佛在以最美的姿态与高处的风景告别。
青柏看着它落在了棋盘上,不偏不倚,正居中央:“国师片面了,万物皆可围棋,事在人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