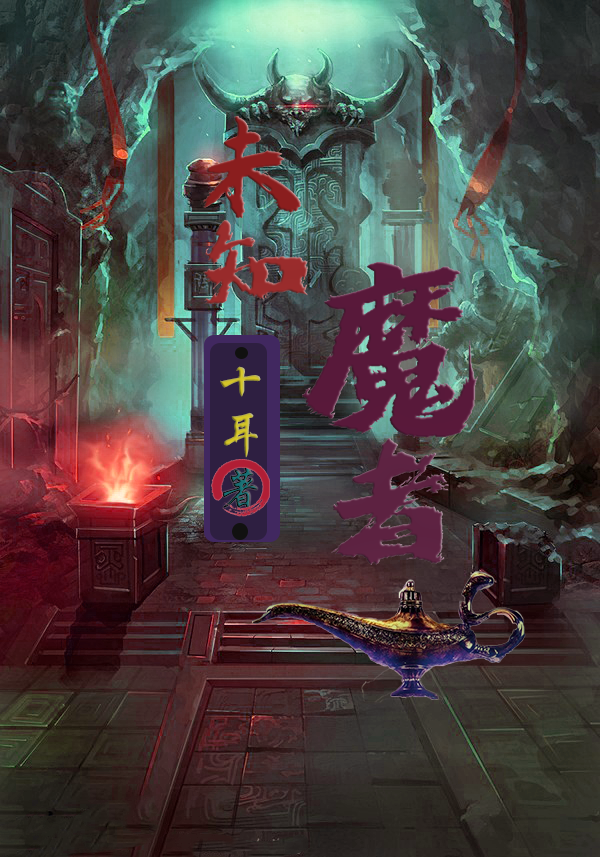好大圣,按一按项上金箍,束一束腰间裙子,执着铁棒,径到大雄宝殿上,指着那尊佛像道:“你本是泥塑金装假像,内里岂无感应?我老孙保领大唐圣僧往西天取经,今晚特来此处投宿,趁早与我报名!假若不留我等,就一顿棍打碎金身,教你还现本相泥土!”这大圣正在前边发狠捣叉子乱说,只见一个晚香的和尚,点了几枝香,来佛前炉里插,被大圣咄的一声,唬了一跌,爬起来看见脸,又是一跌,吓得滚滚跄跄,跑入方丈里报道:“老爷!外边有个和尚打扮的来了!”那僧官道:“你这伙和尚都少打!一行说教他往前廊下去蹲,又报什么!再说打二十。”小和尚道:“老爷,这个和尚,比那个和尚不同,生得恶无脊骨。”僧官道:“怎的模样?”小和尚道:“是个圆眼睛,查耳朵,满面毛,雷公嘴,手执一根棍子,咬牙恨恨的,要寻人打哩。”僧官道:“等我出去看。”他即开门,只见行者撞进来了。那老和尚看了一眼,就吓得把方丈门关了。行者赶上,扑的打破门扇,道:“赶早,将干净房子打扫一千间,老孙睡觉!”僧官躲在房里,对小和尚说:“怪他生得丑么,原来是说大话,折作的这般嘴脸。我这里连方丈、佛殿、钟鼓楼、两廊共总也不上三百间,他却要一千间睡觉,却打哪里来?”小和尚道:“老爷,我也是吓破胆的人了,凭你怎么答应他罢。”那僧官颤索索的高叫道:“那借宿的长老,我这小荒山不方便,不敢奉留,往别处去宿罢。”行者将棍子变得盆来粗细,直壁壁的竖在天井里,道:“和尚,不方便,你就搬出去!”僧官道:“我们从小儿住的寺,师公传与师父,师父传与我辈,我辈要远继儿孙。他不知是哪里勾当,冒冒失失的,教我们搬哩。”小和尚道:“老爷,十分不尴尬,搬出去也罢,杠子打进门来了。”僧官道:“你莫胡说!我们老少众大四五百名和尚,往哪里搬?搬出去,却也没处住。”行者听见道:“和尚,没处搬,就出来一个打样棍!”老和尚叫:“小的,你出去与我打个样棍来。”那小和尚慌了道:“爷爷呀!那等个大杠子,教我去打样棍?”老和尚道:“养军千日,用军一朝。你怎么不出去?”小和尚道:“那杠子莫说打来,若倒下来,压也压个肉泥!”僧官道:“也莫要说压,只道竖在天井里,夜晚走路,不记得啊,一头也撞个大窟窿!”小和尚道:“老爷,你晓得这般重,却教我出去打什么样棍?”他自家里面转闹起来。行者听见道:“是也禁不得,假若就一棍打杀一个,我师父又怪我行凶了。且等我另寻一个什么打与你看看。”忽抬头,只见方丈门外有一个石狮子,却就举起棍来,乒乓一下打得粉乱麻碎。那老和尚在窗眼儿里看见,就吓得骨软筋麻,慌忙往床下拱,小和尚就往桌下藏,口中不住叫:“爷爷,棍重棍重!禁不得,方便,方便。”行者道:“和尚,我不打你。我问你:这寺里有多少和尚?”僧官颤索索的道:“前后有九十二个房头,共有四百四十二个有度牒的和尚。”行者道:“你快去把那四百多个和尚都点得齐齐整整,穿了长衣服出去,把我那唐朝的师父接进来,就不打你了。”僧官道:“爷爷,若是不打,便抬也抬进来。”行者道:“趁早去!”僧官叫:“小的,你莫说吓破了胆,就是吓破了胆,便也去与我叫这些人来接唐僧老爷爷来。”
那和尚没奈何,舍了性命,不敢撞门,从后边狗洞里钻将出去,径到正殿上,东边打鼓,西边撞钟,钟鼓一起响处,惊动了两廊大小僧众,上殿门道:“这早还不晚哩,撞钟打鼓做甚?”和尚道:“快唤衣服,随老师父排班,出山门外,迎接唐朝来的老爷。”那众和尚真个齐齐整整,摆班出门迎接。有的披了袈裟,有的着了褊衫,无的穿着个一口钟直裰,十分穷的,没有长衣服,就把腰裙接起两条,披在身上。行者看见道:“和尚,你穿的是什么衣服?”和尚见他丑恶,道:“爷爷,不要打,这是我们城中化的布,此间没有裁缝,是自家做的‘一裹穷’。”
行者闻言暗笑,押着众僧,出山门下跪下,那僧官磕头高叫道:“唐老爷,请方丈里坐。”八戒看见道:“师父老大不济事,你出来时,泪汪汪,嘴上挂得油瓶;师兄怎么就有此獐智,教他们磕头来接;若我老猪进去,或许他们抬轿来接你哩!”三藏道:“你这个呆子,好不晓礼!师父能强硬他们吗?”唐僧见他们磕头礼拜,甚是不过意,上前道:“列位请起。”众僧叩头道:“老爷,若和你徒弟说声方便,不动杠子,就跪一个月也罢。”唐僧叫:“悟空,莫要打他。”行者道:“不曾打,若打,这会已打断了根矣。”那些和尚,却才起身,牵马的牵马,挑担的挑担,抬着唐僧,驮着八戒,挽着沙僧,一齐都进山门里去,却朝后面方丈中,依叙坐下。众僧又礼拜,三藏道:“院主请起,再不必行礼,你作践贫僧,我和你都是佛门弟子。”僧官道:“老爷是上国钦差,小和尚有失迎接。今到荒山,奈何俗眼不识尊仪,与老爷邂逅相逢。动问老爷,一路上是吃素?是吃荤?我们好去办饭。”三藏道:“吃素。”僧官道:“这个爷爷,好的吃荤。”行者道:“我荤素皆可。只我那胖师弟,是要吃大荤的。”僧官道:“这位大胡子老爷也是吃荤了。”沙僧道:“我随师父吃素。”那和尚道:“爷爷呀,这等凶汉也吃素?”沙僧道:“啰嗦什么,吃素就是吃素。”八戒道:“沙僧也变得假仁假义起来。”三藏道:“那悟能就不会说话,吃素就假仁假义了?我说院主,不要太麻烦,我师徒都吃素罢!”院主又礼拜道:“谢谢老爷了,真要吃荤,还要现到集镇上置办。我这寺院,虽是敕造,这几年香火大不如前了。”三藏还要说话,有一个胆大的和尚忙近前问:“要给老爷们煮多少米的饭方够吃?”八戒见没了荤腥,就喊道:“小家子和尚!问什么,一家煮上一石米。”那和尚都慌了,便去刷洗锅灶,各房中安排茶饭,高掌明灯,调开桌椅,管待唐僧。
师徒们都吃了晚斋,众僧收拾了家伙,又请唐僧师徒喝茶。三藏道:“悟空,我看这些和尚穿的不像,茶饭粗淡,想是生活艰难,不如拿些银子给他,均着置办些衣服。”众僧听着要给银子,都齐跪下叫老爷。大圣道:“都起来。唐老爷给你钱,也不是白给,除置办衣物外,还要拿些钱置办些锄铲钯锨,再买些种子,去那寺外荒坡上,开垦些土地,种些吃物,都有两只手,不强似低三下四去化缘。”众僧道:“谢爷爷指教。”三藏道:“悟净,去把那银子拿出来。”沙僧起身道:“拿多少?”三藏道:“悟空,拿来一半够不够?”悟空道:“足够有余。”那沙僧和八戒却舍不得,只去篾箱里拿来十二三个银鸡蛋给了院主。众和尚都噙着泪再再拜上唐僧师徒。三藏道:“我师徒却在哪里安歇?”僧官道:“恩人老爷不要忙,小和尚自有区处。”叫管事僧:“那壁厢有几个人听使令的?”管事僧道:“师父,要多少有多少。”僧官吩咐道:“着四个给白马安排草料,着八个去前面把那三间禅堂,打扫干净,铺设床帐,着八个准备热汤,快请老爷洗浴安歇。”那些和尚听命,各各整顿齐备,却来请老爷安寝。和尚们牵马挑担前行,他们师徒后跟,径去前面禅堂门首看时,只见那里面灯火光明,两梢间铺着四个藤屉床。行者见了,唤那办草料的和尚,将草料抬来,放在禅堂里面,牵进白马。一时,和尚们又奉上香汤,师徒们都洗了。三藏见门外还有几个侍候的和尚不走,便道:“既此就要安寢了,都就请回。”众人却才敢散去讫。
唐僧举步出门小解,只见明月当天,叫“徒弟。”行者、八戒、沙僧都出来侍立。因感这月清光皎洁,玉宇深沉,真是一轮高照,大地分明,对月怀旧,口占一首古风长篇。诗曰:
皓魄当空宝镜悬,山河摇影十分全。
琼楼玉宇清光满,冰鉴银盘爽气旋。
万里此时同皎洁,三春今夜最明鲜。
浑如霜饼离沧海,却似冰轮挂碧天。
别馆寒窗孤客闷,山村野店老翁眠。
乍临汉苑惊春鬓,才到秦楼促晚奁。
庾亮有诗传晋史,哀宏不寐泛江船。
光浮杯面寒无力,清映庭中健有仙。
处处窗轩吟白雪,家家院宇弄冰弦。
今宵静玩来山寺,何时相同返故园?
行者闻言,近前答曰:“师父啊,你只知月色光华,心怀故里,更不知月中之意,乃先天法象之规绳也。月至三十日,阳魂之金散尽,阴魄之水盈轮,故纯黑而无光,乃曰畮。此时与日相交,在晦朔两日之间,感阳光而孕。至初三日一阳现,初八日二阳生,魄中魂半,其平如绳,故曰上弦。至今十五日,三阳备足,是以团圆,故曰望。至十六日一阴生,二十二日二阴生,此时魂中魄半,其平如绳,故曰下弦。至三十日三阴备足,亦当晦。此乃先天守炼之意也。诗曰:
前弦之后后弦前,药味平平气象全。
采得归来炉里炼,志高功果即心田。”
八戒笑道:“猴哥,还在师父面前摆文,也不知摆正摆不正?”沙僧道:“大师兄此言虽当,只说的是弦前属阳,弦后属阴,阴中阳半,得水之金;更不道:
水火相搀各有缘,全凭土母配如然。
三家同会无争竞,水在长江月在天。”
八戒闻说,上前扯住长老道:“师父,莫听乱讲,误了睡觉。这月啊:
缺之不久又团圆,似我生来不十全。
吃饭嫌我肚子大,拿碗又说有粘涎。
他都伶俐修来福,我自痴愚和下缘。
我说你取经还满三途业,摆尾摇头直上天!”
师徒们便回到房里,三藏道:“也罢,徒弟们走路辛苦,先去睡下,等我把这卷经来念一念。”八戒道:“师父差了,你自幼出家做了和尚,小时的经文,哪本不熟?却又领了唐王旨意,上西天见佛,求取大乘真典,如今功未完成,佛未得见,经未曾取,你念的是哪卷经儿?”三藏道:“我自出长安,朝朝跋涉,日日奔波,小时的经文恐怕生了,幸今夜得闲,等我温习温习。”八戒笑道:“老和尚又变了小和尚。我们先睡好了!”他三人各往一张藤床上睡下。长老掩上禅堂门,高剔银缸,铺开经本,默默看经。正是楼头初鼓人烟静,野浦渔舟火灭时。
却说三藏坐于宝林寺禅堂中,灯下念一会《梁皇水忏》,看一会《孔雀真经》,只坐到三更时候,却才把经本包在囊里,正欲起身去睡,只听得门外扑剌剌一声响亮,淅零零刮阵狂风。那长老恐吹灭了灯,慌忙将褊衫袖子遮住,又见那灯或明或暗,便觉有些心惊胆颤。此时又困倦上来,伏在经案上盹睡,虽是合眼朦胧,却还心中明白。耳内嘤嘤听着窗外阴风飒飒。真个那:
淅淅潇潇,飘飘荡荡。淅淅潇潇飞落叶,飘飘荡荡卷浮云。满天星斗皆昏昧,遍地尘沙尽洒粉。一阵家猛,一阵家纯。纯时松竹敲清韵,猛处江湖波浪浑。刮得那山鸟难栖声哽哽,海鱼不定跳喷喷。东西馆阁门窗脱,前后房廊神鬼镇。佛殿花瓶吹堕地,琉璃摇落慧灯昏。香炉攲倒香灰迸,烛架歪斜烛焰横。幢幡宝盖都摇拆,钟鼓楼台撼动根。
那长老昏梦中听着风声一时过处,又闻得禅堂外,隐隐的叫一声:“师父。”忽抬头梦中观看,门外站着一条汉子,浑身上下,水淋淋的,眼中垂泪,口里不住叫:“师父!师父!”三藏欠身道:“你莫是魍魉妖魅,神怪邪魔,至夜深时来此戏我?我却不是那贪嗔之类。我本是个光明正大之僧,奉东土大唐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经者。我手下有四个徒弟,都是降狮伏虎之英豪,扫怪除魔之壮士。他若见了,把你碎尸粉骨,化作微尘。此时我大慈悲之意,方便之心。你趁早儿潜身远遁,莫上我的禅门来。”那人倚定禅堂道:“师父,我不是妖魔鬼怪,亦不是魍魉邪神。”三藏道:“你既不是此类,却深夜来此何为?”那人道:“师父,你舍眼看我一看。”长老果仔细定睛看处,呀!只见他:
头戴一顶冲天冠,腰束一条碧玉带。身穿一领飞龙舞风赭黄袍,足踏一双云头绣口无忧履。面如东岳长生帝,形似文昌开化君。
三藏见了,大惊失色,急躬身厉声,高叫道:“是哪一朝陛下?请坐。”用手忙搀,扑了个空虚,回身坐定。再看处,还是那人。长老便问:“陛下,你是哪里皇王?何邦帝主?想必是国土不宁,谗臣欺虐,半夜逃生至此。有何话说,说与我听。”这人才泪滴腮边谈旧事,愁攒眉上诉前因。道:“师父啊,我家住在正西,离此只有四十里远近。那厢有座城池,便是兴隆之处。”三藏道:“叫做什么地名?”那人道:“不瞒师父说,便是朕当时创立家邦,改号乌鸡国。”三藏道:“陛下这等惊慌,却因何事至此?”那人道:“师父啊,我这里五年前,天年干旱,草子不生,民皆饥死,甚是伤情。”三藏闻言,点头叹道:“陛下啊,古人云:‘国正天心顺’。 想必是你不慈恤万民,既遭荒歉,怎么就躲离城郭?且去开了仓库,赈济黎民;悔过前非,重兴今善,放赦了那枉法冤人。自然天心和合,雨顺风调。”那人道:“我国中仓廪空虚,钱粮尽绝,文武两班停俸禄,寡人膳食亦无荤。仿效禹王治水,与万民同受甘苦,打井造塘,却都不见功效。如此三年,只干得河枯井涸。正都在危急之处,忽然钟南山来了一个全真,能呼风换雨,点石成金。先见我文武多官,后来见朕,当即请他登坛祈祷,果然有应,只见令牌响处,顷刻间大雨滂沱,寡人只望三尺雨足矣,他说久旱,不能润泽,又多下了五寸。朕见他如此尚义,就与他八拜为交,以兄弟称之。”三藏道:“此陛下万千之喜也。”那人道:“喜自何来?”三藏道:“那全真既有这等本事,若要雨时,就教他下雨,若要金时,就教他点金。还有哪些不足,却离了城阙来此?”那人道:“朕与他同寝食者,只得二年。又遇着阳春天气,红杏夭桃,开花绽蕊,家家仕女,处处王孙,俱去游春赏玩。那时节,文武归衙,嫔妃转院。朕与那全真携手缓步,至御花园里,忽行到八角琉璃井边,不知他抛下些什么物件,井中有万道金光。哄朕到井边看什么宝贝,他陡起凶心,扑通的把寡人推下井内,将石板盖住井口,拥上泥土,移一株芭蕉栽在上面。可怜我啊,已死去三年,是一个落井伤生的冤屈之鬼也!”
唐僧见说是鬼,唬得筋力酥软,毛骨耸然。没奈何,只得将言又问他道:“陛下,你说的这话全不在理。既死三年,那文武多官,三宫皇后,遇三朝见驾殿上,怎么就不寻你?”那人道:“师父啊,说起他的本事,果然世间罕有!自从害了朕,他当时在御花园内,摇身一变,就变做朕的模样,更无差别。现今占了我的江山,暗侵了我的国土。他把我两班文武,四百朝官,三宫皇后,六院嫔妃,尽属了他矣。”三藏道:“那全真与你称兄道弟,已有二年,若变了你的模样,那不少了一个全真,文武百官能不相问?”那人道:“他能言善变,只说全真在御花园化风而去,又说常常思念全真,进了花园更加思念、伤心,他又趁势封了御花园。”三藏道:“你何不托梦于三宫六院和文武百官,叫他们与你报仇?”那人道:“他不知用了什么法术,我的冤魂近不得皇城,梦也转不到皇后皇儿及文武百官那里。”三藏道:“陛下,你忒也懦。”那人道:“何懦?”三藏道:“陛下,既然后妃、文武不能与你报仇,你何不在阴司阎王处具告,把你的屈情伸诉?”那人道:“他的神通广大,官吏情熟,都城隍常与他会酒,十代阎王是他的熟人。我哪有投告之门?”三藏道:“陛下,你阴司里既没本事告他,却来我阳世作甚?”那人道:“我死后,东山山神时常接济我;我无处宿时,就在他那里过夜。是山神告诉我,唐朝的圣僧可帮我报夺国侵家之仇,今知圣僧已到宝林寺,要我快来相求。今来志心拜恳,千乞到我城中,拿住妖魔,辨明邪正,寡人当结草衔环,报酬师恩也。”三藏道:“我有几个徒弟,干别的事不济,但说降妖捉怪,正合他宜。我就着徒弟与你报仇若何?”那人感激不尽,忙与三藏下跪,三藏就去搀他,却又搀了个空。回身坐定,再看处,还跪在那里。三藏道:“我已应了你,何不起来?”那人便千恩万谢地站了起来。三藏道:“那怪既神通广大,变得与你相同,满朝文武,一个个言和心顺,三宫妃嫔,一个个意合情投。我徒弟纵有手段,决不敢轻动干戈。倘被多官拿住,说我们欺邦灭国,问一款大逆之罪,困陷城中,却不是画虎刻鹄也?总要找个由头才好下手。”那人道:“我已是死去的君主了,无计可施。你何不与你徒弟商议商议,他既是擒魔高手,必有计策。”三藏点头应承道:“你去罢。等与你报了仇,叫徒弟去山神庙报你信便了。”那冤魂叩头拜别而去。
却说三藏惊醒,那国王相求一事,原是南柯一梦。慌得对着那盏昏灯,连忙叫:“徒弟!徒弟!”八戒醒来道:“什么‘土地土地’? 当时我做好汉,专一吃那歹人度日,受用腥膻,其实快活。偏你出家,教我们保护你跑路!原说只做和尚,如今拿做奴才,日间挑担牵马,夜间提瓶焐脚。这早晚不睡,又叫徒弟作甚?”三藏骂道:“你这夯货越来越不成器,我就叫声‘徒弟’, 他就有许多话头。”大圣道:“师父甚事?”三藏道:“我刚才伏在案上打盹,做了一个怪梦。”行者跳起来道:“师父,梦从想中来,你未曾上山,先怕妖怪,又愁雷音路远,不能得到,思念长安,不知何日回程,所以心多梦多。”三藏道:“徒弟,我这桩梦,不是思乡之梦。才然合眼,见一阵阴风过处,禅房门外有一朝皇帝,自言是乌鸡国王,浑身水湿,满眼泪垂。”这等这等,如此如此,将那国王之事一一说与徒弟。行者笑道:“不消说了,他来托梦与你,分明是照顾老孙一场生意。必然是个妖怪在那里篡位谋国,等我与他辨个真假。想那妖魔,棍到处立要成功。”三藏道:“他说那怪神通广大哩。”行者道:“怕他什么广大!早知老孙到,教他即走无方。”八戒道:“师父一个梦,猴哥也认了真。我每天做梦想那两个小子,醒来一回也没见着。”三藏道:“那妖怪已是国王,且又风调雨顺,且拿什么由头去擒他呢?”大圣道:“不消多说,今晚且睡,等明日我先进城,观望观望再说。”八戒道:“这鬼皇帝净打扰我做梦。”说着,师徒们息灯安睡。不知明日大圣捉得捉不得妖怪,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