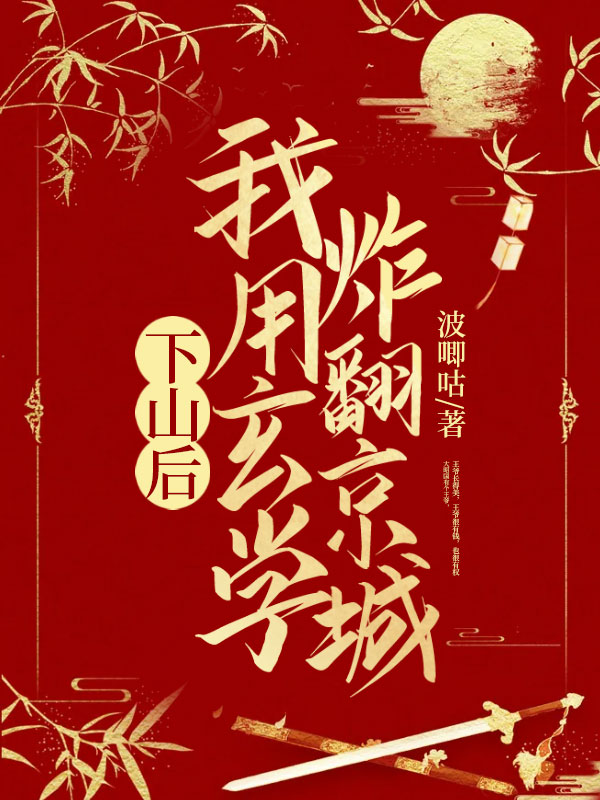“那还是执念。”
唤无余再一次的说道,又拨弄着火炉中的火,火光应在其脸上,眼里充满了的光。
“都说了,不是执念。”
顾言想要争辩起来了身,抬起头,一双眼睛撞上了唤无余的视线,两人就这么对视着。
唤无余直视着顾言的眼睛,缓缓说道:“光明大神官听奉昊天的旨意,向世人播撒光明,驱逐黑暗,对于十几年前冥王之子的事情,想必你一定知道。”
顾言直视他,眼里没有刚才那份懒散,有着的是一种让唤无余都有退意的锐气。
“如果冥王不是冥王呢……如果这里天书就是一个骗局,你怎么办?”
顾言没有继续说下去,反而换了一个话题说道。
唤无余抬头又低头,在望向她的眼里时,他看到了一种执念。
冥王不是冥王,这一句话他曾经听那位老人说过,只是斯人已不在,这些事情也都长埋于心底。
“你是未来的光明大神官,当真是敢说。”
唤无余站起了来,背着手抬着步子,走到了门前。
转身,他看着那盘坐在床上,只穿着很单薄的衣裳的顾言,细细观看良久,在他的眼中,她现在的样子好熟悉。
“哈哈哈哈!”
突然,他笑了起来,不像嘲笑,倒像为了两个人同归殊途的结果而笑。
“顾言,其实不管怎么样,你是不是伟大的光明大神官,我们都是一类人。”
“一类人?”
顾言不懂他的一类人,是指什么方面。
说着,他伸出手,对着天的方向一望,铿锵有力吐了一个字:“魔!”
他望着顾言,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那一抹黑暗,那是快要入魔了,他太熟悉了,熟悉到一眼就能看见。
之所以要大笑,是笑那光明,笑那西陵,也笑着光明神座。
“我曾经相信昊天,是因为光明大神官的命令无错,可现在看来,我有些质疑他了,光明不是光明,这天也不是这天,不管他们是不是冥王之子,还是错杀,现在已经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本天书,那本书可以逆天。”
他拿着脸上带着笑意,似乎说着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顾言心中暗暗作痛,似乎有一种想杀了他感觉。
质疑昊天,是要挑天下之翻覆。
这要是搁在历朝历代,满门抄斩,你家的鸡蛋,都得给摇黄,门前的蚂蚁窝,都得浇上热了水银。
更何况是信徒满天下的西陵,虽然在唐国影响力很小,但在唐国的西陵客卿不少。
顾言看着唤无余,面色复杂。
以为他只是简单的入魔,可没有想到,竟然有如此豪言壮志。
这千年,出了多少英雄豪杰,又吞没了多少英雄豪杰。
希望他不是以卵击石,最后化为乌有。
顾言看着他,想起了那个暮年的老人,想与天斗,雄心壮阔他不惧一切。
天启六年,那一年顾言从光明殿出来,停在门外不远处,往天上望。
掌教神殿宫墙甚高,高的遮住了东升的太阳。
作为整个西陵最高的建筑,最高的权威,自然是其他三殿之上,也必然高处不胜寒。
她摸着了腰中的那个东西,也不知道他们是没有搜到,还是其他的,依旧在她的身上。
在当时老掌教没有给她东西,是假的,但是他的话,至今她还是不怎么太明白,顾言望着手中的令牌,那令牌由特殊的材质制成,里面的凹槽可以说,连唐国的军部,天枢处都无法完全复制,这个材质不同于青铜,令牌不知材质,很轻。
这个令牌,可以调动西陵三殿包括护卫骑兵,虽然也包括西陵客卿,但他们听不听调令,似乎也没有什么用。
火光映射着她的眼睛。
从当年受老掌教点化之恩,她也许就已经注定脱不开这因果。
天启羽化前的那般话,让顾言至今不能参透。
顾言无力地握着令牌,若是你不是卫光明弟子,她也许只会做一个闲云野鹤似的人,可你不是,以后的西陵,不管变成什么样子,西陵需要你。
这一句!
老掌教在她拿过令牌后,才语重心长的说道。
甚至顾言怀疑,他就是故意的。
这一接,老掌教,你可是害惨我了。
扯嘴淡笑。
报了我那仇,见了那西陵无事,依旧屹立在世界间,成了你的心愿,也完成了我的心愿后,我便归去,过我的小日子。
光明大神官爱谁谁去接受,爱谁谁去当。
摸着令牌,顺着唤无余,笑着说:“我还是那句话,人不要期待的太满,因为会很失望的。”
“行,话我说到这里,等这件事情完成之后,你回去你的西陵当你的光明大神官。”唤无余说道。
回去?希望到时候,他不会卸磨杀驴,逼得自己无路可走了。
……
……
在和唤无余聊完了第二天,部落笼罩在一片动乱之中。
到处都在四处奔走,收拢帐篷,驱赶牛羊,准备干草粮食,似乎在准备离开这个地方。
白岚时常摆弄药材,一些新衣服掉在了地上,似乎也不关心,在摆弄好药材良久后,眼瞅着心满意足后,才缓缓收拾着衣服。
顾言依旧懒散的躺在床上,看着白岚在收拾行李,说道:“你也要跟着去?”
“不去,就是光收拾东西,准备迁徙。”白岚低着头说道。
“迁徙,你们是要去温暖的地方而是去找草场放牧?”顾言又转了个身回答道:“不对啊,这大雪天的你们确定能分辨出方向,不应该是等开春才迁徙的吗?”
“我也不知道,就是得到了族长的命令,所以才准备走的。”白岚拨浪鼓似的摇头说,后面那两个辫子被她甩的翩翩起舞。
“没有说什么吗?”
白岚又摇了摇头。
顾言沉默,侧身躺着,看着白岚又想起了什么。
“你父亲不就是族长吗?”顾言问道。
白岚没有说话,手上的动作也停了下来,用眼神询问,似乎也是这么一回事。
白岚望着顾言,对着她说道:“我父亲虽然是族长,可有时候不能耐着性子来,必须以族人来着想,十几年前是的,现在也是。”
说着,她总是泪眼摩挲。
自己的父亲,常年在外,已经很少能回家了。
就像是当年的一模一样。
从前,父亲出征狩猎,或者打仗的时候,白岚常常看到母亲一个人坐在房里,看着空空的小院,空空的房子。
那时候她常问,父亲,什么回来,为什么要出去打仗。
母亲总温柔,把她搂进怀里,宠溺地揉了揉她的脑袋。总是摆手,笑眯眯地说:打仗就是出去打人,保护该保护的人,不管对面是否强大还是弱小,等过几日,就回来了。
母亲总是在张望,张望在的父亲何时归来。
父亲回来后,以为有好日子过了,可没想到带来的是万里的驱逐。
白岚还记得部落远来这里的第一年,下着的雪,满山遍野的豺狼,和一心想抓我们当奴隶的左帐王庭的人。
父亲再一次踏上了征途。
那时候母亲总是爱拉着她到处跑,那时候,母亲轻轻的摘掉她头发上的雪花,那时候,白岚看着病床上,已经骨瘦如柴的母亲。
在驱逐的路上落下的病根,到现在已经无法改救她的命。
直到母亲病逝,父亲仍在征途的路上,回来时只能以人看新坟,烧着那些母亲在世也认不得几个字的捷报,和说着自己的儿子如何英勇的事迹的文书,又如何保护该保护的人而战死沙场的他。
从小睡前,喜欢讲故事的母亲那时候是她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候。但已经不在了,白岚每想着这些就会睡不着觉。
听着顾言给她讲的故事,给她讲着这十几年来她不曾去过的风景,讲着长安城那些药材在一个铺子都能买到的地方,她非常的向往。
只是这一次的迁徙,不知道,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她了。
她真的希望顾言多待几日,多待一会儿。
想着想着就竟然哭了起来,让一旁的顾言都不知所措。
看着面前向着泥娃娃的她,顾言有些心疼:“别别别,怎么了你。”
说着把她拥入怀里安慰。
白岚低着头,良久,平日清脆的声音颤颤着:“能在给我讲个故事嘛。”
良久,才听见那一声。
“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