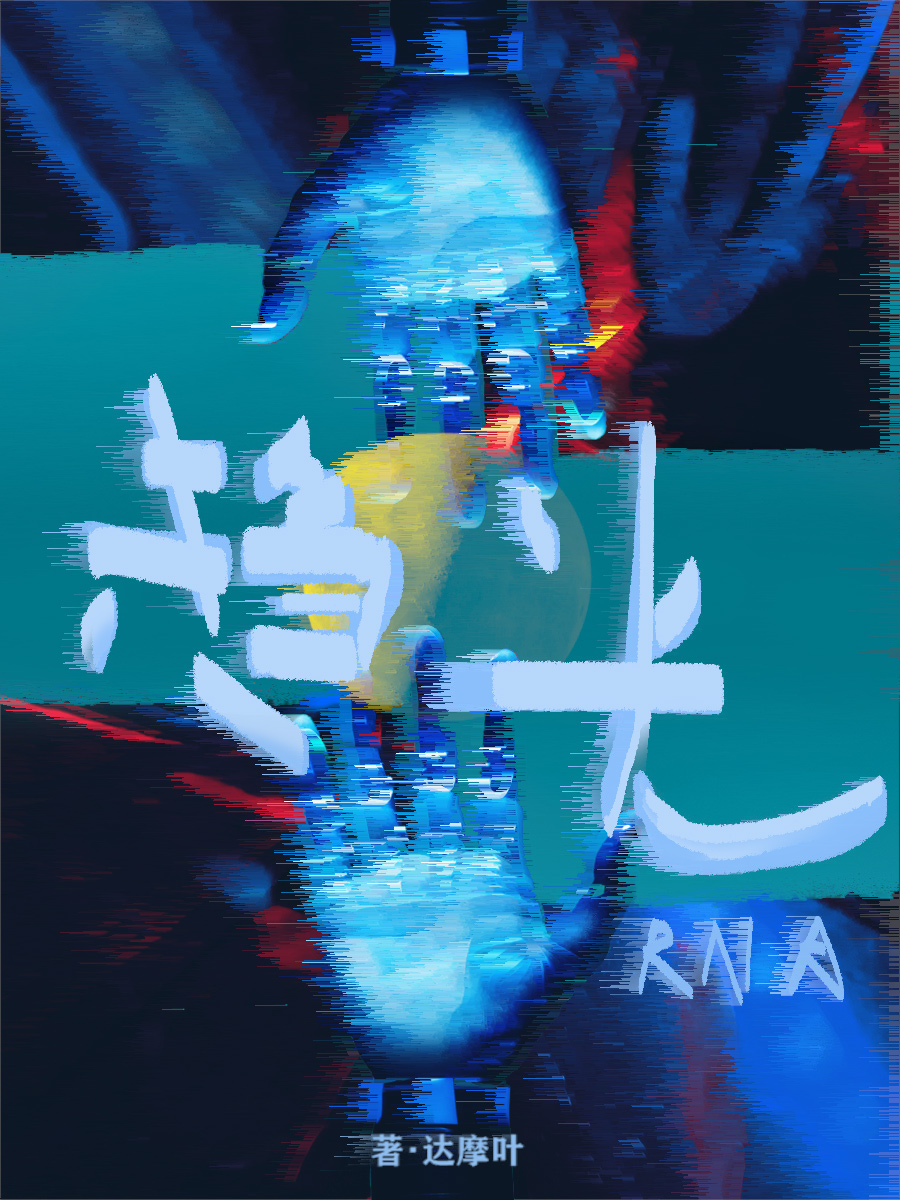医院中。
易青原静静坐在病床边,静静凝望着沉睡中的女儿……心,再不可能完整,肚肠纯青……
耳边响起鞋底与地面轻微的刻意的摩擦声。他的头似转非转,脸上的泪痕迫使他不能把头转动更大的角度。
“这些人怎么处置?”身后之人低声询问。
易青原忽然不敢再看女儿沉睡中,伤痕遮掩下苍白的面容。他的脸一下下绷紧,眼神瞬即变得阴森冰冷,终于,他说:“净身吧!让他们活着!”
身后似乎犹豫了一阵,易青原眉心一拧,就听身后的声音举棋不定:“有一个年轻人……没动”
易青原眉心更紧!
身后之人沉默数秒,转身而退。
“老李!”易青原叫住身后,那人正是易家安保负责人——李叔。“你跟着我多久了?”
身后稍加思索,回答道:“十五年六个月零三天!”等了片刻,见易青原再没有说话的意思,最后说道:“这事之后,我托人把右手(自己的右手)送来!”
何时,易青原的身后空无一人。
女儿的脸上,还残留着野兽的爪痕,易青原胸中窒痛,左手按在心口,搦皱了胸口纸白的衣衫。
何时,有脚步声背后响起。
来人,站在他的面前,挡住了女儿的脸。
噼!
是一记反抽,易青原头被打偏,嘴角顺嘴流血!
“滚出去!”
来人色厉而阴冷,阴冷的目光中,透骨的悲伤与绝望。
易青原偏回脸……他还想再看女儿一眼。
噼!
又是一记!
仍然用尽了全力!
“滚出去——!”
声嘶力竭的吼叫,凄厉不似人声。
如撕裂的心,破绽出绝望嘶鸣……
一记同样重的耳光,如可摧枯一切的利刃,生生斩断他眼中的忏悔和念想……
重症监护室中。
青青面容苍白憔悴,布满畜牲的抓痕……她的脸的底色,和她身上的白衣一样白,像一个纸人。
床边监护仪又发出尖锐的滴滴声,屏幕上的某些波形变化又揪扯住青青的心,心,早已比波形还乱。
身为一名出色的神经外科医生,这种警报意味着什么,她比谁都清楚。
他已经不能承受二次手术,不能……
青青不停亲吻他紧闭着的青紫嘴唇,不停亲吻他紧闭着的眼睛,源源无尽的眼泪,串串坠落他的眉心;
抚在他腹肌上的手,因为紧绷的腹肌而颤抖,她苦苦哀求,求他放松下来。
青青拼命压抑着,低低哽泣,清水鼻涕流在他的脸上……温热的水,带着体温,释出股间,顺着裤管流湿了袜子,她再管不住它。
青青苦苦哀求他
“求求你……求求你……”
“我不能没有你……”
不能没有你……
不能……没有你……
也许,他听到了耳边的哀唤;
也许,是无限依恋的吻起了作用;监护仪上的血压波形渐渐趋于平稳,最终变成循规蹈矩的贪吃蛇。
双腿,再没有力量支撑本就纤柔的身体,青青扑通跪跌下去,仆伏在床边,泣噎到上气不接下气。纸一样白的小手,无意识游走,虚抓;似想要抚摸,似想要抓住……躺在床的上人却似乎什么也感觉不到。
滴————————!
警报器突然长鸣!
所有的热流瞬即破体而出!
所有的热血全都涌入脑海!
青青猛惊抬头,两条直线突兀地横亘在瞪大的双眼中,仿佛生生将她的美丽而绝望的瞳孔无情地撕裂!
忽然,天地为之一黑……
晶晶尖叫着张开双眼,她在恶梦中惊醒,浑身透湿!
她做了一个先美后恶的梦。
梦见一对恋人正在光天绿草地上尽情嬉欢追逐着,一望无垠的青草地,有微丘起伏。风儿吹在脸上,美丽的女子却分不清微风是微凉还是微暖,那风抚过耳际,吹得心痒。蓝天深而且湛,又深邃,仿佛永无止境,又见天际的两端挂着两颗太阳,一个稍大,一个稍小,有热度,又像没热度,她总感觉太阳的亮度不够,就像挂在天幕两端的两盏不等远的日光灯?
天幕的背后悬浮着几颗行星——美丽的行星;其中一颗最大的绿白色条纹的巨行星几乎占据了视界中,三分之一的天空。
远方,起伏的青丘后面似有一片攒动的黑影,那影很黑,黑得发亮刺眼。
再近些,竟有数个之多。
一群黑狗!
通体黢黑的黑狗,每一双狗眼都发出慑人心魄的黑光!颤卷着的长长的黑舌头随步而颠,齐头并进,冲耸着,正向这边狂奔而来!
仿佛有瞬移之能的黑狗群转眼就到了女子和男子跟前,可他们正忘情地躺在和煦的阳光下拥吻。
女子情难自抑,急不可耐,早已把自己剥了个精光,她翻身而上。
至关键时,凭空炸响刺耳嗥叫:
呦!一对野鸳鸯!……
狗群,眨眼幻化成凶煞样人群……
他……仿佛一个远古时候,为战而来的天之使者,挡在心爱的,美丽的女子前面,用无畏的生命,守护着女子的贞洁;
他浑身浴血,却毫不吝惜周身源源流逝着的鲜红的生命!
他的生命点点滴滴从他的身上流逝而去,精与力渐渐枯竭。久攻不下的人群因受伤而躁狂,便渐渐显出黑狗的嘴脸!
一条最大、最凶狠的恶狗凌空从他侧后扑上,空中幻化成人的形状,弯身后折,形如钩月;
日光之下,划出一道凌厉刺眼的寒亮光弧……
“东野承欢——!”
晶晶撕心裂肺大叫!
白顶、白墙、白床、白窗,一切都是白的……!晶晶浑身是水,又痛又酸,疲惫之极!
一动之下,下身牵动的痛楚依然使她倒吸一口凉气,她咬着牙,挣扎着爬下床沿,就摔了下去。
一个泪流满面的女人,冲过来赶忙将她搀扶,那女人美丽雍容的脸因痛苦而变了形状,晶晶竭力挥开她的手,不愿接受她的搀扶。
她艰难爬起,身子摇晃,拉断了的输液软管,针头还插在手上,血和水逆流而出。那女人不顾一切抢上,拔下她手背上的针头,用力捏住那个冒血的针眼。
晶晶再挥开她,挥不动!
再挥开她的手……
“他在重症监护室!”女人住脚在病房门口,手扶着门墙,声音颤得厉害,也似乎只有手扶着门口,她才得以保持站立。
晶晶扶靠着走廊的墙壁艰难前行,没有回应,仿佛什么也没听到。
股间撕裂一般随步而痛,她皱紧了眉间;
淡红的血,顺指而下,垂悬中指指尖,落地无声……
那女人嘴唇发青,颤抖得厉害,眼中摇晃着的身影扶墙远去,越来越模糊……莫大的不可抗力将她抽空,柔软的躯壳贴着门框滑坐在冰冷坚硬的地面,头抵住门口的墙棱,一只手拼命推着另一只手往嘴里塞,眼泪鼻涕齐流……
青青被动睁眼,一个声音模糊响在耳边:“他没事,是你的手碰掉了电极”
——这!是天上地下,最美的声音!
青青的世界,山呼海啸而来!
灵魂猛然归体的青青大力推开谁人的搀抱,张大了双眼,她跳起来冲向那张床,就从床上重重摔跌下去。
她不知道,自己何时竟躺在床上——一张应急安置的简易病床。她全不顾膝上、肘上、股间的剧痛,连跪带爬冲到床边,余光只在时间之外就从监护仪上捕获足够量的信息,她不必将屏幕信息换算心的消息,心就安定;她双手按住床沿,撑起身,闭上眼,激越的唇,附上亿万柔情,深深吻上那片微丘起伏的软韧腹肌。
唇上,传来他的体温,和流入唇间,热泪的咸……
一个身穿病号服的女子出现在病房门口,她形容憔悴而苍白,仿佛被野兽乱蹄踩践过的那朵孤单的花;又像躺在张麻子寿衣店角落里待售的没有血色的白纸人。
站在青青身后的男医生看到她,面露不忍,忙走过去扶她,女子却挡开他的手。
她的眼里只有那张沉睡着的青肿变形的脸……
她跌跌撞撞,摇摇晃晃来到床边,跪跌在青青对面。
她很小心、很小心附耳在他心的位置,倾听那一个足够她勇气活下去的律动;
若没有,一切都没有……
他,还活着,没有醒……
手术成功,也不成功。
是青青身后的那位男医生为他主刀,钩针上的倒钩损伤了部分脑组织、区域性出血;他不是青青,但他尽力了。
那当时,青青昏厥在病床上,下体大出血。
那位男医生姓李,就是青青为惠珍做手术时的一助,本也是一位技术过硬的主刀医生,只是当时情况不容乐观,好几位专家高挂,李医生一直心仪青青,顶压而上……
李医生,终不是青青。
二十四小时后,他还没有醒来。
晶晶守在床边,困倦疲累,摇摇欲坠,她没办法合眼。青青在她眼前晃动,为他做着什么,晶晶看不懂,胸中莫名火起。
第一次,晶晶对青青生出恨意,深深的、单纯的实质恨意!她恨青青没为他做手术;
明知天意难违,她就是止不住恨她!
晶晶的恨,青青感受不到,她却清楚知道,因为那恨,就在她心里。
终于,晶晶再无法忍受恨的折磨,扑到青青怀里,抱住她咬她的肩膀。她痛哭气噎,呜咽着上气不接下气:
“要你……有……什么用!……要……你……有……什么……用!要你……有……”
……
要你,
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