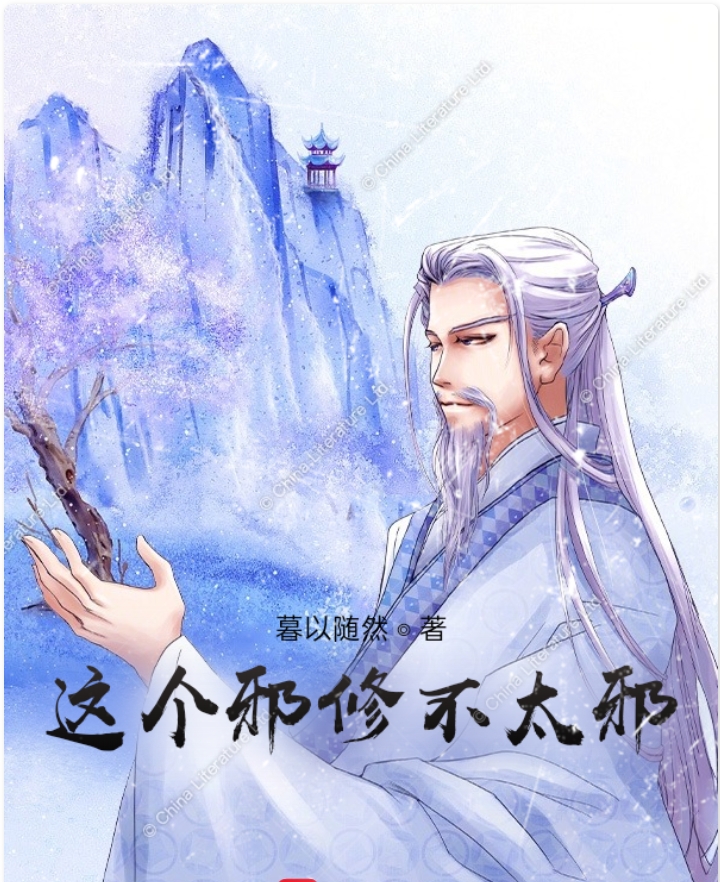半年后。
“老少爷们,今天东家办的这叫喜丧,老太太98了,无病无灾,寿终正寝。哎,东家说啦,喜丧就得办的热热闹闹的,您各位见证,谁要是没使出吃奶的劲吹,谁不是人养的。”
王春生拿着话筒,大声的喊着,果然,上天不养无用之人,会点手艺总不至于坐吃等死。
苍天不负,祖上赏饭,凭借着会吹唢呐的手艺,方圆五里十里,倒还挣了个喝号。再约上几个会其他乐器的,组建了一个乐队,这个乐队和崔建他们的摇滚乐队还是有点区别,主要是针对的项目不同,确切的说,王春生的这个乐队比较亲农。因此他也是名震各村。
专业承接各种红白喜事,开业,过寿等等业务。
一群围观的老少爷们被他刚刚的几句土话逗得哄堂大笑,甚至还有年轻的小伙起哄,“鱼尿(sui)泡,恁家闺女该说老婆婆了不,你看我咋样。”
他们全然不顾这主家的丧事。因为人死了,就什么事都管不了了。
这真验证了一句话,眼一闭,布一盖,全村老少等上菜。
鱼尿泡便是江湖上给的喝号,常吹唢呐的人,没有一个能避免的了的。因为它出现在两腮处,是用来存气的,越大存的越多。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的熊样,你给俺闺女提鞋都不够。”
王春生这样的场面见的多了,立刻给怼了回去。
“是的吗,赶明我给她提提试试。”
又是引来一阵哈哈大笑。
“静一下,静一下,下面咱该烧纸啦,抬桌子,上贡的人都到位。”
村里的知事兼村支书刘立民,过来拿过王春生手里的话筒,说道。
紧接着,在刘立民的安排下,各项工作有序的展开。
王春生也招呼着队友,吹笙的老胡,老张,铙钹的是老丁。四人准备着开始了。
至关重要的总是头一场,娘家人的二十四拜,则是考验王春生等人的专业能力的时候,因为这二十四拜,完成需要一个多小时。没膀子力气,吹不了唢呐。
而今,在诸多城市,这种气势磅礴的二十四拜,显然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因为大家都很忙。因为明明只需要三个躬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还要用它?费时费力,还没有人能看懂。
所以不是每项传统都那么的幸运,它总是会在不合时宜的时候被人们所抛弃。
而办丧,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不是繁文缛节,是出于对死者的尊敬,人们往往都会或大或小的举办一场丧礼。
…………
这一年,春晚上来了一个腼腆到有交流障碍的男孩,他带着一首歌曲走进人们的心里,从此这个男孩便被冠上忧郁的头衔。
不光如此,春晚之后,他的歌曲便充斥着世纪末的各个角落,到处唱的都是白桦林带来的忧伤。
王一鸣和王一文悠然的走在街上,这是一条和浪漫并不匹配的街道,因为只要是能看到的墙,上面都写着三珠口服液或者脑黄金的广告。
这是90年代吴炳新首开先河的杰作,将广告打到农村各个角落。全新概念的营销模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只是这个时候的三珠已经销声匿迹了。同样,史玉柱再高的智商也没能力挽狂澜,让脑黄金起死回生。
这天天气格外晴朗,没有了夏日炎炎带来的焦躁,微风拂面,带给人秋高气爽的感觉。
走在人山人海的街上,音响店会告诉你,今年流行什么歌。
去年王一文经历了一次惊吓之后,刀疤脸便没再出现过,王一文也算安稳的步入高中生活。既然没有什么意外,王一文不再多想了,渐渐的她将这段记忆封存了起来。但她挥之不去的还是那眉宇间,一丝浅浅的忧伤。
王一文左看看右看看,耳朵里时不时的传来白桦林的旋律,她便会问,“哥,你说朴树为什么会唱出这么忧伤的歌?他才多大呀?很难想象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总感觉他有着不符合他年龄的忧伤。”
王一鸣说,“这个我知道,刘铭全跟我说过。这是二战时期,发生在苏联,一片白桦林里的约定,一个爱而不得,孤独守候的爱情故事,故事的结局很凄凉,也很悲惨。女主角等来的是无言的结局。”
“故事悲惨,歌曲也写的忧郁。怪不得听了也会有感同身受的感觉。”
王一鸣敲打着王一文的脑袋,说“你才一个高中生,你懂什么是忧郁么?”
“不懂,有可能是与生俱来吧,反正听他的歌,真的能产生共鸣。”
“你应该换换口味,多听听健康歌之类了,别总是忧郁忧郁的,你再抑郁了就麻烦了。这可是个怪病,听说香港那边有好多人都有这病,每天就是琢磨着怎么才能死。”
王一文没有说话。
过了好一会。
“哥,我退学了。”王一文直接放出了王炸,就好像她已经酝酿了很久一样。
“什么?”王一鸣瞪着不敢相信的眼睛,问道。这对于王一鸣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真的,我已经决定了。”
“是不是又出什么事了?是不是他又出现了,妈的,回头我弄死他。”王一鸣气的直打转,连声逼问王一文。
“没有,和你当初一样,我自己的将来,我要自己做主。”
“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学习,你是高中生了,做事情心里要有分寸。”
“我想离开这里,去打工,去挣钱,我不想再看着你们省衣节食,而我却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王一文有些哽咽的说。
“不对,文文,你告诉我,你肯定没说实话,他是不是又找你了,是不是?为什么你总是要自己承担呢?难道我就这么不值得你去相信吗?”
“没有,哥,我过的很好,你们也都对我很好,他也没再出现过。可是我不喜欢,你们对我越好,我的心理压力就越大,我不希望你们为了我,就不顾一切去挣钱。”
“我们乐意,不用你来操心,你只要安下心来。不要想太多就行了。”
“可是我做不到,看着你们那么辛苦,我不想活的没心没肺。”
“不对,这不是你真正的想法,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也根本不会想这么多。”王一鸣疑惑道。
“走吧别瞎猜了,我已经决定了,学费都让我要来了。今天我也想痛快一回。”王一文拉着不情愿的王一鸣进了一家专卖店。
。。。。。。。
“哥,你说朴树还会写歌吗?他下一首会不会也像白桦林一样忧伤?”
王一文把学费花光了,挽着身着光鲜的王一鸣,在街上漫步走着,眼睛注视着半空中时不时凋零而落的树叶。
“不知道,也许会吧。”
“我总感觉,他内心有着不属于他这个年龄的悲观世界,也不知道他的成长都经历过什么?”
王一文像是在自言自语的剖析着朴树的一点一滴。
正当他们兄妹快走到街道尽头时,公交车上一个英俊帅气,穿着花了唬哨的少年冲着他们打招呼。
今天因为王一鸣请假,特地请了他来替班。
香港有新四大天王,其中虽然郭富城跳舞很出名,但对于内地来说,最出名的还是他的发型。
“你好美女,坐车吗。百货大楼直达。”
眼中透露着挑逗得眼神。
“你要注意你的形象,你带的可是我的工牌。别等你走了,给我留个流氓的名声。”
“你懂什么,这是时尚,是不,妹妹。”
刘铭全根本不理会王一鸣,依旧看着王一文说。
“哎,对了妹妹,最近王杰又出新歌了,要不要听听。”
刘铭全说着还不忘了哼上两句伤心1999的音调。
“全哥,你说的是那个14岁就开始写歌的王杰?唱过一场游戏一场梦?”
王一文显然有点激动。半年前的那件尴尬的事,两人都心照不宣的没再提过。
但从那以后,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你也了解?太好了,上我那,他的歌我那全都有。哎,你也去,省的你再说三道四。”
刘铭全抬了抬头,拿出厌恶的表情看了下王一鸣。
“原来我在你心里还活着呢。不去了,今天回家要挨训了。”
“咋了,哟,看你今天穿的那么风骚,说媒去了?没谈成吧。”
互相贬低成了他俩默契交往的重要工具。
“注意你的用词,那和你是不能比,你大学生,你长的多帅,就凭你的汉奸头,我们就比不了。”
王一鸣回怼。
“我这是郭富城好吗,刚焗的油。哎,我这有刚出的古惑仔看不看?”
“没空。”
“堕落天使,看不看。”
刘铭全坐在车里,敲着车皮,用隐晦的语气说道。这种暗示,王一文是不懂的。
“改天改天。”
十八九岁的年轻小伙,听到这种电影,内心都会蠢蠢欲动的,王一文却不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东西。
“没事带咱妹妹来呀,真的,妹妹,我知道你好听歌,我那港台名歌多的是。今天不上课吧妹妹,走着。”
刘铭全的家底的确很丰厚,他妈在城里留给他一套两居室,这是他的私人圣地。里面陈列的东西都可以抵上一个音像厅的资源了。
“上什么课,不上了,非要出去挣钱。”
“别呀,妹妹,听哥一句,别太草率。哥马上南京走起了,临走前,哥觉得有必要纠正一下你的思想。你单独来找我,咱俩单聊。”
“刘铭全你什么意思你。想打我妹的主意?”
王一鸣一听这话音就不对。这种警惕是在王一鸣6岁时第一次遇见王一文时,留下是模糊的概念。
“我走了,东西都给你了,你怕什么,再说了,我们只是推心置腹的单纯的聊聊天。我还能吃了咱妹不成?”
“全哥,你要和我聊什么?”
王一文,问。
从整体上来看,王一文从认识刘铭全开始,并不讨厌这个有点吊儿郎当,说话不太着调的人。但自从那次被看光之后,仿佛有种“你要对我负责”的态度,对他的好感倍增。
或许是因为她的内心渴望被人关注,又或许是刘铭全的见多识广总是能给她带来新鲜感。
“花前月下,紫滕树旁,聊人生,谈理想,反正能聊的太多了,记得明天来。发车了,记得明天来。”
一股子黑烟,从车屁股那喷射而出,呛的人不得不闭上眼,捏着鼻。
好一阵才散开,王一鸣看着车离开的方向,一路上的尘土飞扬,刚想骂上两句,不经意间瞥见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转眼进了某家门店,消失不见了。
王一鸣又来回找了几遍,那身影好像从没出现过。
“哥,咱去找咱爸吧,顺便让他试试新买的鞋子。”
“找咱爸干嘛?找打呀?你看刘铭全,多好,你要是考个大学,去看看外面的花花世界,我们爷俩也都能替你高兴高兴。多好。”
“哥,咱能不提这事了吗?我没那么聪明的脑子行了吧。”
“你小时候可比这听话多了,好好,不提不提。”王一鸣一看王一文的脸色不太好,索性不去挑战她的耐性了。
一路上,王一鸣被突然出现的身影打乱了平静的思绪。他的内心开始犯起了嘀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