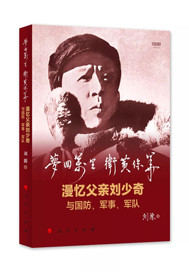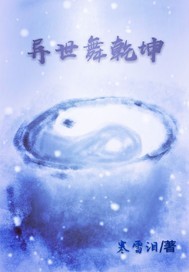山春花喝了一碗热粥,便将自己关在了厢房里,不肯出来。
山二郎拍了拍好奇不已的三柱,“再瞧你就迟了,记住别跟别人说你小姑在咱们家。”
三柱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却乖乖地点头,做了一个捂嘴的动作,表示自己不会泄露消息,看了看日头,着急忙慌地跑了出去。
“你们不是去石垭村了吗?”杜盈秋给山二郎和文县令盛了粥,目光瞟了一眼房门紧闭的厢房,“春花她怎么跟你们一起回来了?”
文县令和山二郎两人无奈地对视了一眼,最后还是山二郎道清楚了原委,“不是跟我们回来的,是我们偷偷把她从石垭村带回来的。”
自从二房搬到县衙后,一家三口加三柱都忙得脚不沾地。
杜盈秋当了锦绣阁和官府的中间人,锦绣阁出绣坊和绣娘,官府出资助以及销路,筛选手巧的流民妇人教授织布和刺绣。
两个小娃娃,三柱要念私塾,山桃要去保济堂坐诊学医,时不时还跟着纪大夫出外诊。
担着师爷差事,山二郎跟着文县令忙着安置流民缓解灾情。
一连近三个月,青山村都没回一次,也不知道杜氏主屋那头又闹了幺蛾子。
“石垭村地少人户少,地高缺水,这回到没怎么糟灾,去也不过是正常训视。没想到在那碰见了春花……那家人说是花了大价钱娶回来的媳妇儿。”
听了山二郎这话,杜盈秋不可置信地抬起头,“春花今年才十一?离及笈都还有几年,怎就如此匆忙的嫁了?”
就算及笈的女子,其实身子也还未发育全乎,过早行房事有害无利,门第高些的,往往会将女儿多留几年,但也不过二十。
但无论富户农家,断断没有嫁十一岁女儿的道理。
杜氏如何将山春花嫁去石垭村的尚且未知,山春花被他们遇见的时候,正在河边洗衣裳,还有几个年纪大的妇人盯着她。
穿得单薄简陋不提,原本清秀的少女,露在外的肌肤遍布伤痕,畏首畏尾,完全没有在青山村时的傲气。
趁着那些妇人不备,山春花偷偷向山二郎求救,只叫了一句二哥就已经哭得不成样。
文县令接过话头,眉头紧缩,“石垭村日子苦,男多女少,娶上媳妇儿多半靠花钱谋娶。整个村子的人倒是心齐,对外什么也不肯言。将山春花偷偷带回只是权宜之计,石垭村的事还得细细查摸……”
听了大人们是谈话,山桃回屋翻找了一些外用的伤药,走到厢房敲了敲门,“小姑,是我,山桃。”
厢房中静悄悄一片,山桃耐心地等了一会儿,也不催促,以为山春花睡着了准备离开的时候,才听见一句沙哑的应答。
“进来吧。”
明明春光正好,山春花却将窗户都关地结结实实,自己也缩在床头,用被子紧紧裹着自己,红通通一双眼睛,失去了所有光彩。
“我以前瞧不起你,还嫉妒你,现在看我如此,是不是觉得我遭了报应?”
山桃端着木盘放到床边小几,坐在床沿上,朝山春花伸出了手,“我是大夫,只会把你当病人看待。”
“对,没错,你是咱们村有出息的小大夫。”山春花紧抓被子,气息又急促起来,“我什么也不是了,娘眼里只有三哥,我只是卖钱给她儿子换束脩的货!”
对着其他人,山春花不发一言,看见了山桃却歇斯底里,破罐子破摔一般,将心里的不平和苦楚都倒了出来。
山桃也没说话,依旧保持着伸手的姿势,静静地看着她似哭似笑。
“家里没钱了,三哥,不,山三郎不下地做活,什么都压给了我,我快累死了,可娘只想着如何给他凑钱,还想将他送去府学……她把我卖给了石垭村的鳏夫,三十多岁,打跑了两个媳妇,我亲娘,要我嫁给这种人……”
通红的眼眸黯淡无光如鱼目,山春花喃喃道:“她是要我死…不,我娘根本不在乎我的死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