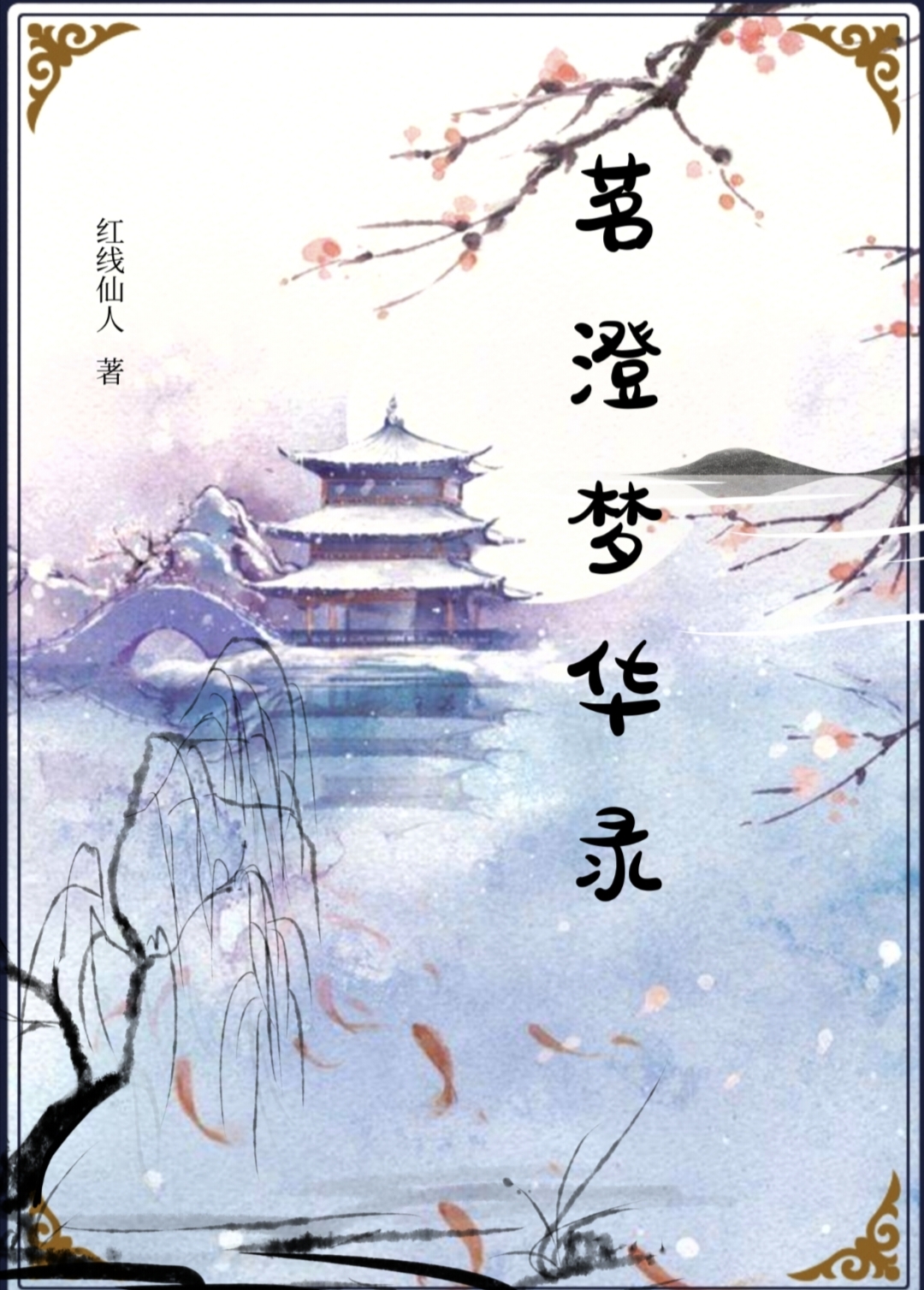吃完饭,杨肜起身说:“我来结账吧。”
姚濯也起身,说道:“还是我来结账。”
两人都走到柜台,杨肜说:“老板,结账。”
老板嚼着槟榔,口里有些含糊:“一共一百二十五。”又指了指二维码。
杨肜说:“什么,二百五?”
老板说:“不,是一百二十五。”这回一字一顿的说。
姚濯说:“肜子,这次算我的,下次你请好吧?”
杨肜没理会他,只管扫码,把钱一付,说道:“好了,已经付了。”
姚濯心想:“这个人有点实诚。”无可奈何的笑了笑说:“谢谢。”
杨肜说:“不用谢。”心想:“我不欠你钱,墙角是要挖的。”
下午休息了一会儿,又练了两个小时的游泳,这才结束。
四人在游泳馆分手,杨肜见姚濯也骑了摩托,心想:“这么巧?我的摩托似乎比他的要贵一点。”他终于找到一点心理平衡。
道别离开,杨肜还得将周晓诗送回白沙小区。
到了大门口,周晓诗将身上的夹克脱下来,连同头盔,还给杨肜。
杨肜被风吹得鼻涕都出来了,鼻子一酸,一个喷嚏打出来。
周晓诗问:“你感冒了?”
杨肜赶紧把夹克穿上,用纸巾擦了擦鼻子,说道:“没事。”
周晓诗说:“回去洗个热水澡,好好休息。”
杨肜说:“知道。”戴上头盔说:“走了啊,拜拜。”
周晓诗说:“拜拜。”
看着杨肜骑车远去,她嘟囔一句:“嘴巴一点都不甜,哄人都不会。”
杨肜回到家,洗了个热水澡,觉得头昏脑胀,脚底发虚,没准备电击器,就直接钻被窝里睡觉了。
睡着,睡着,迷迷糊糊看见一个穿着白袍的人来到床边,披头散发,面目却甚明了,也不知是男是女。
杨肜惊讶的从床上坐起来,打开台灯。仔细看他容貌,却是个白色的面具,表情一副眉开眼笑的样子。
他稍稍收起惊讶,问道:“你是谁?”
白袍人说了一句:“你只管随我走就是了。”分明是男的声音。
杨肜说:“走个锤子呀,穿成这样吓唬鬼哟?”
白袍人抬起双手,手势成爪,眼看着尖尖的指甲长出来,用幽幽的声音说:“没错,就是吓唬鬼!”
杨肜瞠目结舌,“啊”的一声叫喊,翻身滚落下床,又赶紧爬起来。鞋也没穿,赤着脚,直往门口跑。
“咔哒”,把门锁打开,拉开门。刚要出去,只见门外站着一个人,身穿黑袍,同样披头散发,脸上戴着青色的面具,表情却是怒相,目眦欲裂,血口獠牙。
楼梯间的应急灯闪烁,杨肜看清那人的脸,好不恐怖,唬得连连后退,心想:“莫非是黑白无常?”不及多想,转身又跑,却见那白袍人已经从卧室出来。他匆匆调头跑向阳台,想要找条出路。可惜他家住四楼,要果真跳下去只怕凶多吉少。
他推开阳台的玻璃门,逃出去,又反身将玻璃门拉上。然后靠近栏杆,往楼下一看。地面满是泥淖,不见树木,也不见其他的建筑,却长着粗壮的怪藤。怪藤叶子稀疏,却有蒲扇大,沿着自己这栋楼房爬上来,直到他阳台外侧。而这栋楼房颜色灰扑扑的,没有一家亮着灯光。再抬头看天,一轮白月当空,不见星光。没猜出是什么毛病,只感觉阴森森,冷清清。
他回头看,只见白袍人和黑袍人已经来到玻璃门口。
他赶紧翻过阳台,手脚并用缘着手臂粗的藤往下爬。没跑多远,就见白袍人和黑袍人站在栏杆边,探头探脑。
杨肜怕他们追来,加快手脚的速度。谁知那白袍人和黑袍人的身躯化作蛇,人头蛇身,一白一黑,从藤上爬下来。
杨肜跑不过蛇,很快被他们撵上。他看两条蛇模样古怪可怕,而下面还剩两层楼,心一横,松开手,直接跳了下去。扑街,脑袋插在泥里。
这泥土松软,掉下来半点不痛。他用双手撑地,将脑袋拔出来,满是污泥。他睁开眼睛,白色的眼仁格外明显。“呸呸”,吐出嘴里的泥,又用手背在嘴巴鼻子上抹了两下。抬头看那两条怪蛇,已经快下到地面。
他不敢多待,拔腿就跑。然而跑了几步就跑不动了,因为腿拔不起来,陷在泥里。
两条怪蛇撵上他,蛇身上化出两条手臂,将他擒住。
杨肜大呼:“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白色的蛇隔着面具说:“你阳寿已尽,还不随我们去阎罗殿!”
杨肜挣扎着说:“什么,我阳寿已尽?”
白蛇说:“没错。”
杨肜问:“那我怎么死的?”
白蛇说:“高烧不退,病死的。”
杨肜说:“不可能,我只是有些些感冒,怎么会死呢?你们一定搞错了!”
白蛇说:“我们是不会搞错了,一分一秒也不会错。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
不由分说,架起杨肜,从泥地里拖走。
杨肜喊道:“不要,不要,我是个好人,不该死的……”
赶了一截路,来到一个水泽边,两条怪蛇拖着杨肜一起钻进水里。
杨肜忙闭上眼睛,屏住呼吸。过了一会,双脚落地,他才睁开眼睛。脑袋上的污泥已被洗净,身上湿答答的。
只见已到了阎罗殿,火烛通明,黑白蛇又化作人样,站在身边。两厢各有一排红胡子的夜叉,表情凶恶,如雕塑一般动也不动。正前方主座上有个戴着冠冕,穿着紫色团龙袍的人,同样戴着面具,表情威严,想必是阎罗王了。身边站着红衣判官,也戴着面具,表情苦戚戚的。座前又站着两人,各着青袍,一者戴着牛头面具,一者马头面具,想必就是牛头马面。
白袍人拱手禀报说:“启禀大王,杨肜押到。”
阎罗王对杨肜说:“你就是杨肜?”
杨肜哆哆嗦嗦:“我……我……”
阎罗王惊堂木一拍,大声喝道:“是也不是?”
杨肜吓得腿一软,跪倒在地,说道:“是是。”
阎罗王问:“你可知罪?”
杨肜摇着双手说:“我不知道呀,为什么抓我?”
阎罗王说:“不知道?来呀,将他拖下去,放在油锅里炸了!”
杨肜一惊:“啊?”
白袍人和黑袍人立马抓起杨肜的手臂,就要将他拖走。
杨肜呼喊道:“不要,不要!”
判官说道:“且慢!”
白袍人和黑袍人一听,止住脚步。
判官对阎罗王躬身说:“大王,即便要用刑,也得有个罪名,好教他心服口服。”
阎罗王说:“嗯,你说的对。”又对杨肜说:“杨肜,你犯了恐吓罪,该当下油锅。”
杨肜惊讶道:“啊,我几时犯了恐吓罪?”
阎罗王说:“还不承认?来呀,将他拖下去,放在油锅里炸了!”
白袍人和黑袍人又要将杨肜拖下去。
杨肜大呼:“不要啊,不要!”
判官说道:“且慢!”
白袍人和黑袍人又止住脚步。
判官对阎罗王躬身说:“大王虽已指其罪名,然而他尚未招认,因此不可行刑。”
阎罗王说:“嗯,你说的对。”又对杨肜说:“杨肜,你认不认罪?”
杨肜头摇得像拨浪鼓,说道:“我不认,我不认!”
“啪”,惊堂木一拍,阎罗王斥责道:“你敢不认罪?”
杨肜说:“我,我没有罪,为什么要认呢?”
阎罗王说:“你快点认了吧,免得大家麻烦,我还得去睡觉呢。”
杨肜说:“啊?”
阎罗王说:“啊是什么意思呢?是认还是不认?”
杨肜摇头说:“不认!”
阎罗王说:“认了吧,认了我就送你回去。”
杨肜说:“真的?”
阎罗王说:“当然。”
杨肜说:“好吧,我认了。”
阎罗王大声道:“犯人已招认。来呀,快将他拖下去,放在油锅里炸了!”
杨肜一听,说道:“啊?不不不,我没认!”
阎罗王说:“他出尔反尔,快拖出去,炸了他!”
白袍人和黑袍人正待将杨肜拖走。
判官赶紧说:“且慢!”
白袍人和黑袍人止住脚步。
阎罗王问判官说:“又怎么啦?”
判官说:“大王,这样不妥。”
阎罗王说:“哪里不妥?”
判官说:“您刚才是放了他,现在又要行刑,也是出尔反尔。大王金口玉言,岂能反悔?”
阎罗王说:“我没说放了他,只说放他回去。”
判官说:“那不就是放了他么?”
阎罗王说:“诶,大有不同。我说送他回去,是炸了他之后,送他去投胎。并非无罪开释,送他还阳。”
判官说:“大王,这样不好。您身为鬼君,怎么能玩文字游戏呢?如此有失您的威严。”
阎罗王点点头,说道:“嗯,你说的对。”又对杨肜说:“杨肜,这回不玩文字游戏了,你快点招认,好让我炸了你。”
杨肜心想:“这阎罗王怕是有点秀逗,我要招认,岂不比你还秀逗?”说道:“大王,我没有罪,放了我吧。呃,应该是放我还阳去吧。”
阎罗王说:“不行。”
判官在一盘提醒道:“大王,你应该说清楚他的罪状。”
阎罗王点头说:“嗯,杨肜,你是否恐吓过王武?”
杨肜说:“什么?王武两次,不,应该是三次欺辱过我。两次是在海鲜酒楼,一次是夺我女朋友,送给我一顶绿帽子。这等奇耻大辱,我也是敢怒不敢言,哪里会去恐吓他?”忽然又想起什么。
阎罗王说:“哼,你进入王武的梦中,变化出他死去的前女朋友文娟,对他进行恐吓,是也不是?”
杨肜眼珠晃动,低头说:“有这么回事,但是那只是个梦呀,我现实中并没有恐吓他。”
阎罗王说:“你即便在梦中恐吓他,也会造成现实的精神伤害,所以不能逃脱罪责。”
杨肜心想:“我还在梦里杀了文娟,他怎么不提?”
阎罗王说:“你可以认罪了吧?”
杨肜鼓起勇气说:“除非对王武进行精神鉴定,证明我对他造成了伤害,否则我不认罪。”
阎罗王说:“哎呀,你还要求这些。”转头对判官说:“做精神鉴定很麻烦呀,不如拿个罪状让他签字画押,然后炸了他。”
判官说:“大王,这样太草率了。我看还是等王武做了精神鉴定,在定杨肜的罪不迟。”
阎罗王说:“不行,今天我非炸了他不可。”
判官说:“大王,这样太草率了。”
阎罗王说:“不行,今天我非炸了他不可。”
判官说:“大王,这样太草率了。”
……
两人重复来,重复去。
杨肜都闷得慌,说道:“你们说完没有呀?快放我还阳!”
阎罗王不再与判官争执,起身走下台阶,站在杨肜跟前,说道:“你说放就放呀?”
杨肜不敢嚣张,侧身躲避他的目光说:“呃……我……”
阎罗王放声大笑:“哈哈……”
杨肜抬头看他,只见阎罗王摘下面具,露出一张没有五官的脸。
杨肜讶异道:“你……”
没面目的阎罗王说:“我不就是我啰。”说罢,手一挥,阎罗殿变成了蜡像馆。牛鬼蛇神都不见,只剩没面目和杨肜。
杨肜站起来,有点生气,对没面目说:“你在玩什么呀?”
没面目说:“嘿,吓到你了吧?出点汗好,可以治治你的感冒。”
杨肜不想被他小瞧了,说道:“我就知道,那怎么可能是阎罗王呢?言语冒失,行事乖张,完全没有体现出阎罗王的庄重。”
没面目说:“说得你好像见过阎罗王一样。”
杨肜用食指挠了挠脸,说道:“我看过电视里的阎罗王,所以我觉得就应该是那个样子。”
没面目说:“可见你的认知是根据别人的思维来的。”
杨肜说:“难道你不是?”
没面目说:“是,但我在努力忘记过去。”
杨肜心想:“真是个怪人。”说道:“我有一件事不明白。”
没面目说:“什么事?”
杨肜说:“你怎么知道我恐吓过王武?”
没面目说:“因为你做梦的时候我窥探过。”
杨肜说:“你窥探我的梦?”
没面目说:“就像你窥探王武的梦。”
杨肜说:“你为什么要窥探我的梦?”
没面目说:“我对你感兴趣。”
杨肜不由得双手护着胸口,用怪异的眼神看着没面目,可惜从他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说道:“你,你干嘛要对我感兴趣?”
没面目说:“别误会,我对你的贞操没兴趣,只是想了解你而已。”
杨肜放下手,说道:“你为什么不在自己的脸上造出五官来呢?看起来怪吓人的。”
照理说没面目也是人,不会没有五官。而他能凭意识制造梦境,想必造个五官不在话下。
没面目说:“我已经说了,我不记得自己是谁。”
杨肜说:“难道连面目也没了?”
没面目说:“连面目也没了。”
杨肜说:“怎么可能?”
没面目说:“你所认为的可能是基于偏狭的认知,而有些东西已经超出了你的认知,比如说魇魔。”
杨肜一想:“有理,不然我怎么会受制于梦呢?”说道:“哎呀,不说这些了。我喜欢你制造梦境的能力,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没面目说:“帮什么忙?”
杨肜说:“呃,实话实说,我喜欢上了一个女人,我想拥有她。”
没面目说:“哼,感情是痛苦的,和女人产生感情更加痛苦。你何必自讨苦吃呢?”
杨肜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不找女人,难道找男人?咦——”想起男人就很恶心。
没面目说:“我可以帮你,不过你要是后悔了,可别找我。”
杨肜说:“那是,我绝不后悔。”
没面目说:“从哪里开始?”
杨肜问:“什么开始?”
没面目说:“帮呀。”
杨肜说:“哦,我需要一个梦境,让我和心爱的女人在里面幽会。”
没面目说:“怎样的梦境?”
杨肜说:“我觉得应该像仙境一样,琼楼玉宇、流云飞瀑、繁花似锦、仙乐飘飘,有燕山之木,有沧海遗珠……”
没面目插话说:“打住,打住,你别说了,我能力有限,造不出如此景象。”
杨肜说:“你刚才不是造出阎罗殿来了么?”
没面目说:“你看到什么了?”
杨肜说:“一间大房子呀。”
没面目说:“对呀,仅此而已。”
杨肜说:“你还把我家也周围改了。”
没面目说:“改了多少?不就是把你住的那栋楼房置于泥淖之上么,再弄些藤蔓?”
杨肜想想,确实也没什么。除了那栋楼房、怪藤、泥淖,加上一轮月亮,还有啥?周围黑漆漆的,云里雾里。
他对没面目说:“你能造多大的东西?”
没面目说:“我能造一个屋子,里面放一张床,够了么?”
杨肜说:“什么?别开玩笑。”
没面目说:“在此基础之上,屋外弄些花花草草,弄一池水,放两只鸳鸯,如何?”
杨肜说:“能不能造出一片花海?”
没面目说:“干脆一片海,一片沙滩如何?再加几棵椰子树,一个小木屋。”
杨肜说:“呃,那就一片海吧。面朝大海,穿暖花开。诶,这些东西,我自己做梦也能梦见呀。”
没面目说:“没错,不过你梦见的东西是随机的,不受控。你怎么知道你会和心爱的女人,在这种梦境里相遇?说白了,你还是要将她拉入到你所创造的梦境中。”
杨肜说:“那你能不能教我造出一片梦境?”
没面目说:“眼下不能。”
杨肜说:“还是因为我意识的力量不够?”
没面目说:“不错。”
杨肜说:“我怎样才能获得这种力量?”
没面目说:“你需要突破原先的意识,我想想,我当初突破意识是因缘际会,总之不容易。”
杨肜心想:“你这说了等于没说呀。”说道:“好吧,那只能有劳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