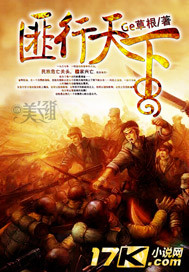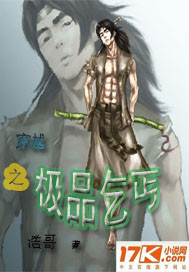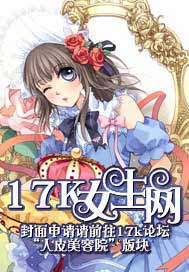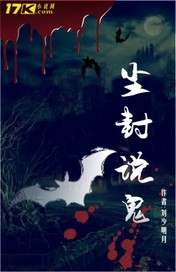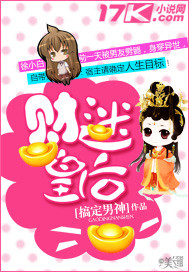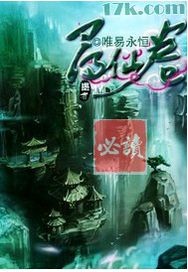现在的安徽省原名叫安庆或徽州,两者皆去一字并称为安徽。
在安庆有处佛教圣地。此处风景如画、重峰叠嶂,青松仓木、傲然凌立。在群峰当中,有座山峰因形似莲花,又有九座而被称为九华山。九华山因地处险峻、峰峦亦状群峰跌宕起伏、巍耸天地著有‘东南第一山’的美誉。
九华山最高的一座山峰名为‘天柱峰’,此峰因地势险拔、周围青松密布围绕傲然凌驾诸峰之巅。在天柱峰上有座寺庙。寺庙门前是处空旷的草地,寺庙规模虽小但高大雄伟,气势磅礴。寺庙门上的牌匾赫然写着‘九华寺’三个大字。
这块牌匾是当年杨广率军南征时,路过山下一时兴起参观完寺庙后,随手所留。本来只是小小的一个题词,却被寺庙方丈后来模仿杨广笔迹改为牌匾高挂门前,为的是显露此山的不凡。
寺庙有些清净素洁,刚刚做完早课的和尚们在清扫院中落下的枯叶。枯黄的树叶倾诉着秋天的到来,抬头望去,四周花草都已凋零,唯有院外的青松还是傲然常青,不畏时间的侵蚀。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唉,”一名扫地的小和尚看到枯黄的花草,又看看了院外的青松,幽然说道“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元直,你又在瞎念叨什么?还不赶紧扫地,要是在午时之前扫不完院中,咱两的午饭就又没了。”旁边正在认真清扫的另一名小和尚看到后,语气有些责怪的说道。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小僧只是触景生情,一时有感而发,元通师兄何必在意。”叫元直的小和尚双手合掌念了声佛经,不以为意的反驳道。
这两名小和尚叫做元通、元直,是整个九华寺年纪最小的沙尼。元通比元直早入寺庙半年左右,所以是师兄。
“嘘!小声点。你不知道两天慧通师叔心情不好吗?要是被他看到我们在这里没有专心干活,又不让我们吃饭了。我倒是没事,只罚一顿。可是你啊,午饭和晚饭又要都没了。难道你忘记昨天的事了吗?”见元直还有些不在意,元通拿起扫把走到元智旁边,低声耳语道。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佛祖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慧通师叔要罚就罚我吧,何必连累师兄你呢。唉,都是师弟害师兄昨天一起受罚,罪过罪过!”元直小和尚一副悲天悯人的表情。昨天因为自己没有按时做完功课,害的师兄也没饭吃。自己受罚,为何元通也要受罚呢?因为元通是他的师兄,负责监督他的功课。由于昨天一事,两人今天负责清扫院中的落叶,偌大的寺院除了清扫院中,还有院外和大殿、后院这一切都必须要日落之前完成。否则明天两人还要受罚。
“唉,你知道就好。别说了,还是老老实实干活吧。等把院中清扫完毕吃饱了午饭,下午才有力气干其他的。”元通见元直有所明悟,便不再多言,开始专心的干活了。
佛教传到东土,大约也有八九百年。从西汉后期时,也渐渐存在。东汉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而后三国混战、两晋时期逐渐陨落。直到南北朝梁武帝推崇佛教,至此大肆公开宣称佛教圣经又有达摩来中土传授佛法理论,佛教一时风光无限将汉人道教狠狠压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杨坚的隋朝。杨坚本人也非常推崇佛家经典。而九华寺就是当年佛家两处圣地之一。经历了南北朝时期的盛期盛衰后,战争的淬炼,九华寺已经不复当年的光环万丈。虽然杨坚再度推崇佛门,但今时已不如往日。国家百废待兴,百姓刚够保暖,九华寺庙前来供奉的香火人数一直有减无增,直到如今已没有人来施舍供奉了。
九华寺庙共有和尚差不多百人左右。其中大多数都是孤儿,被人遗弃在院外被方丈发现后收养了起来,还有一些人则是从外面捡回来的。真正出家修行甘愿剃度脱发皈依佛门的也就十来人左右。寺院从方丈初时的二十来人到现在的百来人,平时的日常花销都靠自食其力,另外山下百姓的捐赠。
每当寺院柴米不多时,方丈会让分两批弟子。一批弟子上山砍柴,采摘一些野菜用来食用。出家人不吃荤,基本上上山砍柴的和尚凌晨出去,傍晚归来都会带有打量的柴火和山中的野菜,有时还有几大包的野果。另外一批则是下山化缘,讨要一些柴米。有时百姓收成不好,寺庙窘迫,下山的弟子则会到城中卖艺表演讨得一些商银用来购买柴米油盐。通常他们表演的都是少林基本功夫,罗汉拳、少林棍法、铁布衫等等。往往这些表演都会为他们带来阵阵围观百姓的喝彩讨取到赏钱。
一些富家子弟特别喜欢他们的表演,每当这些和尚下山表演时,他们通常都会给取很多钱财,除了看热闹之外就是想要拜师学习少林功夫。这些和尚初时以为他们都是爱好习武,有佛性、有慧根的良家子弟能吃的苦。见他们诚意恳求,态度良好,索性就带上了九华寺。
原本这些人都是慕名而来,为的就是学习武动。没想到方丈却让他们每天背经颂文,劈柴挑水这些简单枯燥的活。刚开始他们以为是寺庙的考验,很多人坚持了几天,后来他们问寺中的和尚这样的生活要多久。和尚告诉他们,一直如此。那些平日里养尊处优,心性浮华的公子哥听完后都纷纷下了九华山。要让他们吃一天苦都难如登天,更何况还是遥遥无期。刚开始能忍受就是为了学武,学成之时,好便下山之后卖弄。现在一听这样的苦日子没有出路,一个个都熬不住了跑下山去。
这里面有一个人例外,就是小和尚元直。不论日子多苦多么枯燥,他都始终没有怨言,心甘情愿的呆在这里。这一呆就是三年。这三年除了每天所要做的功课外就是劈柴挑水。整个寺院他劈柴是最好的,挑水也是最棒的。他劈柴好,是因为无论多大的木头他都能劈的整齐如一,每一块木柴大小同等,都是两刀。挑水要到山下去挑,每次挑水方丈都会排他和几位师兄一起去。别的师兄挑水回来,木桶多少都会撒漏一些,有些甚至桶中之水不及桶的一半高。唯有他,每次挑回来的水都是整桶满满的,一滴不撒、水面平静。
方丈得知此事后,从此再也没有让他去挑水劈柴了。安排他每天清扫藏书阁,每天背诵《金刚经》偶尔也让他下山化缘。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却很充实。元直非常喜欢享受现在的安稳宁静生活。与世无争、悠然自在。方丈从没问过他的出处,元直也一直没有说。寺庙中没有人知到他的原名,只知道他是名真正心向佛祖,六根清净的小沙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