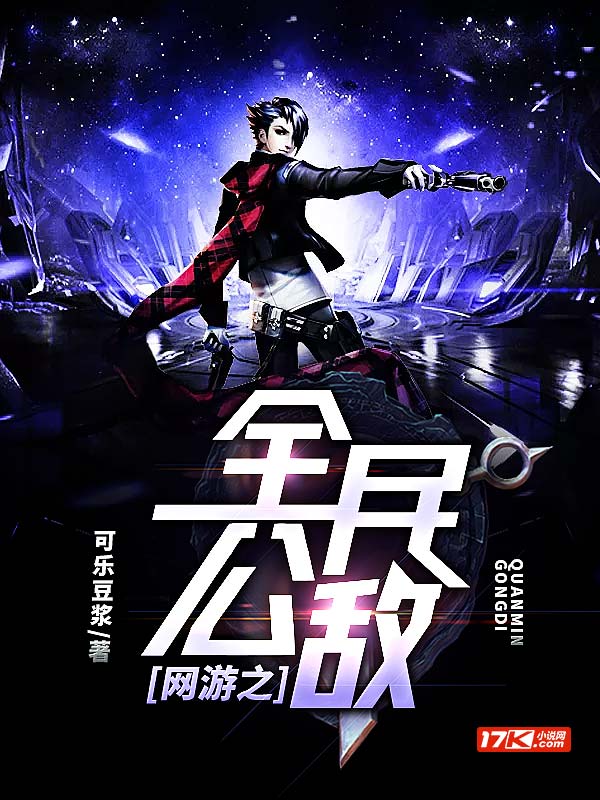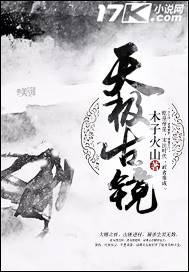词曰:
步花径,小路狭。防人惦记,常受惊吓。
嫩枝咿哑,讨归路,寻空隙,旧家巢燕入窗纱。
话说西门庆在房中,被李瓶儿柔情软语,一顿溜须拍马,感触的由嗔变喜,拉她起来,穿上衣裳,两人相拥而泣,极尽绸缪。
随即西门庆令春梅进屋放桌子,到后边取酒去。
且说金莲和玉楼,从西门庆进李瓶儿房中去,就站在院子门口偷听消息。
可李瓶儿这边又关着门,只有春梅一人在院子里伺候。金莲同玉楼两个打门缝儿往里张望,只见房中掌着灯烛,可里边说话,都听不见。
金莲道:“俺到不如春梅这小冤家,她倒听的清楚。”
那春梅在窗下偷听了一会儿,就走了过来。
金莲悄悄问他房中有什么动静,春梅便隔门告诉二人说:“大官人怎的叫她脱衣裳跪着,她不脱。大官人发火了,抽了她几马鞭子。”
金莲道:“那打了她,她屈服了没?”
春梅道:“她见大官人真生气,才慌了,就脱了衣裳,跪在地上。大官人现在正问她话哩。”
玉楼恐怕西门庆听见,便道:“五姐,咱到那边去罢。”
拉金莲来西角门口。此时是八月二十多,月色才上来。两人站在黑暗里头,一起说说话,等着春梅出来再问她话。
潘金莲跟玉楼说道:“我的姐姐,贼汉子进府前只说疼你爱你,良田美舍,穿金戴银,好食果子,骗得你一心只要来这里。
好日子没过几天,热乎劲都还没过呢,下马威早讨了这几下在身上。
俺这个好酸脸子的货儿,你若顺着他的心意倒罢了。
稍微逆了一点他的心,就马上被摁在地上摩擦,不服气就一直打。
想着先前我被小贱人奴才冤枉造谣,我陪下十二分小心,还被他打得我那等哭哩。
姐姐,你入府也这么久了,还不知他什么脾气!”
二人正说话之间,只听角门开门的声响,春梅出来,径直往后边走。
不提防她五娘站在黑影处叫她,问道:“小冤家,哪里去?”
春梅也不答她,笑着只顾走路。
金莲道:“怪小冤家,你过来,我问你话呢。急慌慌的跑什么?”
那春梅方才停住了脚步,说:“李瓶儿哭着对大官人说了许多话。大官人欢喜的抱起她来,让她穿上衣裳,叫我放了桌子,如今到后边厨房取酒去。”
金莲听了,向玉楼说道:“贼没廉耻的货!还以为是个威风汉子!谁料到雷声大雨点小,说什么这样那样那样这样要收拾这贱人。等真到关键时刻,也不怎么地。
我怎么猜,也没想到是这情况,你尽管取了酒来,叫他们喝。
贼小冤家,她房里自己没丫头么?到叫你替她取酒去!
到后边,又要被孙雪娥那小奴才聒噪,反正又不用我去听,你乐意你就去吧。”
春梅道:“大官人支使我的,和我有什么关系!”于是笑嘻嘻的走了。
金莲道:“俺这小冤家,正经支使着她干活,死了一般懒的动弹。
若去干叼猫逗狗的差事,钻头觅缝拼死了也要去,去的那个叫快!
现在别人房里就有两个丫头,你还替她跑腿,关你个毛事啊!
这个咸吃萝卜淡操心的小冤家!”
玉楼道:“可不怎的!俺房里大丫头兰香,我正经支使他做活儿,她便有的没的拖拖拉拉的。大官人支使她做偷鸡摸狗的事儿,那叫一个听话儿,你看她走的那叫一个快!”
正说着,只见玉箫自后边蓦地走来,说道:“三娘还在这里?我来接你来了。”
玉楼道:“小妮子,吓我一跳!”
又问:“大娘子知道你出来了不?”
玉箫道:“我伺候娘睡下有一会儿了,无聊我就来前边瞧瞧,刚才看见春梅到后边要酒果去了。”
又问:“大官人到李瓶儿屋里,有什么动静儿没?”
金莲接过话来伸着手,指着李瓶儿的房间道:“你进她屋里去,能听个明明白白。”
玉箫又问玉楼,玉楼便一一对她说了。
玉箫道:“三娘,大官人真的叫她脱了衣裳跪着,打了她五马鞭子来?”
玉楼道:“大官人因她不跪,才打的她。”
玉箫道:“带着衣服打的,还是脱了衣裳打的?亏了她那莹白白的皮肤,怎么挨得一顿马鞭?”
玉楼笑道:“你个贱皮子小冤家,今人倒替古人担忧!”
正说着,只见春梅拿着酒,小玉拿着食盒,往李瓶儿那边去了。
金莲道:“贼小冤家,不知怎的,平白无故给人家跑腿儿,云端里老鼠──天生的耗,抖你的小机灵吧。”
吩咐:“快送了就回来,叫她家自己丫头伺候去。你不要管她,我还要用你哩!”
那春梅笑嘻嘻同小玉进去了。当下把酒菜摆在桌上,就出来了,只剩绣春、迎春在房里服侍。
玉楼、金莲问了她话。
玉箫道:“三娘,咱到后边去罢。”二人一起走了。
金莲叫春梅关上角门,回了房间,独自宿歇,不在话下。正是:
可惜团圆今夜月,清光咫尺照他人。
不说金莲一个人睡,单表西门庆与李瓶儿两个相怜相爱,饮酒聊天到半夜,
方才被伸翡翠,枕设鸳鸯,上床就寝。
灯光掩映,香气薰笼,好似花间蝴蝶对舞。
正是:今宵胜把银缸照,只恐相逢是梦中。
有词为证:
淡画眉儿斜插梳,巧手轻拈提玉壶。
云窗雾阁深几许,娇颜兰心款款呼。
相怜爱,美人扶,神仙快乐世间无。
从今罢却相思愁,美满恩爱今夕固。
两人睡到次日太阳照屁股。
李瓶儿正要起来照镜子梳头,只见迎春从后边厨房端了饭过来。
她先漱了口,陪西门庆吃了几口饭,又叫迎春:“将昨日剩的金华酒端来。”
拿酒壶陪着西门庆每人吃了两杯,方才洗脸梳妆。
然后开箱子,打点细软首饰衣服,请西门庆过目。
拿出一百颗西洋珠子给西门庆看,原来是昔日梁中书家中带来之物。
又拿出一件金镶鸦青帽顶子,说是过世老公公的。
起下来上了秤,四钱八分重。
李瓶儿叫西门庆拿与银匠,替她做一对坠子。
又拿出一顶金丝鬏髻,重九两。
她问西门庆:“上房大娘等众人,有这种鬏髻没有?”
西门庆道:“她们银丝鬏髻倒有两三顶,只是没这样的鬏髻。”
妇人道:“那这样的话,我不好戴出来的。你替我拿到银匠家熔了,打一件金九凤的头饰,每个凤嘴衔一溜珠子,剩下的再替我打一件什么呢?大娘正面戴的是金镶玉送子观音满池娇分心,我就打件一样的好了。”
西门庆收了,然后梳头洗脸,穿了衣服出门。
李瓶儿又说道:“我那边老房子里没人,你好歹安排个人儿看守,替了小厮天福儿来家里使唤。那老冯到底年纪大了,说话断断续续,糊里糊涂的。独自在那里,我不放心。”
西门庆道:“我知道了。”收着鬏髻和帽顶子,一路走了出去。
不防金莲头发蓬松的站在东角门口,叫道:“哥,你到哪儿去?这会儿才出来?”
西门庆道:“我有事儿要去办。”
妇人道:“坏东西,着急走什么?我和你聊聊。”
那西门庆见她叫的紧,只得回来。
被金莲拽到房中,金莲坐在椅子上,拉着他的两只手说道:“我不好骂出来的,走路慌慌张张也没个深沉,哪个还能拿大锅烀了你吃!慌里慌张的为些甚的?你过来,我且问你。”
西门庆道:“别这样了吧,小贱人儿,你只顾问什么!我有正事哩,等我回来再跟说。”
说着,就要往外走。
金莲摸到他袖子里重重的,问道:“是什么?拿出来我瞧瞧。”
西门庆道:“是我的钱包。”
妇人不信,伸手就在他身上就乱掏,掏出一顶金丝鬏髻来,说道:“这是她的鬏髻,你拿了去哪里?”
西门庆道:“她问了我,知道你们姐儿几个都没有,说她也不好戴出来,就叫我到银匠家替他熔了,打两件头面首饰戴。”
金莲问道:“这鬏髻多重?她要打甚么?”
西门庆道:“这鬏髻重九两,她要打一件金九凤儿,另一件仿着上房月娘的正面那一件玉观音满池娇分心。”
金莲道:“一件金九凤儿,满打满算三两五六钱金子够了。大姐姐那件分心头面,我秤过只重一两六钱,把剩下的金子,好歹你替我照她的款式规格也打一件金九凤儿。”
西门庆道:“满池娇她要纯金实芯的。”
金莲道:“就是实芯的,使了三两金子最多了。还落她二三两金子,留给我够打个首饰了。”
西门庆笑骂道:“你这小贱人儿!单爱占小便宜儿,有机会就捏个尖儿。”
金莲道:“我得乖乖的儿,娘说的话,你好歹记着。你不替我打头面送来,看将来还和你说话!”
那西门庆拿了鬏髻,笑着要出门。
金莲开玩笑道:“哥儿,你威风上了。”
西门庆道:“我怎的威风上了?”
金莲道:“你既没威风上,为何昨日那等雷声大雨点小,原本说要打她还要看着她上吊。结果人家房里拿出一顶纯金鬏髻来,就支使的你狗油嘴、鬼推磨的,不怕你不听调遣。”
西门庆笑道:“这小贱人儿,只知道胡说!”说着往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