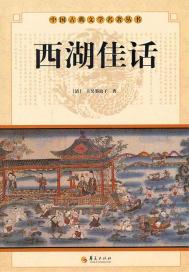酷暑,
残阳下,
扬子江畔,
狭小的廉租房内,一张硕大的桌子上堆满了形形**的书本,微黄的半杯水,从底部开口的牙膏。桌旁有床,挂有蚊帐,帐顶上落有数不清的蚊虫的尸体。屋内角角落落蛛网密布,四壁灰白斑驳不堪,地上一层薄薄的尘土证明此地已经闲置很久了。门后还贴有枯黄的纸张,字迹依稀可辨,“一门一户一人租,一人进来一人出。一餐一饭一人咽,一人笑来一人哭。”
太阳已经西斜,温度却不见降。滚滚的热浪携着地面潮潮的土气席卷而来,把整个房间蒸腾起来了。地上众多的蟑螂正以不规则的S型互相串着亲戚,空中无数的黑白花纹细脚蚊已经组建成一个个集团军,向蚊帐发起了一次次冲锋;窗棂上一只装饰用的青蛇正向屋内“咝咝”吐着鲜红的信子,屋顶上一条褐黄的壁虎迅速窜行了一段,猛然顿住,像想起了什么,转个弯爬走了。
西山终于衔住了日头,天空烧得血红一般。一只探头探脑的小花猫窜上了窗台,看看下面,弓起身子“喵喵”叫了两声。
“咯吱”,床突然一动,一只巨大的折扇伸了出来,啪的展开,烁然是苍穹有力的四个大字——“无欲则刚”。纸扇摇动,片刻后再无声息。
花猫伸出右爪,用舌头仔细舔了一遍,换到左爪,从耳后蹭脑袋,连着蹭了三四遍,猫耳朵突突地抖了几下,支楞起来了。花猫扭着屁股,高举着尾巴,沿窗沿走了几遭,探出头看看地面,一俯身跳下来,地面上便沾满了串串小梅花印。小猫来到床脚,喵喵几声低叫,把两个爪子对这木制的床脚,噌噌地磨起来。
许久,床又是一动,一声长啸传出,“大梦谁先醒,平生我自知。陋室吾安睡,窗外日迟迟。”
“花花,你又饿了不成?”话音未落,一人持扇而出。观此子,目若朗星,脸似银盆,两道剑眉斜插入鬓,高鼻梁,方阔口,束腰乍臂,扇子面的身材。上身穿月白段的背心,下身穿一件蹲档绲裤,脚蹬抓地虎的刺花拖鞋,腰系鳄鱼板带,真是上上下下千般锐气,身前身后百步威风。这就是高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个空有报国志、苦无黄金台的小人物。
高辉从柜顶拿出一碟香肠,抽出一片,掂量一下,又拿指甲抠出一个小角,把盘子放回柜顶,转身来到小猫身边,“花花,我知道你想吃,你想吃就说嘛,你想吃又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吃。你如果说你想吃,我怎么会不让你吃?即使我不让你吃,你也不该跳进我的屋子里来。即使你跳进我的屋子里来,你也不该抓我的床啊,即使你抓我的床,你也不该咬着我的手啊……啊……死猫……撒嘴……那是老子的手指头,不是你的香肠……”
夕阳已经下山了,天色正逐渐暗下来,傍晚像一个长有巨大羽翼的吸血鬼,他的身影正一点点吞食光亮。高辉站在窗前,仰首望着北方薄薄的一片灰色光亮和西方一丝丝苟延残喘的红光,长叹一声。
北方,那里有他的家,有他的亲人,有疼她爱他宁愿为他付出一切的亲人,有世间一切都比不上的温柔。十年前,高辉求学异乡。曾立下重誓: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到今日,居无定所,学无所成,生活艰苦,无以为继,上不足以侍奉父母,下不足以蓄养妻儿,谈何学而优则仕,有何面目见家乡父老?唉……
“咣当”一声撞击声把高辉拉回了现实,他低头一看,小花猫后退几步,怯怯地看着窗户上的玻璃,而外面另有一只猫冲这边喵喵低叫。高辉拍拍小猫的脑袋,“古人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花花啊,你咋老空呢?”花猫从半开的窗户重新窜了出去,两只猫拱在一起,亲昵地蹭着,跑向远方。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高辉淡淡的身影在窗前拖得好长好长。屋里,床铺已经整理好,热水瓶已经打满,衣服都已经洗干净叠好,文具都已经归类到一起。高辉喃喃自语道,“是时候离开了,离开这个心向天堂、身为刍狗的世界。”
好了,好了,一死百了,剩得个黑漆漆世界,好干净。
…………
2008年6月,“海燕”台风边缘波及上海,一栋廉价居民租房被吹倒,经查,无人员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