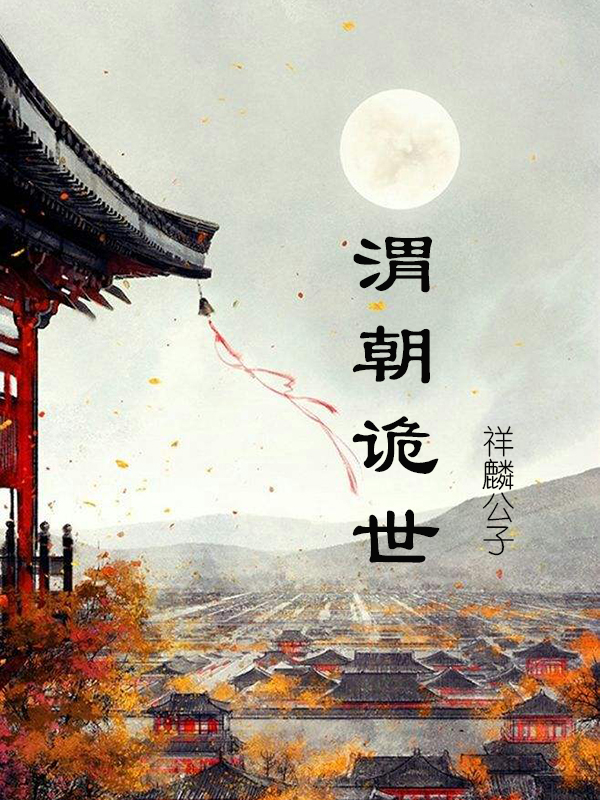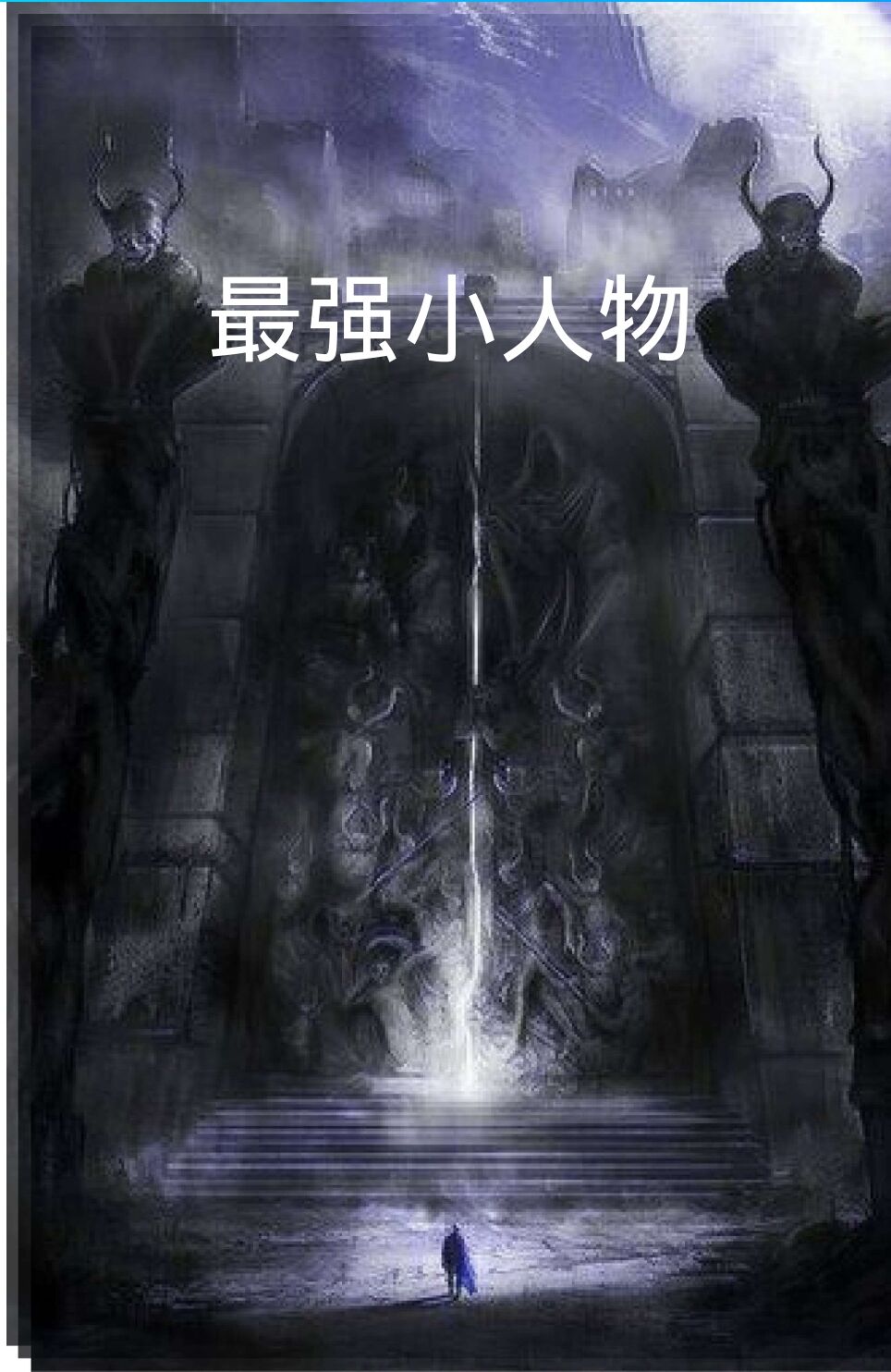当晚,公主没有再做噩梦,却也病了。太医院急急派得力之人来诊治,虽说得出并无大碍的结论,还是小心翼翼地开方熬药,不敢有半分怠慢。如意顾不得别的,只是彻夜不眠地守在公主身边,见其花容月貌憔悴了许多,全不见往日神采,自然心疼不已,也照例什么都问不得、说不得。她知道定是公主的课业出了问题,因为此前每次自丰渠阁回来皆有封赏,奇珍异宝数不胜数,而这一回,她看到了公主从未展现过的一面——失魂落魄。
天色未明,贵妃也赶来了,见女儿睡得很安稳,心情略微平复,便自如意那里问明了大致的情形。正准备回宫再做筹划,竟在长廊上遇见了匆匆赶来的太子,心头不免有了一些暖意。二人便去公主的书房里坐了坐,随行之人自然都守在外头。
“听说是功课做得不好,陛下倒也没说什么,她自己偏就怄起来了,幸好此时已无大碍,还让殿下跟着担心一场。”太子忙说,“皇姐病了,儿臣自然担心,派人来看又怕说不明白情形,只得亲自赶来瞧一眼才会放心,其实也没顾得上礼数。”贵妃自然明白太子话里的意思,便顺势说,“殿下与玥儿血脉相连,自小陪伴着长大,感情深厚,臣妾都明白。”太子释然叹气,就此告辞。贵妃出了书房,又去嘱咐了如意一番,便也回宫了。
“昨晚到此时,质子可有异动?”晨间,焉汶坐在自己的宅院里喝茶,伺候茶水的焉知停下了手上功夫,低声回复,“不眠不休地抄写金刚经。”焉汶冷笑道,“真是难得……莫不是为谁祈福吧?”见焉知不语,便又继续敲打道,“有些人啊真是愚钝,明明自己就是症结所在,只会连累别人,却不自知。”焉知嘴角抽搐了一下,眨了眨黑亮的眼睛,终究没有说出反驳的话来。
太子刚刚回到寝殿,又碰上了在此等候他的皇后,自知逃不过一场审问,索性就先发制人,全部交代出来。赵皇后倒也没有如常地训诫儿子,“公主病了,去看看也对,陛下知道了也会觉得你有情有义,不会怪罪什么礼数不周的。”然后话锋一转,说出正题,“明年春天质子也要成亲了,所以太子妃的事情哀家也想听听你的意思。”
太子心里正惦念着皇姐的病因,担心与质子相关,是受了其连累,这会儿又听了母后念叨质子,顿觉无比烦闷,“母后,质子成婚与我何干?”赵皇后略一蹙眉,慢条斯理地说,“你若置身事外,就要全凭哀家做主了。到时候,无论是谁,都务必要和美地成婚,早日开花结果。你不是临安公主,可以肆意胡闹,花样百出,不成体统。”最后一句实在刺耳,太子心头一疼,索性施了礼,便头也不回地逃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