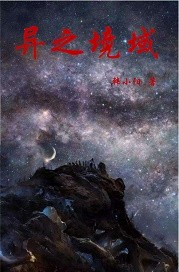———太子府
苏寒玄着一身霜白底广袖流云纹常服,正处理着近几日积留下来的折子。
苏栩称病不朝,泗城那边孙括又动作频频,他们连着追查了几日货物的来源,却发现不止胤都,连着近四座边境城池都与泗城有货物往来,而那些城池,都坐落于秦厦与华序的交界处……
另外两国中,楚国虽强盛,可国家内部却忙于清剿地方遗留的豪强势力,根本无暇过多关注外界。
所以,秦厦是目前对华序威胁最大的国家,秦厦尚武,且历代君王励精图治,以至秦厦国家富庶、军事实力十分雄厚。
赶在这三国盛会到来之际,再微小的动作都会对局势产生影响,更何况,那批货物的内容他大约也能猜到一二。
再加上今晨,唐临痕向他汇报的皇城中的近况,诸事纷杂,偏偏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着实令人头痛。
窗前,雕花香炉中的香料燃得愈发浓郁,案几周围云雾缭绕。
许是太过疲倦伤神,也只有在这满室轻烟内,他才得以稍稍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
感受到一阵奇风掠过,他双目微阖,启声问道:“事情查的怎么样了?”
深书立即在他面前站定,恭敬回道:“宫中的暗线说,谢贵妃一开始只是将小姐关在了一个冷僻的宫殿里,派人看守着,后来却不知为何,小姐突然消失,明面上所有证据都指向谢贵妃,此事她辩无可辩。”
“而据我们另一边查到的消息称,在小姐被谢贵妃带走时,有人冒充了我们的人,与小姐派出去报信的侍女接应。卑职推测,这分别出自于两方不同的势力。”
“嗯,看来是一场精心布下的局,完美的嫁祸。谢湘华即便要杀人,也不会蠢到在宫中动手,她应当没想要伤害昭儿。”苏寒玄颔首。
“那,小姐会不会是在被关押时,被其他人带走了?”浅卷在一边将烛芯拨高了些,拧着眉道。
“可是守卫就在外面,小姐若是被人强行带走,又怎会一点声音都没有?”深书摇头反驳。
“除非,是昭儿自愿被带走的。”苏寒玄睁开双眼,眸中寒光毕现。
“殿下您的意思是……”浅卷面色也凝重了下来。
“令牌不必再找了,本宫知道它在何处了。”
苏寒玄起身,声线沉冷:“备马。”
———华序皇宫,教坊司
那宛若山中高士的矜雅公子,正抬步跨入教坊司的雅座,他身着一件云青色的氅衣,眉目间挑尽了山林雅意,看到一早便候在雅座内的女孩儿,他眼中多了些笑意。
“便是这般盼我不及,早早就在这等着?”
裴兴奴如一只活泼的雀儿一般小跑到他身侧,轻轻抱着他的手臂,笑吟吟地仰头望他:“起时哥哥都好久没陪我吃饭了,今日可不许再提前离开了!”
云起时环住她的纤腰,轻吻了下她的鼻尖,低声道:“好,今日依你。”
裴兴奴拉着云起时在桌边坐下,贴心地为他布菜。
云起时含笑将她布的菜吃下,状似不经意的问道:“不知我让阿奴办的事,如何了?”
听到他唤她“阿奴”,裴兴奴不高兴地瞋视了他一眼,将太子府的令牌递还给他,然后应到:“已按照起时哥哥的吩咐,都办好了呢。”
“嗯。”云起时接过那块白色的盘龙玉佩,小心的收了起来,得到了想要的答案后,便不再说话。
雅座外丝竹之声悠扬,教坊司内美人如织,这热闹的舞乐之欢并未因苏栩病重的传言消减半分,便足以见王权式微。
如今华序真正的权力,是掌握在太子殿下与护国将军孙括手中的。
在华序这盘棋局中,殿下与孙括各执一方,以各方势力为棋子,五大世家在其中扮演尤为重要的角色。
而楚家那位小姐,身世离奇复杂,背后还不知究竟牵扯到多少势力,这般亦正亦邪的角色,绝不适合拿来当棋子……无论殿下有多看重她,她的存在,都只会让这盘棋多一分变数。
所以,倒不如趁她羽翼未满时,除掉她。
“起时哥哥?起时哥哥?”裴兴奴见他一直不说话,不禁扯了扯他的衣袖。
云起时收回思绪,温柔的抚了抚她的额头:“阿奴乖,我下次再来看你。”
说完,便起身准备离开。
裴兴奴见状立即红了眼圈,又不敢在他面前太过放肆。
云起时虽瞧着温柔,却是个心狠手辣的主儿,他即便待她比待其他歌姬好些,可她也真的不敢恃宠生娇。
于是,她只虚留了一句:“真的不能再待会儿了吗?”
云起时弯了弯眉眼,语调温柔:“真的不能了哦,一会儿有一人就要来找我了。”
说着,他却取出一只机关精巧的玉方块递给裴兴奴。
“过会儿若有人来找我,就请阿奴把这只匣琅交给他。”
“是,兴奴知道了。”裴兴奴带着些委屈低声应道。
见她听话,云起时十分满意的揉了揉她的头发,转身离开了。
云起时走后不到半刻钟,白衣谪仙般的清绝公子便策马而来,他跨下马走进教坊司,在一楼大厅的太师椅上落座。
他面色清寒,不发一语的坐在太师椅上,周身携着凛冽迫人的威压,使满座之人皆不敢直视。
丝竹管弦声立即停了下来,众人正要起身,却见他抬手挥了挥,冷声道:“礼数免了,让云起时出来见本宫。”
教坊司的主事嬷嬷赶忙上前,小心翼翼道:“殿下,云公子方才已经离开了……”
苏寒玄冷冷的扫了那嬷嬷一眼,那嬷嬷吓得立即跪倒在地:“殿下恕罪!”
气氛正冷凝时,裴兴奴拨开人群走到苏寒玄面前,恭敬的将玉方块呈出:“殿下,云公子离开时吩咐奴家将这只匣琅交给您。”
“哦?这么说,他早知本宫会来找他,却提前跑了?”苏寒玄嗤笑着拿起那只巴掌大的玉方块,玩味地盯向裴兴奴。
裴兴奴腿软了软,还是硬着头皮道:“回殿下,云公子只说过会儿会有人来找他,奴家也不知他说的人是殿下您……”
说到最后,她的声音已经低的不能再低。
苏寒玄哂笑一声,也懒得迁怒其他人,他掸了掸雪白的宽袖,便起身带着侍卫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