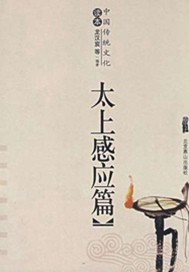我们刚搬过来时是无地方安置的,学校方面也都还沒决策好,因此我们的行李都成堆成堆凌乱的堆放在老师那里。搞得老师也十分为难,学生生活起来也很不方便。
但校领导说:“开学在即,人先来上课了再打算。”
这边的老师我一个都不认识,学校被取谛也并没有一刀切,家门口那边依然还有一至四年级,我的行李放在低一个年级同学小孙的亲戚那里。
小孙的叔叔阿姨都是老师,且全在这里面教书,我与她的交情至此也最多是因为她年年名列前茅,我偶尔名列前茅,大家在领奖台上点头相见,合影,微笑,便得以认识。
刚来的时候许多主任不接纳我们,他们说:“念书可以,但突然多出几十个人来住学校,确实是个大难题,不是加减乖除法,也不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方案就能解决,而是一群人吃喝拉撒。”
且不说我们住的地方有没有,单是我们习不习惯这种尝试还有待言说。
学校发了一批老师去走学校到我们村的路,看一下一个来回要多长时间,结果走了才定,没一个半脚程是走不到学校。
冬季天黑得早,万一下雨,来上学就更加辛苦。加上那边山高坡陡,路十分不好,等待决定那几日,许多人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我们更是吃不好住无固定,人生地陌,一点都不舒服。
还好学校方面动作快,我们的安置马上有了下文。
就在我们搬行李去上学后不久,我们就获得了一处地方,是老教学楼,我跟着同学们走进去,里面的那种黑,似乎是几百年的老房子才会有。
因为突然并了许多小村庄的学校,教室一排再排也不够多出的许多班级用,老楼也就无法退休,光荣坚守。
老楼的下面是教室,上到楼上,依旧可以看到分厢房和大间两个屋,如果这类房屋作家用,厢房的外面肯定立了牌位贴上对联当香火用。
但它们现在却变成我们的女生宿舍,依旧是活动床板铺出的小位置,没有铁架。
厢房住三人,大房住九个。床铺一路铺过去,相互挨着,铺完一看,花花绿绿的,刹是好看,你睡这颜色,我睡那颜色。就算一不小心滚到一块了也不介意,好歹有个睡的地方,比什么都强。
要睡觉了,同学们便脱了鞋爬到自己的床铺上,然后把被子折成桶,整个人钻进去,因为不那样睡,多的地方是没有的。
最难为那个胖胖的主任,他在屋里给同学们规划,地方窄得他转不过身。这也算独在异乡为异客,大家都分外关心。
经常推了门进去,大家都脚挨着脚坐在一起聊天,我们又因为个子不高,床头还可以放一口大箱子。把所有的东西放里面,上一把锁,吃饭把菜放箱盖上,大家分着吃,生活也有滋有味。
以前在家,父母煮什么就吃什么,或者想吃什么就自己去煮两下子,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现在不行了,饭都放进铁盒里统一蒸,为了买一个饭盒,母亲还特意走四十公里一个来回去赶集市。
菜是从家里带的酸,用油炒一下再放些盐,装成小小的一瓶,这样就吃一星期。或者还可以去食堂打,一毛钱一份的酸汤菜。
就算半年不吃肉,人也是开心的。
外面还有米粉店,没有钱还可以拿大米去换。我当然听父母的,并没有拿米去换,连老师后来都开会说禁止那种只赔不值的消费方法。
六两米换价值五角钱的粉,半斤米也不止值这一点。
我们并不清楚一斤米当下值多少钱,但我们也觉得十分的不划算,有时候身无分文了也会去换。因为大米放在家里,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只要你背的动。
吃没了也是父母操心还轮不到我们。可见那时的我们多处心积虑的和父母对着干。
父母说这样不行,越不行我们就偏要那样,没心也没肺。
后来听了老师的告械之后,我每次去吃粉,提着空盆子去,走在路上都觉得十分荣耀。那种感觉就像在学雷锋。
你坐车让座了,或者在地上捡个垃圾丢桶里了,好像全世界都在看你一样,此刻,你又正是底气十足的时候。
人向善时都不惧有人看,只有向恶了才威威欺欺,膽前顾后。然而我又是多么的相信老师们肯定会看着,专门盯着那些不听话拿米去换粉的学生。
一件事如果被禁止了,你再明知故犯,那就是很不光彩了。
我如果真的没钱,就不去吃了,等有了钱再去,少一顿又不会少块肉,但少一种硬气,那就是不诚实了。
况且,酸伴饭的吃法也节省时间。
有的男生自制力差,就会去换,当然,上有政策下就有对策,他们巧妙的把米放在液窝的衣服那,假装成用钱买的样子。
但在路过校长楼门前,因为心里有鬼,仍须底头默默的走,切不可东张西望,更不可与老师们交谈,以免露陷。
其实我们根本不用在吃饭这一块节省时间的。以前,经常放学回去,家里都还是冷锅冷灶,父母都还在外面干活全没回来。
因此我们放学又有得忙,家务活永远做不完似的,刚吃好饭,又要去上学。
现在,放了学,时间就全是悠闲自在的。写完作业,等着吃饭就行了。
日子过得简直好上天。
那些开始不赞成我们住校的老师看我们那么乖,也掏心掏肺的相处起来,不再忧心肿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