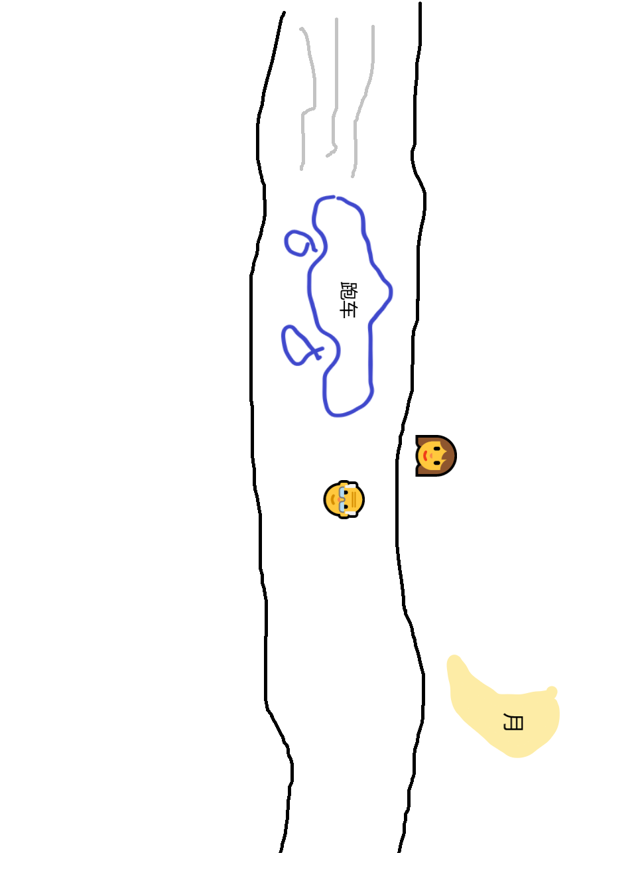春天悄无声息地走进了,伦敦却依然寒冷。街上的行人仍旧很少,整个城市依然沉浸在一片寂静的萧瑟之中。一个报童穿着破旧的棉衣,在街上一边跑着一边叫卖手中的报纸。如果上帝愿意,他真希望能再爆发一次世界大战。那几年的报纸就比现在好卖多了。时运不济啊,那些有钱的人宁愿花大把的钱去吃喝玩乐,也不屑于把零钱施舍给那些连温饱都得不到的孩子!报童跑着跑着,突然在拐弯的地方和一个人迎头撞上。他几乎没看到那个人是怎么出现在自己面前的,等反应过来的时候,自己已经四脚朝天,手里的报纸也掉在了地上。
“对不起!对不起……”报童一边从地上爬起来,一边说着抱歉。世态就是这样,穷人的孩子摔倒了,还得自己爬起来跟人家说道歉,不然有钱的人会怪你弄脏了他们的衣服。可就在他转过身子准备去捡掉在地上的报纸时,却发现它们已经被人捡起来递到了自己跟前。
“谢谢您!先生……”报童双手接过报纸一边说着谢谢,抬头想看看面前的这个好心人,却顿时就愣在了原地。
“请问,”面前的那个人低头看着他说,“这里是伦敦吗?”
报童抬头看着他突然说不出话来,只是愣在那里,机械地点了点头。他从没见过这样的人,披着一件黑色的大斗篷,风帽拉得很低,几乎看不到那人的眼睛,只能看到没有血色的脸,和两片微启的说话的嘴唇。
“谢谢。”那个人微微笑了笑,把报纸递给孩子,继续往前走。
报童瞠目结舌地看着他走开,等回过神来的时候,只觉得手里的报纸有些不对劲。低头一看,报纸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点燃了!奇怪的是它们并没有着火,而是从刚才那个人拿过的那一边开始逐渐化成灰烬,眼看就要蔓延到自己的手上了。报童赶紧把手里的报纸丢掉,报纸就在地上像自燃一样瞬间消失,最后连灰烬也没有了。
春天——正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不是以温暖的春风,而是以冰凉的冷雨——宣告了自己的到来。那几天我把自己整日关在阁楼里,却始终没有想通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莉莉·艾施死亡当晚是克罗斯温最混乱的一天。据说她的父母带着警察风风火火地一起来了,闹得整个街区都不得安宁。当晚我在阁楼里听到下面一阵喧嚣,缩在墙角战战兢兢地不敢出声。艾施先生带来的人砸坏了大厅里所有能砸的东西,后台和化妆室也被他们弄得天翻地覆,剧院里没有一个人敢吭声。已经下班的院长刚回到家又被打电话叫了过来,被艾施先生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扬言如果不赶紧给他们一个交代,他就要放火烧光克罗斯温,让里面所有的人都为自己的女儿陪葬!他的这句狂言还没来得及兑现,更加离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就在莉莉·艾施死后的第二天,他的父母亲被人发现横尸别墅。据警方说报案的是他们家的佣人,打电话的时候说话一个劲儿地哆嗦,警察听了好长时间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赶到艾施家别墅的时候,佣人离开豪宅远远地等在大门外面,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了。她说自己家的主人肯定是惹怒了魔鬼,才会死成这个样子。警察想问她几个问题,她却一直在那儿胡话连篇,看上去已经神志不清了。一个警官让她带路,她却死活也不肯再踏进那座别墅一步。警察们无奈,只好自己走进偌大的豪宅去找艾施夫妇的遗体。结果当他们在卧室门口看到两人尸体的时候,吓得都不敢进去,其中一个年轻的探员当场就吐了,尽管那天早上他根本就没吃东西。这些话都是一个家里有亲戚在警局工作的同事在剧院内部传开的,被人们越传越邪乎,简直就是“血腥玛丽”再世。那个传播消息的人一再声称这绝对是独家报道,警方对外已经封锁了消息,声称艾施夫妇是丧女生悲自杀身亡。而那个见过他们死相的佣人,从那之后就丧失了语言交流能力。
风浪过了好几天才逐渐平息,剧院里的恐慌气氛也有所减退。一个礼拜之后的一天虽然下着雨,可是如果我再不出来透透气,不是被自己的想象吓死,就是会被在阁楼里活活逼疯。
“文海之家”在雨中看起来就像是一间被人遗忘的小屋子(其实自从我来到这个地方起,它就没有红火过)。我捋了捋湿漉漉的头发,轻轻地推开门进去。店主维克托尔森听到门上的铃铛响,从柜台边抬起头来。当我以为他会像往常那样热情地跟我打招呼的时候,他却只是出于礼貌地对我微微一笑:“欢迎光临,请随便看看!”
如果是在以前,我一定会想出点法子调侃他。可我现在明显没有那个心情了。
“您知道的先生,”我有些自嘲地笑着说,“‘醉翁’又来了。请问伊戈尔在吗?”破天荒的第一次,我上来就坦白了自己的来意。我不想再借用任何的理由来掩饰自己了,把自己关起来的这几天,我的心里一直在想着一个人。他就在这儿,他就是我频频造访这里的真正原因。他一直在我的心里,可我之前却总是用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饰这一点!但今天,就在这个觉醒的日子,我冒着雨专程为他而来,就是要告诉他之前一直没有勇气对他说的话:我知道自己一直想要的是什么,也明白能够为此放弃什么——我愿意放弃一切跟你走,再也不要追求那些没有意义的虚荣,而是要从此摘下面具和你一起去寻找一条叫做心灵的河流!
“抱歉,小姐,”店主平静地对我说,“这里没有叫伊戈尔的人。”
“他不在?”我说,“店里就您一个人?”
“不,”店主摇摇头,好像从来不认识我似的,“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人,这个小店里只有我自己。”
我听了先是一愣,随后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您就别拿我开玩笑了,”我说,“谢谢您的好意,可我今天状态不太好,所以……”
“不,小姐,我没有跟您开玩笑。”店主一本正经地说,“您恐怕是找错地方了。”
我顿时就不笑了,改为一脸疑惑地看着他。如果是一个不够自信的人,这时候一定会跑到店门外边去抬头看看店名。可是我确信自己不会走错,绝对不会!这里对我来说太熟悉了,我闭着眼睛也不会走到旁边的店里去!
我站在柜台前盯着他看,等着他突然放生大笑,然后像以前那样大言不惭地跟我调侃。
可是他看我的眼神越来越陌生,好像以前从没见过我。
“要是您忙,我就先不打扰了。”我说,“如果伊戈尔回来了,请您转告他……”
“我很想帮您转告,”店主说,“可是他恐怕不会来,因为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人来过。”
我顿时就无话可说了,可还是有些不甘心地朝里面张望了一下。一排排的书籍默默地陈列在木制的架子上,仿佛真的没有任何人存在的迹象。
“打扰了,先生。”我勉强地说出这句话,随后低头转身走出了书店。
走在路上,我几乎没有了方向。街上的行人在我的身边冒着雨匆匆地来回穿梭着,我却像是一只透明的影子一样,在人群中机械地迈着步子。我已经忘记了哭泣,可雨水就像冰冷的眼泪一样不停地在我脸上流淌。
先是一直和我作对的安娜贝丝被告知是我自己捏造出来的,然后是我一直深爱着的伊戈尔,他曾经是我心灵唯一的港湾,是我不让这座城市把自己吞没的唯一寄托。我曾经为了自己所谓的追求而忽略了他,以为他一直会在那里,等结束了这一切我随时可以回来找他。可是……
不知不觉地,我已经走到了特拉法尔加广场。天不作美,所有的鸽子都回巢避雨了,小广场上一片空寂。长椅上坐着那个我曾经遇到过的诗人,他正打着把黑色的伞,坐在长椅上静静地看着雨景,就像个天真好奇的孩子,又如同历尽沧桑的老者。
我默不作声地坐在他的旁边,他从伞下转过头来微笑地看着我。
“您好像很伤心哪,小姐。”
我也想对他微笑,可是嘴角刚抽动了一下,眼泪就差点流出来。
“先生,”我轻声地问他,“您见到过鬼魂吗?”
“我一直很希望能见到,”他说,“但是很可惜……怎么,您见到过?”
“而且还爱上了。”我说,“可是他就那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从我的世界里。”
“如果是那样,”他说,“每个人都见到过鬼魂。他们就这么奇迹般地走进你的世界,然后又悄无声息地在你的生命里消失。”
“所有美好的东西都这样吗?”
“是的。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什么是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可最珍贵的东西为什么总要错过呢?”
“这就是我们的愚笨所在。”他说,“这就是生命。”
我想我明白诗人的意思了。生命的意义就是在失去之后,懂得什么才是最珍贵的。而不是在那之前。这就是生命教会我们的方式。
当我走回到“文海之家”所在的查令十字街的时候,雨下得更大了,密集的雨点从高空落下,街道两边石砌的店铺小房静静地在雨中接受洗礼,有如被蒙上了一层梦幻的面纱。我站在路的对面静静地看着“文海之家”,此时的情景让我想起了初次见到他时的情景:一面流水的玻璃,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身影。现在想想,那个景象或许只是我看到的一个幻影,一个朦胧雨幕中捉摸不定的幻影。我把这个幻影当成了一个真实的人,并无法克制地爱上了他。
“风雨无情啊,姑娘,”身后的花店老板说,“店里一下又冷清了很多!”
我回头对着他微微笑了一下,突然好像想到了什么,迈步就朝对面的“文海之家”走去。
走进书店我没跟柜台后面的店主打招呼,而是径直走到里面的书架前,随意从上面抽了一本书,接着走回来一把将书撂到了柜台上。
柜台后面的店主抬起头来看了看我,想说什么却被我抢先开口。
“请帮我把书包起来。”我说。
店主又疑惑地看了我一眼,随即把书拿了过去,转身扯下一块草纸,笨手笨脚地在柜台上开始摆弄。摆弄了半天,他还没把书整齐地包利索。我一直看着他,他则一直皱着眉头。
“您根本就不会弄。”我说,“现在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以前那个包书很在行的人哪儿去了?”
店主放下手中不成样子的活计,叹了一口气。“我跟你说过了,从来没有过那个人。”
“那我一直见到的就是鬼魂喽?”我说。
“你既然能见到鬼,当然也能看见它给你包书。这个店里根本就没有在行的人!”
我顿时就无话可说了。这么说所有关于他的一切都只是我自己的幻想?
“我知道自己的服务态度不好,手艺也差,所以客户想象店里有一个各方面都好的人也很正常!”
“您曾经是个很热心的店主,”我说,“难道您忘了吗?”
店主扬了扬眉,做了个“我有吗”的表情:“那可能也只是你的臆想吧。”说完把包得一塌糊涂的书推到我跟前,“抱歉包得很烂。”
我默不作声地付了钱,拿着那本书走出了店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