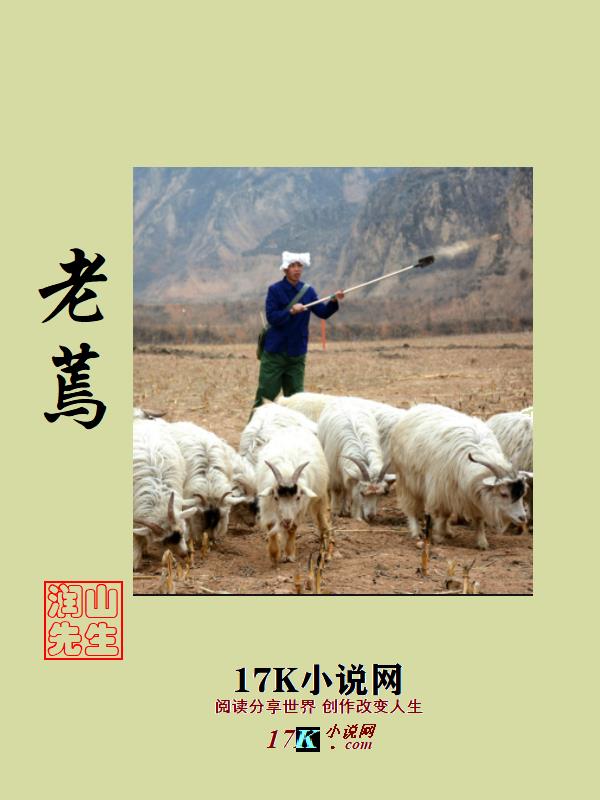物以类聚,人以群居。
穷人自然就和穷人住在一片地方。
为了活下去,不管是你争我斗也好,还是相互帮忙也罢,时日久了自然就相熟了。
“你帮我去找一些人,我要把后面这一片胥耶林里老胥耶都摘下来,工钱……你觉得多少算合适?”
南宫晚棠本就是来自异世,原主又是大富大贵的人家,自然不知晓这平民百姓做一日活该是多少工钱。
给多了,不仅会被人当冤大头,还会因为破坏了行情而被人针对,给少了又没有人愿意来做。
夏立有些惶恐,小姐竟然问他该给多少钱。
稍微想了一想,他伸出了两个手指:“咱们去打临工是二文钱一日。”
他又伸出了三个手指头:“到港口搬货,能有个三文钱一日,若只是采摘胥耶,给二文钱一日已经足够了。”
“那就给够三文钱吧,你去找一些人来,年龄大一点也无妨,只要人老实一点,没有那么多的花花心思。”
顿了顿,南宫晚棠又淡淡道:“今日之内,人要到齐,能做到吗?”
“能。”
“那去吧。”
夏立行了一礼,转身离开,走了两步,他又停了下来,欲言又止。
南宫晚棠如何不知他的心思:“我不是个记仇的人,只要能改过自新的,我都会收。”
夏立顿时心里一喜:“是,小的晓得了。”
这么多年,多亏老胡一家帮忙,不然他和阿奶都活不到现在。
如今有这么好的活计,他也想拉老胡一把,可念起老胡之前对小姐做的事,他便不敢开口,幸好小姐是个不记仇的。
他心里有了念头,脚下的步伐加快了许多。
南宫晚棠也不问他如何做,也没告诉他要多少人,全看他自己的领悟能力,太过死板,推一推才动一动的人,她不想要。
老胡为了帮他愿意去做傻事,在明知道可能会被砍手的情况下,他还勇敢地站出来替老胡承担罪责,可见他们都不是坏人,就是情急之下,用了最差劲的办法而已。
若是夏立做得好,她不介意拉他出泥潭的。
夏立首一个就到了老胡家中。
老胡的儿子胡玄冰正在院中劈柴。
老胡媳妇就坐在一旁的小椅子上缝缝补补,嘴里说的是南宫晚棠那日在海边救胡玄冰时的情景。
夏立来的时候,老胡媳妇正说到开药方那儿。
瞧见夏立过来,老胡媳妇便停下了话头,朝夏立道:“怎么过来了,是不是你阿奶有什么事?”
“谢谢!”夏立接过胡玄冰端来的水,一口饮尽,用衣袖胡乱抹了抹嘴:“我刚从南宫家过来,南宫大小姐要找人做活,三文钱一日,我来看看胡大哥去不去?”
老胡媳妇把针线篮放在地上,站起身,疑惑地看着夏立:“三文钱一日?真的假的?”
也不怪老胡媳妇不相信。
她们也是跟着父辈抄家流放过来的,自然知晓同为抄家流放的南宫家能有多少银子,莫说招人做活,就是解决自己衣食住行都不够。
“听小姐说是要摘胥耶,我寻思活儿也不重,一来能赚点银子,二来能帮到小姐,算是赎罪,也算是报答,所以我就来问问。”
夏立伸着脑袋往屋里张望:“嫂子,胡大哥呢?”
“刚去后边翻地,冰儿,你赶紧去喊你爹回来,唉算了,我自己去,等你磨磨蹭蹭,人我都喊回来了。”
老胡媳妇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线头,快步往屋后走去。
没一会儿,老胡夫妻俩便回来了。
老胡老远便喊:“你说的是真的?”
“我还能骗你不成,你去不去?”
“去,不要工钱我也得去。”
老胡一拍手掌,心意已定。
一旁的胡玄冰看着几人,一个想法如同种子一般,在他的脑海中落地生根,萌芽成长,最后成为一颗参天大树,且愈发茂盛。
自从知道自己已经没了气,南宫大小姐还能把自己救活之后,胡玄冰对南宫晚棠既感激又崇拜。
原本漫无目标的生活,突然就开了窍,他觉得往后的日子都有了奔头。
他想跟在南宫大小姐身边学医,不说能做到南宫大小姐医死人肉白骨那个地步,能治个伤寒拉肚也成。
不管是要签活契,还是要签死契。
只要能跟在南宫大小姐身旁,他做牛做马都愿意。
反正他也是流放犯的后代,没有大赦,他一辈子也只能这样了。
倒不如,跟着有本事的人,兴许还能有一番作为也不定呢。
胡玄冰把斧子一扔,冲到老胡夫妻两人面前:“阿爹阿娘,我也要去干活,我想留在南宫大小姐身边做事。”
老胡夫妻俩一愣,以为他也是要跟着去摘胥耶,便问夏立:“南宫大小姐要多少人?”
夏立笑了:“那么大一片胥耶林要摘,估计得要一二十人,咱们都去,看小姐要多少人,不行咱们再回来就是,我还得去喊别人,你们在村口等等我。”
不到一个时辰,夏立便带着人过来了。
茯苓来报的时候,南宫晚棠正在房里提笔写着详细的计划。
闻言,她放下笔,拿起纸张吹干墨迹折起来收好,才站起身,去一旁净了手:“那就过去看看。”
前边院里,人头攒动,把小院挤得满满当当。
夏立和老胡就站在前头。
老胡身边的少年郎,南宫晚棠也认得。
正是刚到琼州岛那一日,她在海边救起的那一位少年郎。
瞧见南宫晚棠过来,胡玄冰远远地便朝她行了一礼。
南宫晚棠点点头,径直来到廊下。
周昇搬了一张椅子过来。
南宫晚棠刚坐下,便瞧见晴儿也搬了一张小杌子坐在她身旁,一双眼睛清凌凌地看看众人,又看看长姐,脸上的笑容里带着满满的兴奋。
“长姐,你要做什么?”
南宫晚棠宠溺地揉了揉她的脑袋:“长姐有事要忙,乖乖坐好。”
“好。”
毛茸茸地小脑袋轻轻点了点,然后真就直挺挺地坐在那儿,双手放在膝盖上,像是个初入学堂的幼年学子,又好奇,又懵懂,又乖巧,让人看了心底发软,不由自主的想答应她所有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