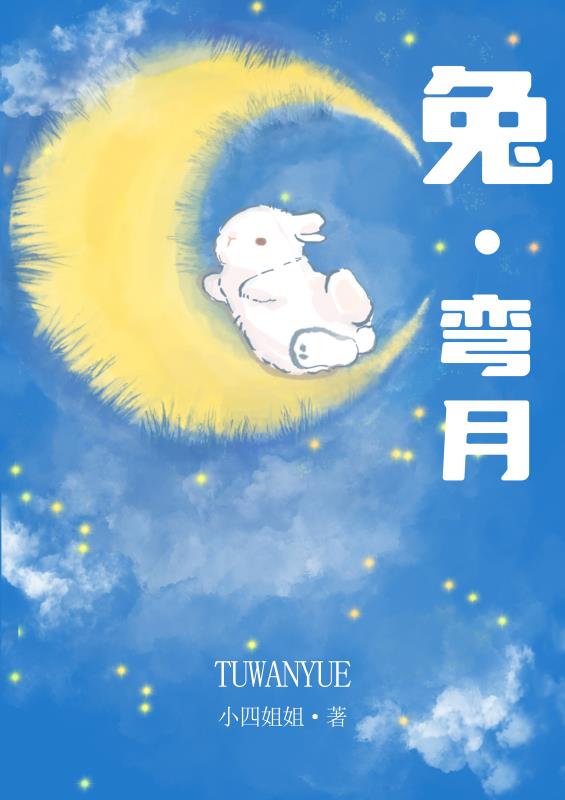却说那打电话的正是江成的父亲江利,告知江成他母亲被车撞倒,在XX医院重症监护室昏迷不醒!江成脑袋里“翁!”地一声,眼中充着血丝,泪如泉涌,跌跌撞撞地爬起来,胡乱抓了衣服到包里,疯一般冲出了酒店。在路上忐忑地摸了好几回那张存有打工所有积蓄的银行卡,自我不断安慰祈祷:不怕!不怕!您一定要坚持住!咱们有钱!有钱!一定没事的!
一路上,江成心如火焚,不断催促的哥加速,觉得分分钟如年漫长,煎熬了不知多久,终于飞到了医院。到了医院,江成才得知母亲被车撞倒后并无大碍,只是腿脚受些轻伤罢了,可司机自以为那处并无监控,生怕被讹,竟丧心病狂地将老人拖行了数十米远,无法动弹,想那死无对证已定,方扬长而去。俗话说:人在干,天在看,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那时恰有一位姑娘在枫树下录制短视频,刚好录到这一幕,由此铁证如山,罪无可逃。
江成泪如雨下,喉咙痛地针扎一般,无法言语,心里七刀八刀乱搅,失神地透过监护室的门,只看到母亲静静地躺在那里,几个医护人员忙忙碌碌地左来右去,江成想叫一声“亲娘”,脸上淌着泪,胡乱地翻看衣箱,想把为您精心挑选的新衣让您试穿,想偎在您的怀中再撒娇一回,想再吃一口您亲手做的热气腾腾的面条,想再听一听您慈爱的批评。。。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了遥远而痛苦的奢望,而我们母子间也徒增了这么多冰冷的阻隔!“您要坚强,一定会挺过去的,您的一生经历了那么多风雨,这点儿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您真的要走的话,”江成哽咽地用牙狠狠地咬着手臂:“那便带孩儿一块儿走吧!没有您的世界,是永远的孤独!没有妈妈的家,孩儿不想回!”手臂上的血一滴滴和泪水滚落下来,混在一处,明晃晃地,是那么刺眼。
“老子有的是钱,你说个数,咱们可以私了的!”肇事者见逃无可逃,接到警方电话后,第一时间先奔到受害者家属处,拿着一大堆营养品,欲花钱消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此时江成正自悲痛欲绝,见父亲还同那个杀人黄毛司机语论喋喋不休,仇恨之火顿时铺天盖地冲入命门,一时不知被什么操控了,还是内心的有些东西突然苏醒了,万丈火苗心中起,眼里尽是血红赤丹,面部青筋无不暴起,双拳一握,全身的气血似乎一下子被感召而来,风一般扑过去,眨眼间到了黄毛司机面前。黄毛正在和江利求和,哪料空中突飞来铁锤般大小拳头,直击太阳穴!只一下,黄毛的眼神便定在了那里,舌头不及伸回,倒了下去。江利见又生一祸,忙死死抱住已杀红眼的江成,江利使尽全身力气竟快被江成挣脱,忙大声呼喊在旁的亲戚搭手协助,几个人齐齐上手,才勉强将其按住。
医院又一次启动了急救模式,黄毛司机被拉入抢救室。几个小时后,医生无奈地做出结论:“颅脑受损严重,语言障碍,以后恐怕不能自主行走。”直到此时,江成似乎才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医生通过黄毛的手机找到了他的家属,家属到了医院,又哭又闹又骂,撕扯着江成的衣服,拉拉拖拖,又拍又抓,江成面无表情地竟也任由其胡闹。警察一会儿便到了,江成直言不讳地供认打人之事。临走时,长跪在监护室门外,满眼泪水,依依不舍地磕了无数个响头,额上渐有血渍,转身再回首,泪已纵横:“儿不孝!您要好好的!”来到父亲面前,从口袋里取出那张银行卡,交到父亲手里:“这是我这几年攒下的,有200多万吧,给母亲看病应该能顶上一阵子,如果不够,就卖了房子吧,一定要将母亲治好!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父子,我进去了,一切都要靠您了,照顾好母亲,也照顾好你自己!”江成痛苦地在脸上挤出个乐观的笑态,对着父亲,和警察转身离开了。江利泪水盈眶,看着儿子渐行渐远的模糊身影,痛而无奈地连声叹气。
又过几日,江成母亲各项指标稳定且脱离了危险期,便被缓缓送出了重症监护室。人虽睁眼了,但大部分时间皆在睡梦里,偶尔睁开眼,也只是疲惫不堪地瞅人两眼,满目苍茫,丈夫,亲戚,一个也不认识了。似这一病,将从前所有痛苦的,美好的记忆一次清零了。人若活到不问从前是非,喜怒哀乐,便也是一种境界。不过这种放下,似乎又有些太过悲凉和惨痛:生活不能自理,气管,胃管,尿管等等管子一大堆,像株植物却不是,有呼吸却不知何时断供。
妻子自脱离了重症监护室后,江利一个人本就有些吃不消了。什么都要靠自己,吃喝拉撒样样无菌流程。刚转个身,病人的痰卡了,你要忙呼医生,防着痰堵气管,片刻要命。吊针一天里,半天都在打,你要边吃饭边留着神。病人每日需数次翻身,外敷中药,针灸电烤,不能落下。一日接一日无缝衔接,一周连一周紧锣密鼓,想那江利也是半百的年纪,三折腾,二倒拉,终于有些熬不住了,在医院楼道里一脚不稳,差点儿一头栽下去,恰巧此时医院一护工从身边经过,忙上前扶住,才稳了下来。江利抬头看那护工:秀秀的眉,瘦瘦的脸,长长的腿,高高的个儿,年龄虽近中年,未饰粉黛,却藏不住几分好颜色,不禁多看了几眼。且说这大医院做护工的人本是形形色色,长于和不同人群打交道,思想也较为开通,善于嘘寒问暖,示好讨乖,见江利形貌衣着有些讲究得体,又独自一人身困此处,想必是有病人在医院,劳力太甚,需帮求助。随前后揉捏捶打,以示勤快,技艺精通。江利连月操劳,本是身疲情乏,突被这一通忽紧忽慢的操作服侍地舒舒服服,含笑在心里,不知是个什么想法,坐在那椅子上分明是不想起来了,竟忘了病床上的结发正卡痰喉结,痛不欲生。开始的时候,二人还分坐在走廊椅子的两头,你一言我一语。待话多语畅,渐渐熟络起来,二人近了一步,到了最后,二人距离只差一拳。江利倒葫芦似地将苦水和煎熬一下子倾了出来,老泪纵横似孩子般委屈、无助。护工徐娇满面同情悲苦,似自家心上覆有无尽哀愁,挥之不去,让人怜惜,欲要将面前这个男人头面揽入怀中,让他痛苦放松一回,却又觉得太过仓促,怕人笑话自己轻薄。随亮了职业,愿帮大哥生活所难,江利笑脸含泪,二人就这样一日日走近来,成双出入,共迎晨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