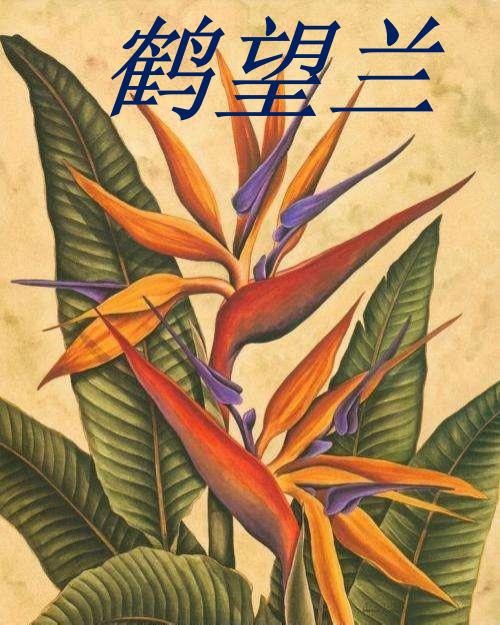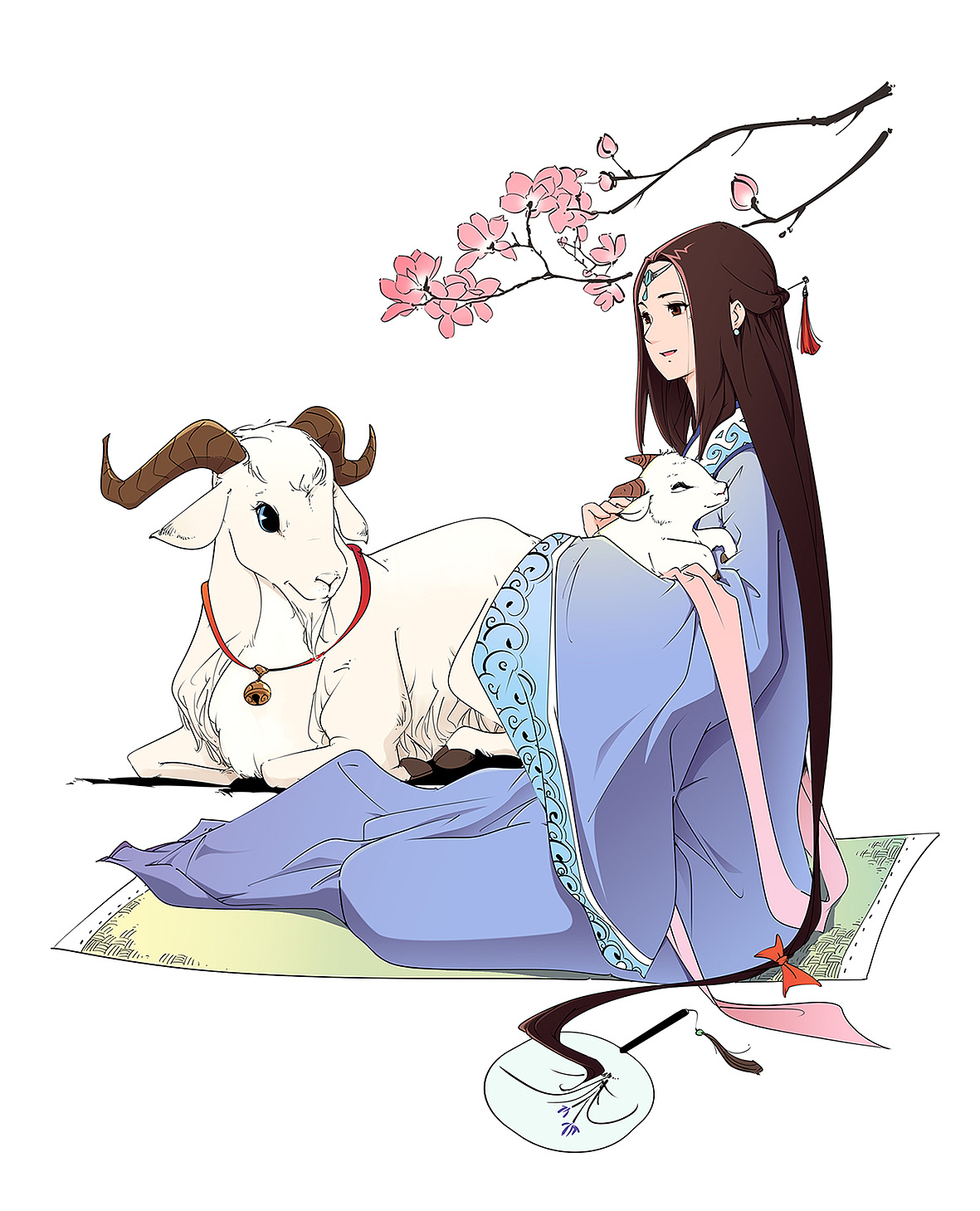且说那青儿满腹泪水,看着眼前人不是江成,恨那混蛋,又想得十分。郁郁地一个人强颜欢笑,在婚宴上喝了一杯又一杯,杨耀猜地几分道理,心痛地劝了好几回无效,只恨不得将那情敌碎尸万段,方解其恨!出了宴会厅,打电话招来几个黄毛混混,脸阴沉地杀气重重,对那为首的头儿嘀咕了几句,便又进宴厅,笑脸迎客起来。
人常言天地莫测,风云变化,世间事少有同一而语,岂容被轻易窥探,由不得你胡作非为,一切自有术数。芳儿斜斜地依在江成肩上,望那空中乌云密布厚重苍劲,看那雨丝亦万般柔情,想着林青青已嫁,江成的好便尽数收了来。但此处多有二人感情遗迹,难免睹物思人,不如尽快下了江南,早早完婚,好过在此处异乡陌生。于是便劝江成道:“林青青已嫁作他人妇,自此再与你无关系,伯母不幸,伯父也不必你记挂,你那么重情,留在此处尽是伤心悲痛不绝,不如今日便备一备,明日起早一块儿同我下江南,你看怎样?”江成见提到青儿和母亲,心里自不是滋味,深情地环顾这诺大的屋宇,空荡荡,好不凄凉,却也只是舅舅暂借处所。茫茫苍宇,曾经在这一片故土上,有多少美好的故事发生,山水土丘然在,花木年年荣衰更替,如今却没了自己容身之所了,伤心地点了点头。芳儿见江成答应了,忙取来两把油纸伞,对江成道:“我们先到伯母坟前去祭拜祭拜,然后再去告别舅舅。”江成接过伞,深情地看着芳儿:原来这一世,我从来都无法抉择我的喜好,还妄自尊大什么。后半生竟也是与你纠葛,原来的原来竟似梦如幻,亦真亦假了。合上门,二人相依相偎地消失在了雨中。
再来说这帮黄毛绿毛泼皮,每次打打杀杀完总会得到杨耀公子不少犒赏,足足够好几个月挥霍玩乐。这次听说收拾的主儿一定要使其断上三根肋骨或废条腿脚才可。又言加大了赏赐,个个脸上皆挂满了喜乐,摩拳擦掌,手舞铁棒,虎狼般扑向了江成的居所。一路颠簸,终于寻到了晦气处,见门栓挂搭着,其中一个黄毛对大哥绿毛道:“看样子这小子不在家,倒让咱兄弟们扑了个空,只是这回去又怎么交代!”绿毛面不改色道:“人应该没走多远,让兄弟们先进屋歇歇脚,留两个在门口把风,见那小子回来,立刻支应。”一行人涌进了屋内。却说那隔壁有个李婶儿出门买菜刚怀来,见一帮人凶神恶煞地破门进了江成家,忙急急的奔进屋子说于丈夫听,丈夫听后冷冷道:“你真是吃饱撑地慌,狗拿耗子,那儿那儿有你的事儿!你既知歹人,专来告我,就不怕我斗不过歹人,被他们杀了?!我若死了,你好跟江成舅舅过好日子去呀!”“放屁!打我上世来,就没见过你这号胡搅蛮缠的,你不就是记恨江成舅妈年轻时拒绝你,选择了他舅吗!别以为你那点儿破事儿别人不知晓,不帮就不帮,真倒是烂泥你别扶,痞劣货从来正事不干!”“你!”男人暴跳如雷,气歪着嘴,在地上来回震脚,欲骂将回去,妻子却管你吹鼻子瞪眼,胡转乱闪,自个儿悠悠先进了里屋,男人愤愤地在原地抓狂,等妻子进了里屋,蹑手蹑脚来到门口,微微压一条门缝儿,见妻子面急心焦一次次按了电话的重拨键,似乎那边儿并未有人接听,心下狠狠道:“一定是给江成他舅打呢!他妈的!一天吃喝着老子的,却想着外面的如意,净操心琢磨人家男人的冷和暖,把自家的祖宗田地晾在一边当成了废料场!”欲冲进去骂那婆娘个狗血喷头,猛地直起腰板,却忽有些心虚:这自己的老底儿媳妇儿尽知,一会儿开骂上了头,她要是不管不顾起来,将那陈年往事尽数给左邻右舍抖搂出来,岂不是惹了大麻烦?!心中只觉闷闷地自回屋中喝起酒来,喝了半会儿,脸红扑扑的,望碟中的花生米少之又少,摇晃着去厨房取一些来,见妻子正备着下午饭,心下有些快慰,想着你江成舅得意个毛线,我媳妇正在为我做饭呢,一会儿还要为我洗衣打扫庭院,到了晚上是我和他同眠共枕,不是你!似刚才并无吵嚷,各自也并不言语。男人端着满满一碟子花生米来到里屋,看着酒杯中自己苍老的倒影,叹了一声,忆起当时年少风流倜傥,咂着嘴咧开了少颗门牙的嘴巴,偷乐一回,喝了一杯又一杯,只觉酒香甘醇,侧身又去抓花生米,竟不由地倒在一边,眯着眼,甜甜地入梦了。
李婶儿一会儿便将饭造好了,去屋里叫丈夫吃饭,远远地便闻那鼾声如雷,也不进去了。一个人自思道:这会儿,那帮杂毛该走了吧。出门故作倒水,却仍见二个混混游来荡去门口,面色突凝重起来:这帮人来而不走,莫非是有意要等江成归家寻仇滋事?!想那江成孩儿母去父弃,孤身一人,怎斗得过这帮“歪脑壳”!又忆起江成母亲在世时广播慈爱,二人也曾掌灯同窗共读,心下悲悯连连,感慨万千!忧心忡忡:盼江成千万不要此时归来,恨自己又妇道人家一个,手无缚鸡之力!正急间,一条妙计上了心头。
再说江成门口那两个黄毛,远远便嗅到了屋内的酒肉香浓,想着正是饭点儿,兄弟们都饿了,拿他家些东西煮了吃喝定会分自己二人一些,不想香愈浓肚愈饥,屋内欢笑声碰杯声一片,二人在外吃着冷风,干着急,巴望着,唾液咽了一口口,就是等不来酒肉面前,气便不打一处来,一个骂道:“这帮孙子!只顾着自己快活,倒把你我兄弟做傻蛋儿来扛门,咱们俩儿挪活不挪死,也去那厨房取个一二来,要不等会儿连骨头渣渣都不剩了!”另一个点头称赞。二人就这样一个去拿酒,一个去取肉,一时间,门口竟无一人值守,李婶儿眼尖,拿出备好的虎头锁从外将门一拉,锁死,牢牢地将众毛怪囚在了屋内,喜乐地转身去准备其它物事。此时天将暗下来,东边的乌云低沉沉,雨也住了,枝头的麻雀逗趣地飞来飞去,一会儿又不知到了哪里。那刚才门口的二毛兴冲冲从屋内携一大堆酒肉自得地奔将过来,到了跟前,却见门合上了,以为是夜风,推了一下,竟不开,又一脚踹过去,那门不开反将整个人差点儿弹飞,二人不觉奇怪,仔细从门缝儿一瞧:我的天哪!拳头大的一个铁疙瘩锁,死死给锁上了?!莫不是主家回来了?!发现了端倪?从外先锁上?忙着去叫人?不放过一个?!想想都后怕,口中肉顿觉无味,喝口酒也苦地难咽,忙奔进正堂,向老大绿毛怯怯报告道:“我二人去方便,不知谁从门外上了锁,门打不开了!”绿毛半口酒在口,突喷了出来,眼睛瞪地差点儿上了额头,怒怒地上来,一脚一个:“你俩怂货同时尿急?!”二毛倒向一边。绿毛急奔大门口,余众尾随其后,绿毛到门口用手电筒透过门缝儿仔细研习查验一番,来不及搽去额上的冷汗,惊慌道:“这他妈肯定是要将我们一锅端了!赶紧撤离!若有半分迟疑,等对方人都到齐了,我们兄弟人生地不熟,被关门打狗,必死无葬身之地!”众人本无主意,听大哥这么一分析,个个慌得六神不稳,四散跑开去找这间屋子的后门,寻来找去,怪了!这间屋子竟无后门?!众兄弟齐齐地奔来向大哥禀告。绿毛听后一头雾水,酒醒了几分,懊悔不已。忽听门外由远而近似脚步声齐齐有节奏踏来,夹杂着锣鼓声阵阵威武呼喊,正门方强光忽忽闪闪不一而定,众毛怪不由得向大哥靠拢来,个个急的似那热锅上的蚂蚁,惊恐万状。
绿毛警觉地环顾四周,身后南边门已上锁,北边无后门是屋宇,东边人声鼎沸,鼓噪喧闹,唯西边静幽,来时无意间发现是个菜园子,可赌一把!忽见那门缝光闪频频加快,想是人又多了数倍,忙大声疾呼:“翻西墙!快!”众毛得令,早脚底抹了油,飞将墙根儿。这帮人要说行侠仗义定是无,翻墙打家劫舍全在行,墙虽高,个个勇猛矫健跃身起,片刻间“咚咚咚”已落于墙外,人人脸上现出才脱樊笼之欢喜,张三夸李四身手,李四赞王五不凡,但个个却只觉身上黏黏地,臭气哄哄,一时也顾不了那么多,气喘吁吁地飞跑了一阵,见离那怪屋远了,人声嘈杂也似有似无了,才缓缓地歇下心来,在路灯下一观,我的那个脑瓜壳子,个个身上尽是屎尿,肮脏糊糊不堪!原来那西墙的菜园子昨日才上了数车人粪便,备着干上一阵,翻到地下,来年种些瓜果蔬菜。不料被这伙儿酒肉先尝了个鲜,连涂带抹拖拖拉拉所剩无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