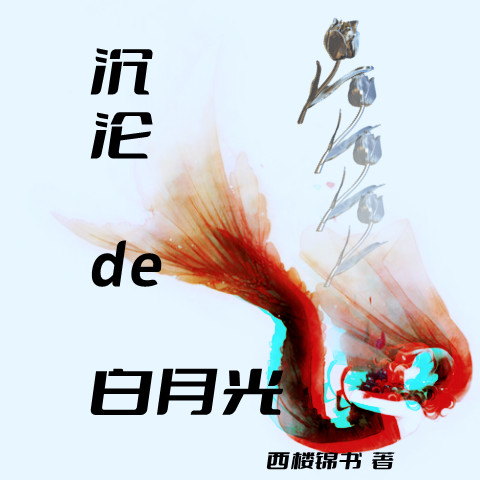却说江成自呕出邪阻淤血来,只觉梦醒眼亮,没事儿人般站了起来,见众人笑,自己也笑,唯芳儿喜极而泣。蒋媛走过来将如何救起江成之事说与他听,问他怎就倒在了泥水中。江成此时神智已明,被这一点拨,突想起青儿愤愤奔去的伤心欲绝,胸口突如炸裂般,心摇神荡,安宁不得。望那众人期盼的眼神,苦笑地找个借口,转过身,早已泪流满面,扑向自己的房间。众人疑是病留症然,未至痊愈,随行诡意怪,郑大夫却道:“已无大碍,需静修数月便好。”舅舅及几个直系亲属本欲再去敲门挂问,听此话,也就止了步,又商议将宴客之事只得往后推迟了。芳儿皱着眉,巴巴地望着江成的房间失神,嫂嫂见状,上前拉了她的手:“没事儿的,休息一段时间便好了,你且先跟我回去,改日再来,那时你的如意郎君便神采奕奕了。”芳儿边走边回顾身后,却并未见江成出了那个房间。亲戚朋友有到舅舅家去的,也有先回去至约好日子来的。一会儿厅堂上便只剩下几个邻里帮忙整理物事的了。
江成在房间里不知来回踱了多久,缠绕在心头的情思结成了疙瘩,扭成了团,死死地堵住了心门,纠纠不放,动一动便痛彻全身。望那窗外的雨丝在黄昏暗色的掩护下,平添些神秘和静谧,夜幕徐徐划近,日复一日,终将耗尽世人所有的珍贵,低着的头猛然间昂挺,喃喃自语道:“愿我今日的冲动不成为残忍的掠夺;愿你执着的选择他日不后悔悲伤;愿我们悄悄地走,不给爱我们的人留下无尽的苍白和失落。”拿起电话,眼里憧憬着淡淡的期望,欲打给青儿,电话却恰在此时打了进来。一看号码,他乐了,竟是青儿!真是说谁谁到,想谁谁痴。江成欣喜地欲起了乐子,逗青儿一回,那边儿电话里却传来了冰天雪地的寒音:“江成!首先祝你新婚快乐吆!这么大的事儿!也不告我一声,真够小气的!好歹我们也好了这么久,你可真没良心哪!说散伙就散伙,说不玩儿了连个人影儿都没了,这至于吗!哦,对了,你还不知道吧,我明日便也要结婚了,我的这位郎君呀,家里有钱有势,又长得帅,比你好多了!”江成无声地落着泪,心如死了一般。青儿不知怎的,明明在笑,眼泪却不争气地一个劲儿往外流:“明日娶亲的要路过你们家门前,你若还记得我的半点儿好,便出来看看我,就当是送别一个普通朋友去远方,因为她也许再也不会来了。若你有事,就当我没说!”不及江成回答青儿挂了电话,关了机,嚎啕大哭起来:“为什么?!为什么?!我对你那么好,将你视若眼睛,我的命,你口口声声甜言蜜语,一转身,却娶了别的女人!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在乎过我的死活吗?!你要结婚了,那我算什么!全天下最大的傻子吗?!”
江成突觉自己的世界天摇地荡,心的位置突飞来数把利刃胡乱翻搅,“哇”地一声,满口的鲜血喷在了地上,似一朵奇异的花,散发着让人窒息的气味。突觉一阵阵心焦口苦,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若再犹豫,怕是来不及了,此生便要真的失去生命的至宝了。显然,他已后悔地要死,心急如焚地将电话拨了过去,竟是关机,又拨过去,又关机!“青儿呀!你这是在惩罚我吗?”江成眼角挂着泪,疯一般冲出了门外,直奔青儿家。
一路上江成心牵着青儿出嫁之事,心神恍惚不定,不知跌了几跤,痛也不知,土也不拍,踉踉跄跄,跌跌撞撞便来到了青儿家门前。只见大门紧关,按了数次门铃,竟无人来开。又拨青儿电话,依然关机。急地满头滴汗,在门前焦急地踱来踱去,不知如何是好。原来这世间姻缘本是一刹那两重天。什么天造地设,什么青梅竹马,经不起一个符拍的错乱,挡不住一句妄言。
青儿给江成打过电话后,急匆匆,气呼呼抱了从前所有江成送她的礼物,流着泪,痛不欲生地去了二人八年前偶遇的地方——爱满庭。青儿的母亲为女儿去置办陪嫁物品,这两日一直很晚才回到家。
青儿的父亲眼看着女儿嫁入“豪门”,想着自己在不久也将如日中升,只觉天高地阔,精神振奋。早早地到了家,开了往日舍不得的陈年佳酿,翘着二郎腿,哼着京曲儿,边品边沉浸地咂着嘴。忽听门铃震响,摇摇地走过来,透过猫眼儿一观,见路灯下那小伙子怎如此神似一人,揉揉眼再望去,可不就是那混小子!思想着:这小子此时来定是不善,冷他一冷,挫了锐气,自会散去。于是归到屋间,门铃复响,也不去理睬。一杯接一杯斟饮,不多时酒菜便已过半,昏昏然半飘半浮起来,只觉体沉欲眠,刚躺下,那门铃又炸地一声响起,正值口干舌燥,又添心烦意乱,带着七八分酒气,怒目圆睁,冲到门前,打开门,果见是那小子,气便不打一处来!江成见门开,是青儿的父亲,如久旱遇了风云变幻,希望在即,上前忙赔笑拘谨道:“叔,青青在吗?我找她有急事!”说着往门口走去。“干什么!干什么!”青儿的父亲用身子堵住了门口,一脸鄙夷,狠狠地在地上吐了口浓痰:“你个没皮没脸的,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什么德性,整天纠缠我女儿不清,今番还找上门儿来了,你是不信我会报警吧?!”江成哀道:“我们是两情相悦的。”“呸!还相悦呢!真不害臊!你一个穷光蛋,吃风喝屁的,还来祸害我女儿!还大学生呢?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呀!”“您说话别太欺人。”江成有些听不下去了。青儿父亲冷冷道;“就欺负你了,怎么着!我还要痛打你这丧家犬呢!”猛抄起门后的木棍扑了过来,江成冷不防木棍已到跟前,撒腿就跑,边跑边大喊:“青儿,嫁给我!青儿,嫁给我!。。。”青儿的父亲到底年老体衰,加之又喝了些酒,气喘吁吁,自是赶不上小伙子。江成在原地跑了好几圈,喊得声嘶力竭,屋内却并无回音,也并未见青儿出来,心早凉了半截,又想青儿父亲刚才堵在门口,强不让进,青儿定在,却又不出,片刻间心室冰雪皑皑,似全身的一半儿血液皆冰镇住了,顿觉神衰意落,举步维艰。青儿的父亲见前面狂奔的人突似泄了气的皮球,已没了力气,大步向前,上来就是狠狠地一顿棒棒捶捶,打了一阵又一阵,那年轻人似傻了般,不格不挡,棍棒虽如雨点,却似打在了别人身上,与自己毫不相关。青儿的父亲还有怒气未消,突被冷风一吹,带走了几分酒气,却不知怎也下不去手了。看着江成低着头,一句话竟也不反驳自己,慢悠悠地走向远方,心里竟不知突然多了种奇怪的滋味。
深秋的夜风冷飕飕的,无情地撕扯下昨日还绿意怏然的枝叶,呼啸了一阵又一阵,似在随时准备接引冬的到来。那漆黑的远处的星星点点又是谁家的灯火,是否其乐融融,是否又争吵地喋喋不休。江成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此刻自己的身体竟是如此地虚弱,被冷风一浸,全身的毛孔似都在哆嗦。他使劲儿裹了裹衣服,恍惚地不知自己为什么又走在了这条似曾熟悉而又陌生的路径上。那座夜色中只有半截影子的房子分明就在眼前了,却怎么也走不到。突然,一个名字在他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对了,青儿明天要和我成亲的,我怎么在这里?什么都没准备呀,我得赶紧回家!江成脸上浮着怪怪的笑,疯言疯语地自我诉诉,忙奔跑起来,一会儿气喘吁吁地终于到了家门,屋内竟是一片昏暗,他急了,将庭院所有的灯烛一齐打亮,向屋内大喊道:“都快起来!不要睡了!明日我要大婚哪!。。。”也许他已经忘记这屋里从来都只住着他一人,喊了数声,并无一人应答,那荡来荡去的回音也渐渐淹没在了夜的静寂中,慢慢地,他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散去了,终于低下了头,心头蒙灰一片,哽咽道:“妈妈!你在哪里?他们都不管我了,我好想你!”转过身,泪已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