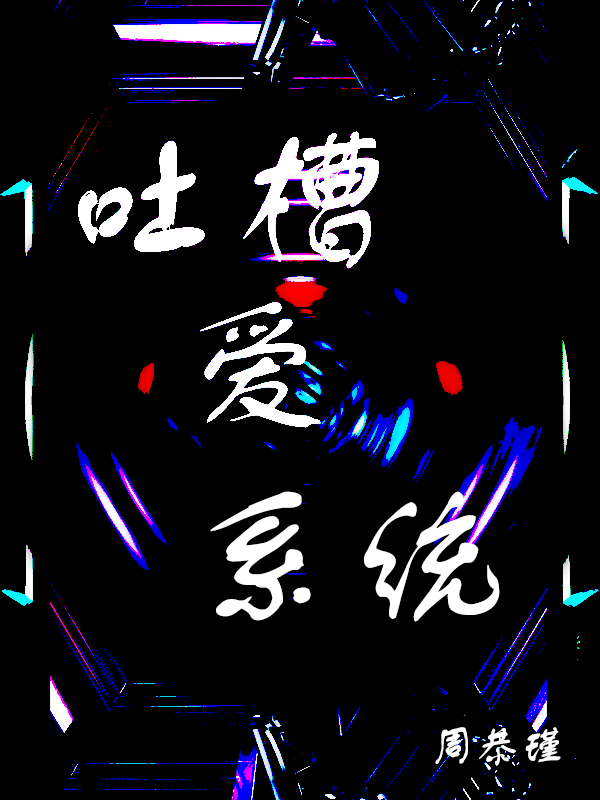此时见到这情景,非但不喜,反而有些恼火,立刻不和这地涌夫人如同往日般客套。一甩袖,背向窗外怒斥道:“夫人既然为有道女仙,又是有生祠香火的女菩萨,为何在小弟面前如此大放情怀?还请自珍自重自去!”
“弟弟糊涂,这双修的法门,又怎有不近女色的法门?”地涌夫人辩道:“道门也分全真、正一,有三宗之分。我密宗虽然名声不显,可也是降魔的佛家正派,怒目状的金刚,又非邪道,怎么就放荡性情了?”
“夫人自当言之有理,可小弟自有自的坚持,这男女情爱交合之事却不能如此随意,还请回转!”
张诚决绝,而这老鼠精听了则是愤慨,也不如开始的含情脉脉。
“呵,原来如此,还什么七尺男儿,血气方刚。”她一合衣衫,“原来是个不吃酒的糟鼻子——枉担其名!”
“才子佳人,风流韵事古今皆有,这自是大千缤纷,不过小弟却也有小千方圆。”张诚傲然一笑,“却是夫人多虑,某已有意中人,从此不二色。”
“你——哼!”
这地涌夫人听完此话,更加的恼火,却是这到嘴的肥肉想要跑。
心中暗自思索,今日咱就莫说吃与不吃俩可之间的事,见了本姑奶奶的男人只有急色脱衣就上与慢色耳鬓厮磨调情的,还没有碰见这么个石头性格的,便是石头,姑奶奶我也非要嚼碎了吃!
“定然是那个小浪蹄子,让这石头疙瘩念念不忘,坏老娘好事!”
想及此,她银牙紧咬,冷笑一声,撂下一句“走着瞧”,便裹着衣裳怒气冲冲的出了房门,然后一挥手,带着侍里俩旁的女婢往回走。
话说这无底洞天真是个好福地,虽无飞鸟走兽,却这梅、兰、竹、菊四君子四季常青,桃、李、杏、梨、枣五果常有,连片成群,端是个漫步观赏的雅处。这地涌夫人有心,特意将张诚师兄妹的房间隔的远,不过沐凝冰素来喜花爱草,每日研读疲倦,就独自到这林间游玩。
却是今日二人在房中争执的声音大,正好被在这林中的沐凝冰听到了,闻讯赶来,还没有走到大路,就见屋中出来了个地涌夫人,衣衫不整,春光半泄,双颊飞霞。
常言道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眼见为实,她看到此番情景,马上自觉晓得了其中的道理,真要让她说,她也说不出来,反正既是悲伤又是失落,不过紧接着便是愤怒。
“哼,果真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果然是人不风流枉少年。”她敛住气息,隐入林中,闻着面前扑人而过兰麝气,看着那绝色佳人影,凄然一笑。
“枉我身中寒毒,原来有眼无珠,错看一丘之貉!”她一把捏碎身边竹竿,恨恨想到,“好,既然敢伤我沐凝冰心,定叫你等十倍奉还。”
她切齿横眉看了一眼远去身影,然后又冷笑的看了一眼茅庐,便又隐入竹林之内。
却说俩个女人是不知不觉间结下了恩怨,而张诚自己反而成了无妄之灾的对象。
不过他虽然不知,但是此时复手在茅庐中左思右想,心里明白此地恐怕已经非是久居之所。这地涌夫人乃是老鼠成精,亦正亦邪,在这屋檐之下总会有一天小事变大,会有麻烦上身。
与其导致最终闹得不欢而散,还不如就此离去,也留下一份儿香火情,想到这里,张诚激流勇退之意更切,不过刚刚恶了别人,现在辞退实在是面上有些难看,他便打算过上俩三日便和师妹商量之后,联袂辞别。
他这里有所思想,而其他人也自己有自己的打算。
花开俩朵,各表一枝。
就论这地涌夫人回转自己厢房,怒气冲冲的想着如何夺了张诚元阳,又如何神不知鬼不觉的除掉沐凝冰这个竞争对手,而旁边的婢女虽然不晓得自家夫人的心中所想,却是也听到了当时二人在屋中争吵话语,也晓得的男女情事。
就见其中一个灵懂的当即边倒茶,边道:“奶奶,可是为那男女情事忧愁?先喝杯凉茶消消气。”
“你又知道什么!”
地涌夫人斜眼瞥了一眼,便端起茶水一饮而尽。
“奶奶,您定然是为除掉那贱婢伤神,是也不是?”
“废话!你是有什么办法,还不快快道来?”
“奶奶糊涂,要除掉她又有何难?”这婢女放下茶壶,又道:“夫人是这东道主,又是她二人的传授老师,此为我地,想个法儿,开个鸿门宴,杀了她便是。”
“哼,就你这蠢法子,本姑奶奶岂能想不到?若是惊动了那小子,他不委身于我,闹起来又如何是好!”
“奶奶平素里不是最恨那帮用什么上师灌顶妖言,做人皮唐卡法器,赚取女弟子肉身的苯教喇嘛吗?”女婢笑盈盈捏着地涌夫人的肩:“为何不来个祸水东引,先把这贱人赚出洞府,杀了之后把这黑锅扣在那镇海禅林寺的喇嘛僧头上?”
“这红口白牙的,他岂能信我?”
“为何不信?夫人乃是个十里八乡有生祠庙宇的活菩萨,那鱼龙混杂的喇嘛寺臭名昭彰,那该信谁的当然不言而喻,到时候再巧施美色,把他哄得五迷三道,到时候颠鸾倒凤生米熟饭,便是日后事发,人死灯灭,他又岂会对夫人辣手?”
这女婢的计策十分毒辣,而这地涌夫人金鼻白毛老鼠精听了之后,十分的高兴,面色立刻稍霁,转为欣喜。
“好,好个一石二鸟之计。此计若成,你就再我跟前当大丫头,掌这一洞老小便是。”
“谢奶奶垂恩!”
这地涌夫人干脆利索,立马便是草拟一份手函,把沐凝冰骗出洞外,知道是去外界散心,实则是内藏凶险,她也不劳动溘家老小,自己带着双股剑便出了洞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