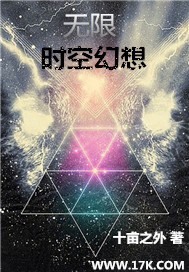开到荼靡花事了,上海的春天像夕阳里的影子,你刚踩住它的衣角,它已悄悄掠过了屋顶,等你抬头看去,它又飞的老高,只余下高楼大厦上半遮半掩,半阴半阳的痕迹,证明它驻留过,又匆匆离别了。
宥维和老爷去了欧洲半月有余,府上一如既往地平静,除了太太偶尔的两声咳嗽,刘管家的那些糊涂账,萼雪这段时间倒没什么可操心的,只是她总奇怪着,自上次舞会后,蓉蓉便和宪兵队上校陈浩川迅速陷入热恋,这速度,令一众旧时同窗都刮目相看。
斟酌再三的推荐了庄北楠,论才貌比那陈浩川不遑多让,又是世代做生意的商贾子弟,相较于硝烟战火中出生入死的军人,多的就是眼下人人需要的安稳。
萼雪从不做媒,一来她认为姻缘天定,不可强求,二来婚姻大事,关乎男女双方的终生幸福,若凑成一对美满夫妻,自然是积阴德,可若是夫妻不睦,日久成仇,媒人岂非成了他们的祸根孽端,因此,她不敢也不愿做那牵线搭桥的媒妁之事。
但对蓉蓉,她犯了戒,却也栽了跟头。
“唉!就知道我不是个擅牵线做媒的人!”她叹了口气,摇摇头苦笑着。
“奶奶,车备好了!”顺儿捧着件艾绿色的旗袍进来,看纹路是湖绉的布料,显得清爽又干净。
“刚让吴妈熨好的!”顺儿将衣服平平整整的铺在床上,又在衣服上放了两粒珍珠耳坠。
“对了,大爷那边可来了电报?”萼雪问道。
“来了,说是一切都好,让奶奶无须挂心,另外还需厂里再支六千大洋打到欧洲那边的账户上,说是要用。”顺儿回道。
“......怎么又要这么多钱。”萼雪嘀咕了几句,抬头道:“今天刘会计在厂里吧?挂个电话过去,我待会过去支笔钱。”
“是!”顺儿领命下去了。
说起刘会计,倒和管家刘贵是本家,两人虽是远房表兄弟,个性却截然不同,刘贵擅察言观色,处事上圆滑知进退,刘会计却是个极严谨乃至于有些木讷呆板的人。
“等会去支钱,又要听刘会计絮叨!”萼雪穿戴整齐上了车,对着刘司机埋怨了声。
“唉!我表舅就是这脾气,之前在府里管账,少爷要支钱都被他管的死死的,好在他人也是清廉,所以老爷对他向来看重,厂子那么大,流水似的钱来钱往,没他看住,真不知要亏空多少。”刘司机也颇了解他这个表舅。
萼雪听到这话不再言语,她初管家,正头疼不知如何面对刘贵的烂账,听到他的表兄弟如此清廉刚正,倒生了条妙计。
上海的地界比起北平,并非纵贯南北的开阔大气,相反,历来都是紧密密的算计安排,当时为了六华纺织厂的这块地,谭老爷煞费苦心,最终择在江湾大上海市中心区的殷翔路,如今地皮虽涨了价,厂子里却是一年难似一年。
未到门口,远远的已看到四五个人迎了出来,为首的是个中年人,姓周名桓,是副厂长,总管着厂里的大小事务,他身后的几个是厂里的小头目,萼雪看其中一人,有些眼熟,却硬是记不起来。
“哎呀!欢迎欢迎!少奶奶莅临六华,真让此地蓬荜生辉呀!”周厂长看车停稳,忙上前开门。
说他是个马屁精,他的确很会阿谀奉承,但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很会打通关系,税务局的,警署的,供货商的,他方方面面都交到了朋友,从六华在上海扎根落地到现在日渐兴旺,他算是大功臣。
“周厂长,看你,都是一家人,偏你礼节多,外人不知是我越俎代庖的来管闲事,只会以为税务局又来打抽丰了!”萼雪笑道。
“哈哈,不敢不敢,少奶奶幽默了。”周厂长知道她聪明玲珑,马屁话便点到为止,忙将她往账房请。
刘会计还是那副轱辘眼睛,磨磨唧唧的翻着账本,又拿算盘细细的算,蝇头小楷的字像隔着影纱描的,又端方又齐整,许是周厂长提前打了招呼,他没了那些絮叨,不过也是侯了半个时辰才把钱提出来。
周厂长又唤来两个保镖,准备护送萼雪去花期银行汇钱。
“看你,太周全了些,我这次来,还想去厂房看看,方便老爷问起来好交代。”萼雪虽然有了厂里的钥匙,却是一次都没来过。
周厂长权当她是来走个过场,便又笑着把她往厂房里请。
六华的厂房和其他纺织厂有些不同,一来机器的轰鸣声更大些,马力更足,二来就是女工的制服更齐整些,白围裙,棉手套,布包头,一应俱全,谭家的家风一向宽容待下,管理职工也是如此,虽然工资这两年减了,可给女工的安全措施却是一样不少。
众人上了二楼,沿着走廊看着一楼厂房里的运作,大锅炉里的蒸汽热腾腾的往上飞,一股股机油味熏得人恶心,巨大的电力推动着青黑色的轮轴,杠杆,支架,顶针,一经一纬的密密纺着那淡牙黄的布料,女工们立在机器的间隙里低头劳作,倒像钢铁巨兽齿缝间的食物残渣,脏脏的,毫无生气的被咀嚼着。
“周厂长,国际五一劳动节要到了,厂里可有什么工人活动?”萼雪扭头问道。
“唉~!少奶奶,什么劳动节,眼下刚接了日本的一批订单,正是加班加点的时候,哪里能有什么活动,无非是有些奖金,还是您往日提的。”周厂长心里知道她聪明,却也知道她的不切实际,锦衣玉食的少奶奶,讲些仁义道德的生意经,实在令人想发笑。
“嗯!”她点点头,也不好多说什么,空中楼阁般指点江山,她知道有些滑稽。
围着三个大厂房走了一圈,到了最后一个,明显看出了些异样,厂房里的工人似乎少了些,那些之前攒动的人头变得稀疏多了。
“看来游行过后,有批人已经离开了。”她心想着。
上次舞会后,斯兵赛·罗德的纺织厂已经紧锣密鼓的运作起来,为了让中国人好接受,还引经据典起了个中文名——“织女”,对外的口号是中美合资的国际型工厂,日日都在《时报》《字林西报》上打广告,上海的工人社团里又有被买通的托儿,绘声绘色的向他人宣传着厂子里多么多么好,引得一群不明真相的女工人来签了工作契约。
织女纺织厂是否真像外界传言的那么好,萼雪不敢断言,但他们厂里的机器,都是之前被迫倒闭的厂子遗留下来的破铜烂铁,赚钱,或许有,风险,则更多。
谭家人往日来厂里视察,历来都是不进到车间里,远远的听着汇报就好,可今天,萼雪停住了脚步,远远地看着什么东西出神。
周厂长顺着她得目光看去,心里一怔——是个小童工!
原来自从上次游行事件过后,有一批工人已经离职,后续的人力补充不上,订单却随着时局动荡多了起来,无奈,他便听了手下人的建议,先招进一批童工补缺,这事儿本是偷摸着进行的,也没想要持续很久,只等谭老爷快回来便遣散这批童工,今日听说少奶奶要来视察,已提早让童工们回家了,谁知这里竟有个漏网之鱼。
“周厂长.......童工兹事体大,《国民政府工厂法》的新规定了不准招14岁以下的童工,就算满了14岁,也只能从事轻便的工作,像这样梳棉工,小孩子怎么胜任!”萼雪语气中带了愠怒。
“是是是,我不知道怎么昏了头,听了小人唆摆,一时心软,留了这个没爹妈的孩子在这里打工糊口。”周厂长辩解着,猛地回头朝身后就是一声吼:“武弛!都是你干的好事,滚出来!”
听到武弛,又见人群里出来个三角眼,高颧骨的精瘦汉子,她一下恍然大悟了。
——原来是他!
“您侄儿将来发达了,少不得做牛做马回报少爷少奶奶!”吴妈当日的奉承犹在耳边,不想还没来得及找宥维谈这事,武弛已悄摸摸的寻了门路来“催”她。
可惜,谭家一向重信誉,这样欺上瞒下,胡作非为的人留着便是祸患。
更何况,周厂长等一干人也脱不了干系,若不来个杀鸡儆猴,以警效尤,以后口子放宽了,便再难收回。
“去,把她唤过来!”萼雪指了指那个埋头在流水线上的女童工。
监工把那女童工领了过来,只见乱糟糟的一头长发,被破了洞的包头粗粗扎起,脸上乌糟糟的都是黑泥,分不清何种布料的衣服从洗得发黄的围裙缝隙里挣脱出来,活像她身上的肉烂了,又生了脓,肿胀着绽开一条条沟壑。
“你叫什么呀?”萼雪有些心疼,低头看向她。
那小姑娘怯怯的缩着身子,纸片般的肩膀筛糠般颤抖。
“她叫小花,是潭子湾的棚户,无父无母,前年和她爷爷从苏州乡下逃难来这里,上个月她爷爷病死了,邻居便把她介绍来这里做工谋活路。”监工解释道。
“唉.......是个孤儿了!”萼雪心里叹了声。
她父母也走的早,爷爷奶奶将她带大,姑姑教她读书做人,可有些东西,谁都替代不了。
想到这里,她心里满满的都是怜悯,转而,她愈加愤恨身边这些视人命如草芥的吸血鬼。
“周厂长,六华素来赚的都是良心钱,靠着这份良心,我们老爷才能在上海滩站稳脚跟,你跟着谭家,劳苦功高,按理我当唤你一声周叔叔。”萼雪说这话在笑,看向众人的眼神却带萧瑟的怒意。
周厂长明白她的意思,脸上也是颇难堪的神色,身后的武弛更是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
“少奶奶,这事是我误听谗言,坏了规矩,下不为例,我会立刻整改,至于始作俑者,六华容不得他!”说完,周厂长斜眼狠狠瞪了武弛。
弃卒保车,兵法中的上策。
萼雪并未言语,只向顺儿叮嘱了句:“送这孩子去澡堂子里洗个澡,换身衣服,家里最近伺候的人手不够,让她出了厂子就是断她活路,不如来府上跟着伺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