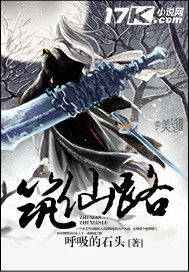中国人习惯低眉顺眼,习惯在蛰伏中计算着来日方长,也习惯对事物边观察边质疑,对人性本善的质疑,对因果循环的质疑,甚至对自己的人生亦充满着质疑,这些质疑深埋血肉,只待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将其剖开,便展现在世人面前。
顾华奇没有这些习惯,他也从不质疑发生在他身上的任何事情,他认为所有事都应顺其自然,所以被捕后,他毫不犹豫的背叛了,一五一十的供出了昔日的战友,连同谭府的五百大洋,也成了他埋怨的理由,家大业大的谭府掏出这么点钱打发他一个常委,他不服,他要给蔑视他的人一点教训,哪怕这教训将带来性命攸关的后果。
他满足于自己的机敏,得意的点起了一支“哈德门”,那是他最爱的牌子,焦香的烟草里有股清凉油的味道,直窜向脑门,这令他神台清明,凭着这点自以为是的清明,他认定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至理名言。
抽着烟,踱着步,推开了洒满阳光的落地窗,正看见楼下一个修剪得有棱有角的花坛,青翠的树叶在方形的框里,延伸出去的部分都被园丁修剪成了直角的形状,浓绿的伤口中偶尔滴下两滴汁液,都化在满是苔痕的青石砖路上,瞬间不见踪影,这令他想起一个魔术,那还是上个星期在江汉关码头表演的戏码,先借来一位美丽女士的手绢,在迅速交错的瞬间,把手帕偷偷赛到袖口里,等到美丽的女士向他投来惊愕、崇拜的目光,他方才手腕一抖,把那手帕原原本本的又变回来,他很享受那种感觉,那种被关注,被围绕,被赞叹,被崇拜的感觉,那是隐姓埋名,深藏幕后的根据地给不了他的。
一阵歌声打断了他的思绪,那声音来自花坛旁一面灰白色的高墙内,这里面关押着他曾经的战友,如今于他而言,则更像邀功的筹码与加官进爵的台阶。
他笑了,为这些人的酸腐书生气,囿于铜墙铁壁之内,还能朗声高歌,实在是有些黑色幽默。
他满意于自己的务实,便又畅快的吸了口烟,舒服得眯起了双眼,就见路口拐弯处驶来了一辆福特汽车,那是台产于1920年的黑色老爷车,偌大的两个车灯,像圆睁的双眼,半拱形的车头,气派又充满男人的勇猛感,自从他来了上海,他一直想要这么一辆车,最好能带着花枝招展的长三女先儿,去高级餐厅用餐,什么牛排,面包,还有闪烁着银光的餐具,都如梦如幻,都触手可及。
沉醉在痴梦中,他笑了,很快笑容僵在了脸上,因车上下来个熟悉的人影,那是谭家公子——谭宥维。
“怎么!?昨晚熊司令不是派了人去谭府兴师问罪吗?怎么没把这家人抓起来!”他有些惊慌,心虚的猛抽了两口手中的烟。
紧接着,又下来位深色旗袍的年轻女人,凤眼柳眉,极清雅,倒是没见过。
“有钱人就是好,身边的女人都是个顶个的漂亮。”他吐了口唾沫,将烟蒂子狠狠弹进花坛里,避回了房间。
这里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外面看却极像一座严密的城堡,双层门楼,墙体顶端设堞口,二层楼台设岗楼,土黄色的墙面因岁月侵蚀,满是陈旧腐败的沧桑,可经年的萧杀之气,还是让看到它的人遍体生出寒意,只因这里所关押的,都是所谓的“地下党”。
一男一女两个门神脸的守卫细细搜过了身,确认没有锐器或不安全的东西,才放萼雪和宥维进来。
进门就是敞阔的前院,有棵丈来高的芭蕉立在中庭,因阳光充裕,便贪心开了满树的花,红艳艳的像吐着蛇信子撩人,一位秘书模样的女人从芭蕉叶下迎了出来,笑容却是极谨慎。
“谭少爷,谭少奶奶,熊司令今日会鲁主XI去了,特命姜副司令接待二位,来,仔细脚下台阶!”秘书招呼着,带领着两人往楼上去。
“副司令!?若是推给了副手,那说明昨晚上的事,他们上上下下早就通了气,想来那五千大洋早早也瓜分干净了!”想到这里,萼雪心里便觉气愤,民脂民膏搜刮了那么多,又霸占了教育界那么些经费,如今借着汉奸倒戈的机会,还来敲老百姓一笔竹杠,真真是密网子捕鱼——大小都不留。
“姜副司令~!”秘书娇甜的唤了声。
一位中年男子回了头,倒是两道浓黑英气的剑眉,眼神炯炯的锐利,扫在人身上,令人胆气生寒,二人瞥见那“一杠双星”的领章,大概知道了他的资历深浅。
“姜副司令,你好!”宥维跟他握了手,三人便在会客室落了座。
“司令部威风呀!上个月还去江北练场看了操练,果然是保家卫国的铁骨男儿,有这气势,日本人哪里还敢嚣张。”宥维递上支登喜路的雪茄烟,自己也点了支,烟雾缭缭升起,人与人的距离变得模糊,矛盾似乎也就有了转圜的空间。
“哈哈,保家卫国,军人本色嘛!说起来,令尊也曾在去年的战役中支持过我们,算是我们熊司令的旧相识,这次的事,实在是郑副官无礼了!”姜司令似乎是少抽雪茄的人,话音刚落就咳了声。
把过错推给下属,那便是含糊其辞的不愿承认自己的看法,这官场套路宥维岂会不明白,忙又点头笑道:“司令言重了,谭府一向谨遵良民守则,府里上下都是守法公民,郑副官来了,也亲眼见到了,确认情况属实才离开,所以无礼谈不上,只怕是无心。”
姜司令脸上的笑意多了几分,点头道:“谭厂长明白就好了,毕竟有人已经向我们举报了,我们吃官家俸禄,肃清乱党是己任。”
“这自然,这自然!”宥维点了点头,又试探性的问:“听卢局长说,此人是地下党的重要领导,不知姓甚名谁,又是否交代过何时混入谭府的。”
姜司令将烟灰弹进烟灰缸里,又嘬了口雪茄,意味深长的一笑,道:“何时混入谭府不重要,何时从谭府偷到那笔钱才是重点,这些地下党,有了钱便目无王法,怎能让他们如愿!”
听到这话,萼雪和宥维皆松了口气,正要说话,又见姜司令脸色沉了沉。
“目前是非常时期呀,谭厂长!断不能让乱臣贼子在眼皮底下招摇过市,若此人招供的越多,他便越安全,反之,他便越要吃苦。”姜司令讲这话时像在思考,讲完又抬起头看向二人。
“当然,当然,司令部励精图治,整肃上海内乱只是起点,这我们明白,也会全力支持,纺织厂如今虽大不如前,但我和父亲一样,赤诚忠心向着党,只要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宥维极认真的点头表态。
“言重!言重!若保家卫国的军人要老百姓肝脑涂地,别人倒要笑话我们白吃军饷了!”姜司令大笑起来。
“哈哈,姜司令幽默呀!”宥维,萼雪两人也跟着笑了起来。
“我听姜司令口音,不知是否是南京人?”萼雪方才不便插话,见气氛稍稍缓和,便开口问了句。
“喔!那倒不是,不知谭夫人何出此言?”姜司令见萼雪问的突兀,便有些好奇。
“我可忘不了上次在光明饭店宋夫人举办的交谊舞会,您和夫人真是一舞惊人,都说南京人跳起舞来风度翩翩的,所以我才有此疑问。”萼雪笑着道。
“哈哈,过奖了,过奖了呀,谭夫人!”姜司令笑的便有些骄傲。
方才略局促的气氛在这声笑中消弭殆尽,此刻,再往下,便是势均力敌的交易了。
“南京好地方呀!六朝胜地、十代都会,出了多少了不得的大人物,如今您和夫人长居上海,一定有空要来谭府坐坐,到时,内人亲自下厨,做几道拿手上海菜给您尝尝。”宥维邀请道。
“诶!方才还说不能白吃军饷,这会儿又要我白吃美味佳肴,二位给我添了不少心理负担呀!”姜司令抬了抬眼皮,又笑了,空着的那只手在椅子沿敲了敲。
“心怀天下,自然是负重前行的,何况姜司令如今身居要职,为了我们这些老百姓,自然是辛苦些!”萼雪也笑了。
接着,就从提包里掏出只小犀牛皮五寸见方的盒子,看了宥维一眼,递给了他。
宥维将那盒子递到姜司令面前,颇诚恳的道:“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国军实在够得上这样的赞誉,我见姜司令行事严密,必然在时间上争分夺秒,这有两支家父亲选的百达翡丽,望姜司令能笑纳,另一支您转交给熊司令,就说是谭府上下的一片心意。”
“若不是姜司令这样戎马倥偬的赤胆军心,眼下上海时局也不会这样日趋平静,所谓礼轻情意重,姜司令务必给我等表示心意的机会!”萼雪忙补上一句,话说的是极诚恳。
“见外了!见外了!”只见姜司令眼神闪了一闪,起身便开始推却。
“这可不光是我们的心意,最重要的是老爷与两位司令的交情,您若不收,岂不是要我们做后辈的为难!”宥维将表盒恭恭敬敬的放在了办公桌上。
那紫黑色油亮如漆的皮质,沉甸甸的都是富贵的重量。
姜司令皱了皱眉头,深深吸了口雪茄,道:“唉!国之火种,承上启下,你们年轻人难免犯错,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总可以拨乱反正,如今你们人来了,心意也来了,我若不收,倒显得我计较了,那我就暂且代表熊司令收下,日后若再与谭府打交道,我一定让下属谨记尊重二字!”
“谢姜司令!”二人不禁松了口气,只要这礼物送出去,那谭府的风波可算是告一段落了。
三人正在交谈着,就听隐隐的歌声传来,唱的什么听不清,倒是悲壮雄浑的气势滔滔。
“这是?”萼雪小心翼翼的问。
“呃!一群糊涂人罢了!”姜司令尴尬的笑了笑。
两人不便多问,告辞后便离开了司令部。
站在窗台的姜司令目送两人走远,便把那表盒丢进了抽屉中,又将一盆万年青摆在了窗台上,从窗台望出去,正是那高墙之内,森严的三排平房宿舍,低矮潮湿,除了屋顶的一溜气窗,再无阳光可以洒进去。
这厢刚破财消灾,一家人还惴惴不安的琢磨着是否有后续,那厢谭老爷便接到了张市长秘书的电话。
这通电话讲了很久,谭老爷的脸色时阴时晴的不停变换,刚从司令部回来的两人在旁边看着,心里也是七上八下。
等电话讲完,下人端来的茶水早就凉透了,老爷觉得口干舌燥,将就的抿了一口,才缓缓道:“是兆顺洋行的幕后股东——斯兵赛·罗德在搞鬼,他仗着手上有大笔现洋,所以便联合一些同路的商界名流,想妄图先搞垮六华等一干老厂,等到我们撑不下去,他们再低价收购我们的设备厂房,这如意算盘打得可是真精明!”
萼雪似乎想到什么,问道:“前些日子我隐约听人说,上海有些设备老旧的纺织厂,比如华美,顺南已经都关门倒闭了,起初我以为是竞争激烈的缘故,现在想来,该不会就是这些洋人恶意收购的的吧!”
“可恶的是这些人都藏在水下,没人伸手捞捞还发现不了,要不是备了厚礼去打听,这背后的人至今还揪不出来!”宥维有些恨恨的道。
“今日是税务局的新规要从账上划走一笔,明日是市长大寿要送的厚礼,再来就是司令部的明里敲诈暗里勒索,到底是年景不好,牛鬼蛇神都出来横行霸道!”萼雪怨着。
老爷摆了摆手,道“现在说这些也无用,我们需要登报澄清收买警局这件事,否则他们一直抹黑六华,我们名誉扫地,以后如何在上海立足?”
“文化界的朋友倒有,登报的事并不难,只是......”萼雪沉默片刻,道:“只是需防后手,我看这个斯兵赛·罗德没那么容易罢休,不给他教训,他不会知难而退。”
“只是洋行都是财主,我们要反击,若不能一击即中,恐怕到时还会打草惊蛇,被群起而攻之。”宥维沉思道。
“此事不宜先动手,眼下我们已是被动,还是等登报以后,信誉挽回了,再从长计议。”老爷是积年的生意人,凡事求一个稳字。
宥维和萼雪对于老爷的最终意见,一贯只用点头,毕竟传统中式家庭,若人人都争做那拍板定案的人,再和睦的家庭都得乱套。
“司令部那边暂时不必担心,他们既收下了钱物,短期内便不会再来找我们麻烦。”老爷看了眼宥维,又道:“我和宥维下周就动身去德国,看看那边纺织厂的先进技术,然后进口一些好的机器回来,只是这次出国所费颇巨,近期又流水似的花了大钱,须得从厂里的公账上划一笔货款先挪用着,另外府里近日会有一次大的宴会,到时贵客临门,一切事务必须尽善尽美,雪儿,你要多花些心思了。”
萼雪点了点头,似想起什么,又道:“老爷不在的时间,我定会照顾好太太,既然下周就走,要带哪些人提前说,我好做准备。”
老爷点了点头,表示随萼雪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