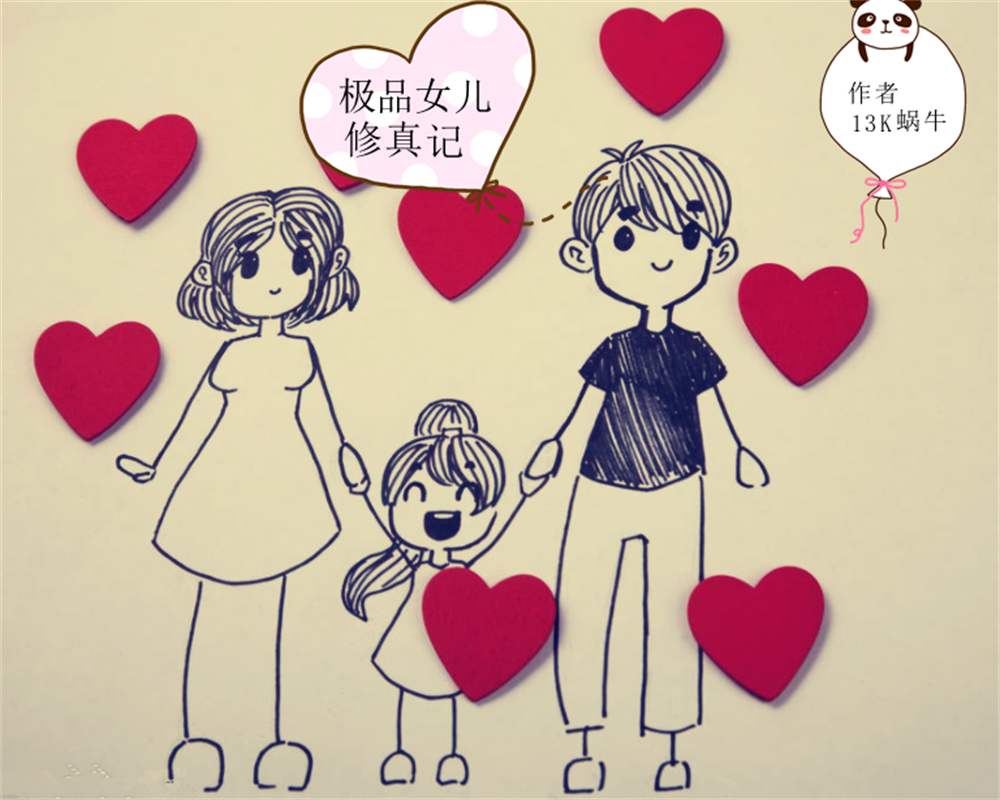从思明道沿着花坛骑行几百米,是燕大的北院,有德、才、均、备四幢男生宿舍,传闻宿舍砌墙的砖都是清明两代留下的城墙砖,又用素灰勾了缝,所以外表看来格外严肃深沉,好在有数根修长的大理石罗马柱嵌入墙体做支撑装饰,整个建筑又在中式的肃穆中多了些挺拔的西洋精致,再往西是穹棱拱顶的华氏体育馆,沿着体育馆旁刷得雪白的健体道一直骑到头,就到了燕大的西校门,这是座单檐王府大门式校门,面阔有五间,中间三间为三框对开大门,两侧稍间为门房,五步台阶两侧一对从淑春园的遗址里搜寻到的石狮子,虽历经百余年,依旧不怒自威,镇压住了来自西山的荒野之气。
这时节正是春风有意,百花留情,燕大学生喜欢凑几块钱租两只毛驴,从西校门出发,骑着小毛驴往西山上去看风景。
玄岳载着萼雪往校门口走,沿路遇到相熟的同学,他都殷勤的一一打招呼,萼雪坐在后座,却尴尬的不知如何是好。
及到了校门口,就见姚梦熊和一班男同学骑着毛驴刚从西山下来。
见到二人奇奇怪怪,不免会心一笑,眼神中都带了几分戏谑的神情。
“梦熊~!”萼雪坐不住了,从后座跳了下来。
“咦!你们两这是要去哪儿?”姚梦熊似笑非笑的看着萼雪。
“看到方海了吗,我们这会儿正找他呢!”萼雪也笑了笑。
“哦~!刚才我们一起爬山的,他先下的山,说是中午有饭局。”其他同学答道。
“那你们还往山上去吗?”姚梦熊又问。
“我们.....”玄岳正想说。
“不去了!”萼雪已经打断了。
这声“不”,算是给了玄岳决绝的回答,也将他的暗恋情愫斩断于此。
哪个少年不钟情,从施德楼骑车到这里,萼雪便觉出来那些与平日的不同,虽说以前他也是这般绅士,也是这般凡事想着她,只是今天,似乎多了些试探,那是她意料之外的。
她不想深究他的想法,那是一种不敢,不忍和不知所措,往日,何尝没有好事的同学向她吐露一二。
只是,今天不同了,她下定了决心。
在河边读到那句——“你这只美丽可爱的小鸟,要把我的心衔到什么地方去呢?”那一瞬间,她想起的是方海,是他挺拔的鼻梁和藏青色的中山装,那颗情窦初开的心像苹果,“碦”的被人咬了一口,痛痛麻麻痒痒,甜丝丝又带着些青涩的酸。
听到她的回答,玄岳的语气又变得跟平日一样沉稳冷静,向其他同学点了点头道:“对,我们不去了!”
听到这个回答,她不敢回头看他,因为她听到了他心里的失望与落寞。
同学们笑闹着走远了,两人还在原地沉默着。
终于,他先开了口。
“今天天气真的挺好,我陪你走到山腰就回吧!”他的语气不悲不喜,如旧。
她点点头,终于回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令她有些心疼,他的眼神分明是难过的,攅着自行车把的手用力到了发红,平日高挑的运动员身材蓦然矮颓了很多,她明白,他的心此刻一定是一片寒冷的死灰色。
“给痴情的人不切实际的幻想才是最大的残忍!”她努力安慰着自己,笑着跳上了后座。
她希望给她一个甜美的笑容,告诉他,感情的表达方式可以有很多种。
他也看着她,笑了笑,眼睛闪了一闪,又平静了下去,他总是那样,不笑的时候眼如潭水,笑起来就是清波,很招惹人。
“坐稳了!”他的语气充满着安全感。
西山并不陡峭,他却蹬得很用力,肩胛骨的轮廓时隐时现,不一会儿竹布长衫就打湿了一小块。
她想拿帕子帮他擦擦汗,却没有伸出手,他那么可爱,又那么聪明,她却只想保护他。
自行车在山腰的一个坳里停了下来,那是茂密桃林的深处,粉云压枝,密密层层,人在里面,也像被云裹挟着在飘。
“从这里往下看,燕大是不是显得很小,像座小城,像被遗忘似的。”玄岳坐在一旁的石头上,双手搭着膝盖,端端正正的像个军人。
“是呀~!我总以为燕大是乌托邦,是风雨不侵的城堡,可是......”她顿了顿,又道:“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已经嗅到了革命的气息,我们肩上有没有属于我们的使命呢?最近,我多了很多疑问。”
玄岳看着她,眼中多了些温柔,片刻又消弭,仍旧认真的道:“阮君,我们太渺小了,只是被这时代推着走,走好自己的每一步,比起去操心这个时代,前者更重要。”
“玄岳,我听蓉蓉说,你与方海常去广和居参加聚会,席间谈的都是国家大事,又听说上海有了新的政党,我们的老师也是党员,不知你是否有耳闻?”萼雪带着些试探,小心的询问着。
“你们小姐妹平时也聊这些吗?”玄岳笑着望向她。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你们能关心,我就不能吗?”萼雪笑着反问道。
玄岳没有回答,只扭过头看山间的云游走,如层如积的聚拢在燕大的上空,将那亭台楼阁,飞檐斗拱的华丽遮蔽,只余那朗朗书声破出迷雾,飘摇直上。
“你当日读书是为了什么?”玄岳还是没有看向她,却问了她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我......大概是为了自己.....又或许是为了父母,你突然问起来,我倒有些说不清。”她有些震惊于自己的回答,也愕然于自己的迷糊,竟连个读书的缘故都说不清。
“我父亲是1889年的进士,本已打算到归德府上任通判,谁知次年八国联军侵华,皇帝太后出逃,中央的任命文书被烧毁,无奈之下,他只能避开战火,狼狈回乡。知县怜他人才,给他挂了正术的闲职,亦有进士俸禄。按理说是衣食无忧的富贵闲人,此后却一直郁郁寡欢、终日酗酒,每每烂醉之时,便大吐苦水,以未投身报国为耻。”玄岳忆起过去,眼底出现少有的伤感之色。
“我母亲曾告诉我——学而优则仕,走上仕途,男儿大丈夫才能掌握风云,运筹天下,我以此言为警示,故从不敢懈怠学习。”玄岳读书以来,奖学金是年年必有,想来除了刻苦,便是如此掷地有声的决心。
萼雪望着眼前的玄岳,似乎对他有了新的认知,那个总是沉着冷静,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原来内心盘旋着一只志在千里的鸿鹄。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萼雪念出这首诗,又由衷的关心道:“玄岳,你有青云志,将来可定要娶一位具停机德的贤妻辅佐你。”
“开拓者都是孤独的,我不敢妄求知己,只求有人能稍稍懂我心事足矣。”玄岳说这话时,才回过头,他的眼神炙热,却又在冷静中切换着,像内心有煎熬,欲语还休。
“玄岳~!”萼雪有些心疼他。
他又扭头看向了云海深处,此刻山岚吹散,阳光射透桃花瘴,把那万千花蕊一一点亮,漫山都绽落了金色的华彩。
“他朝芳菲自有信,花蕊相对共此心。”萼雪又对着他笑了笑,这笑容充满的是理解,是爱,是怜,是重视与疼惜。
玄岳也对着她笑了笑,似卸下心中千钧担。
也许,正与萼雪想的一样,她对他爱的表达,非他初始所愿的那种,可收获到另一种世间少有的爱,未尝不是让人怦然心动的幸福与甜蜜。
二人说笑着下了山,又在女生宿舍前道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