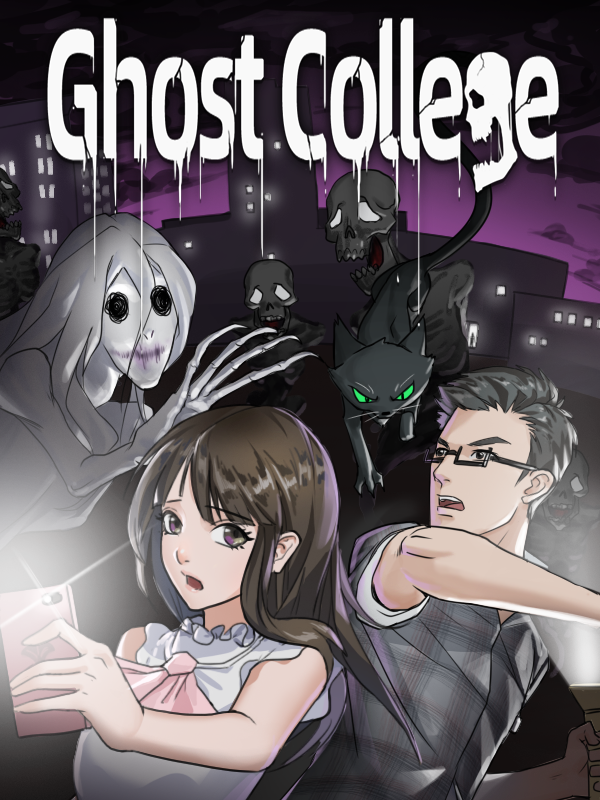“你要自认为自己还算个汉子,”林跃轻轻地说,“就找一个心平气和的日子,和她把话说明白了,别拍桌子,别拿你自己那一套衡量别人,听听她怎么说……黎默我告诉你,我认识顾安安这么长时间,就没见过她跟谁红过脸。不用说客户投资人之类的,这个牵扯到职业素质——就是张轩那前妻在她面前那么找茬,你看见她气急败坏了么?看见她连话也不听就摔门走人了么?”
黎默终于迷茫地抬起头来。
“唉,怎么二了呢?”林跃嘀咕一声。
顾安安确实很少发脾气,即使是让她恨得牙根痒痒的那些人,一般也只能激发出她的杀气,很少能有什么事把她“气炸”了。
她很烦,但是连个林岚之类的狗头军师也没有,甚至没有人梳理她毫无缘由的愤怒。
于是蛋饺的大鱼大肉生活终结了,从此过上了每天吃猫粮的苦逼日子——把这个吃货郁闷得每天没精打采,连沙发也懒得挠了,没过几天竟然忧郁得开始掉毛,后背居然出现了一块斑秃……
另一个表现就是她开始夜宿公司,没完没了地亲力亲为各种事,以致于所有的计划都提前进行了,跟补课老师抢进度似的。
后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工作狂是一条不归路——当她打乱了计划,把所有的东西都提前着手的之后,等过了几天,她终于平静了一点,那点怒火被肝功能自动消化了一部分、大姨妈平稳离开的时候,顾安安就发现……停不下来了。
刚起步的公司事只有越办越多的,她一开始躲着黎默,自发自愿地在办公室泡着,就导致了后来就是不得不在办公室泡着,有时候死狗一样地回家,好不容易睡一觉,上下眼皮还没来得及凑在一起相思一下,一个电话来了,又得出去。
她看着忧郁的斑秃蛋饺,终于良心发现地给它改善了伙食,算是百忙之中积攒人品,以免落到和它一般的下场。
等黎默企图重新振作起来,主动去找顾安安的时候,就连顾安安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哪了。
她一出差就是半个月,回来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坐在办公室喝口水,就听说楼下有一位先生找她,已经等了她好几天了。
擦咧,顾安安阴沉着脸想,现在才想起来找老娘讲和,黄花菜都凉了,没门!不见!
结果她就这么想着,端着还没来得及喝的水杯下楼了。
顾安安下楼梯的时候还想,难道是黎严那条生产线谈下来了?怎么李伯庸这么有空天天来等?不对啊,就算生产线谈下来了……之后的接洽、资产重组的杂事也应该挺多的。
等她走到会客室的时候,才发现,这位“等了她好几天的先生”并不是黎默本人,而是他外公。
老头还穿着一身乡土气息十足的棉布衣服,洗得发白,但是很干净,脚下放着一兜看不清是什么的东西,估计是老人家自己种的什么,坐在新沙发上,只敢坐一个边,好像生怕弄脏了什么东西似的,僵直着哪也不敢碰,一看她进来,立刻站了起来。
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新一代的劳模顾安安同志的睡眠加起来总共也就二十来个小时,本来连眼都快睁不开了,却在看到李老先生的那一刹那,奇迹般地肾上腺素飙升,清醒了。
“爷爷……”她甚至有点手足无措地站在他面前,“您怎么来了?我刚出差回来,您看您也没提前说一声……”
不会是姓黎那王八蛋出了什么事吧?顾安安已经在昏迷的良心出现了一点清醒的迹象。
她惴惴不安地看着黎默他外公李爷爷面前那杯一口没喝的水,转身从会客室的桌子底下翻出一盒茶叶来:“要不我给您沏杯茶吧?”
“不用不用,别忙啦!”李爷爷看见她,脸上笑出一朵花来似的,“见着你就行了,喝茶咱们家喝去,这是公家的东西,可不好瞎糟践。”
“……”顾安安眨巴眨巴眼,干咳一声说,“爷爷,这是私企,‘公家’有百分之三十是我家的,您放心,一杯茶喝不完这盒的三分之一。”
老人愣了片刻,好像还不大能明白她说得这些事,只是冷眼旁观,觉得这些来来往往的人都听顾安安的,让他觉得她是个了不起的姑娘。
“哦,是啊?”他拘谨地笑了笑,屁股稍微离开了沙发一点,小心地接过顾安安给他泡的茶,捧在手里,不知道该感叹什么,只是过了好一会,才轻轻地说,“我年纪大了,又没什么文化,好多事不知道,你别往心里去。”
他讪笑一声,脊背划过一个不自然的弧度,就像他的背不是自己弯下去的,而像是被什么压弯的一样:“我就是来看看你们……嗯,你,跟我那败家孙子,都挺好的就行了。”
很早以前,听黎默提过,他外公年轻的时候是个脾气火爆的人,因为他犯的一点错,老头子拿着皮带追着揍,结果也可能是那年头皮带的质量也相当一般,居然把皮带都给抽断了。
顾安安看得出来,李爷爷不适应这种转着弯的说话方式,他小心得过分,显得紧张而不知从何说起。
于是她犹豫了一下,主动交代:“呃……我们前一段时间闹了点别扭。”
李爷爷抬起头来,目光从老迈的、充满松弛和皱纹的眼睛里射出来,并不清澈,甚至有些浑浊,像是几十年的喜怒哀乐混合在一起,彼此谁也分不出谁的那种浑浊。
“是怎么回事呢?”
这句话彻底把顾安安给问住了,她突然沉默,那一瞬间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怎么回事呢?连她自己也说不清。
整个人生经历的不同,观念的不同,甚至迥异的价值观。
顾安安知道黎默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他更像是那种老一辈的商人,精明、宽厚、有大局观,但是对风险异常警惕,是个彻头彻尾的风险厌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