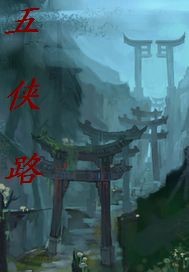剑鸣七个老人望着面前的两个人,其实就是望着一个人,而另一个人直接被七人随意带过,七人的眼光落到王苏棋的身上,王苏棋能感觉到,但是他没有勇气抬起头,但是他的心中却带着某种侥幸,希望七人能够认出自己,但是他却失望了,七人的目光就像过眼云烟般,又想天际的流星般快的难以捉摸,快得来不及享受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王苏棋低着头,七人的目光移开的那一刻,他的心头一松,带着某种诡异的安慰,和浓烈的失望充斥他的心,安慰的是他如此狼狈的样子没有被他的师尊发现,失望的是,他如此处境没有被发现,那么他又该如何翻身。
带着无比尴尬的心情,他慢慢抬起头,小心把眼光投向那七个老人,投向那七个老人中的一个,投向他的师尊,投向清风子。
但是此刻清风子的眼中完全没有他,清风子的眼光浑浊但是又带着某种炙热,这种炙热的眼光不是赐予给他的,而是那个披着他的皮的人,千面郎君。
剑鸣的风带着剑鸣独特的味道,这种风王苏棋在大夏峰的小院中吹了几百个日夜,日日吹,夜夜吹,每次吹着剑鸣温暖的风都有一种莫名的享受,在外域的日子中也会莫名想起,但是外域的试炼毕竟是短暂的,所以王苏棋没有在意太多,当他再次回到剑鸣,吹到剑鸣独特的风的时候却莫名觉得风有些冷,有些烈,仿佛烈酒洒在心上的灼烧感,仿佛寒冬腊月身披单衣站在寒风中般。
七人的目光很自然冷落了他,冷落了这个与剑鸣毫无关系的人,但是千面郎君那里又有另一番感觉,七人的目光齐刷刷的落在千面郎君的身上,千面郎君突然觉得周身一僵,一种莫名的害怕在心底涌起,这七个人每一个都修为高深,而更可怕的是这七个人全都在望着他,他的心里一瞬间闪过无数个念头,刚刚的欣喜顿时被恐惧所掩盖,他有些后悔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还是传说中梵天第一宗的盘。
如今这个时候,千面郎君觉得进退维谷,他不明白为什么偌大一个广场上只有他一个人,这是一个陷阱吗?他的心底也知道面对这七个人他是毫无还手之力的,哪怕只有一个都会把他当做蝼蚁一般捏死,但是他的手中还有一个底牌,他的这张底牌就是王苏棋的命,他不自觉的瞟了瞟一旁的王苏棋,但是他的心底还是没底,第一他不知道这张底牌够不够硬,第二他不知道所谓的正道究竟是什么样子,反正魔道中碰到这种情况便是一个结果那就是两个人都得死。
这种尴尬的情况没有持续太久,七个老人中有个老人向王苏棋这边招了招手,示意“王苏棋”过去,千面郎君一愣,该怎么办?他望了望那个老人,只见那个老者白发白须白袍,面容苍老却很慈祥,看着他招手的样子,千面郎君的心莫名轻松了一些,这个手势好像在哪里见过,如果千面郎君再没有动作败露是迟早的事情,既然入了虎穴那便既来之则安之,千面郎君正了正衣襟大步走向前去。
虽然只有两个多月没有见到王苏棋,但是清风子却很想念这个弟子,这种想念不仅仅是因为王苏棋是剑鸣的归宿,也不仅仅是他喜爱王苏棋。清风子浑浊的双眼,和满脸的皱纹很好地解释了这个问题,他老了,人既然老了总有些莫名的挂念,所以他望着“王苏棋”的眼神是那么亲切,这种眼神在四百多年前是绝对不会有的,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因为今天他老了。
千面郎君虽然决定地很干脆,但是他的心却已然在敲锣打鼓,他走到那个老者的面前,保持着两米的距离,他不知道这个老者意味着什么,他也不知道这个老者的身份,甚至不知道老者与王苏棋的关系,但是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
千面郎君站在老者两米开外的位置恭敬一礼,随即跪下重重磕了几个头,这个过程中,千面郎君没有说一句话,没有说话便是最聪明的选择。
老者一愣,随即哈哈一笑,轻抚了下齐腰的白须,其余六个老者纷纷微笑颔首,清风子手腕一抖撩开拖的很长的衣袖,上前一步扶起“王苏棋”,笑道:“棋儿,你懂事了,为师很欣慰啊,看来外域的试炼还是给了你颇多的体会啊。”
清风子扶起千面郎君,千面郎君听到清风子的话,眼珠一转,心中一松,站起来的千面郎君依旧低头恭敬说道:“一切还是师尊的教导。”清风子眉头一挑,道:“哈哈,没想到两个月的时间,你小子的嘴是越来越甜了,不错不错。”
清风子的话让千面郎君的心蓦然一松,但是千面郎君却不敢多说话,又是恭敬一礼,站在一旁没有言语。
偌大的广场上顿时陷入了一种沉默,只有幽风轻轻吹过,清风子这时才真正注意到那个一直站在那里的人,于是问道:“棋儿,这个人是谁?”
千面郎君不紧不慢,他已经想好了说辞,于是恭声说道:“禀师尊,此人是弟子在外域遇到的魔教弟子,被弟子降服一心归于我宗,我思索着我们乃是名门正派既然有魔教的弟子要改邪归正,那弟子也不好痛下杀手,所以弟子擅作主张将他带了回来。”
清风子捋了捋白须,笑道:“不错不错,既然是你带回来的人还是跟着你,若是他表现好也不是不能考虑让他拜入门派,棋儿你这是大功一件啊。”
那边师徒情深,这边王苏棋孤独着站在那里,看着那个人夺走属于他的一切,享受着原本属于他的温暖,微风中的王苏棋感到了一阵无力,这种无力来自心底,来自最薄弱的那丝灵魂,剑鸣的风还是那样的风,但是王苏棋却觉得此时的风好像吹散了他的灵魂,吹走了他的思绪一直飘到很远很远,很高很高的地方,然后重重摔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