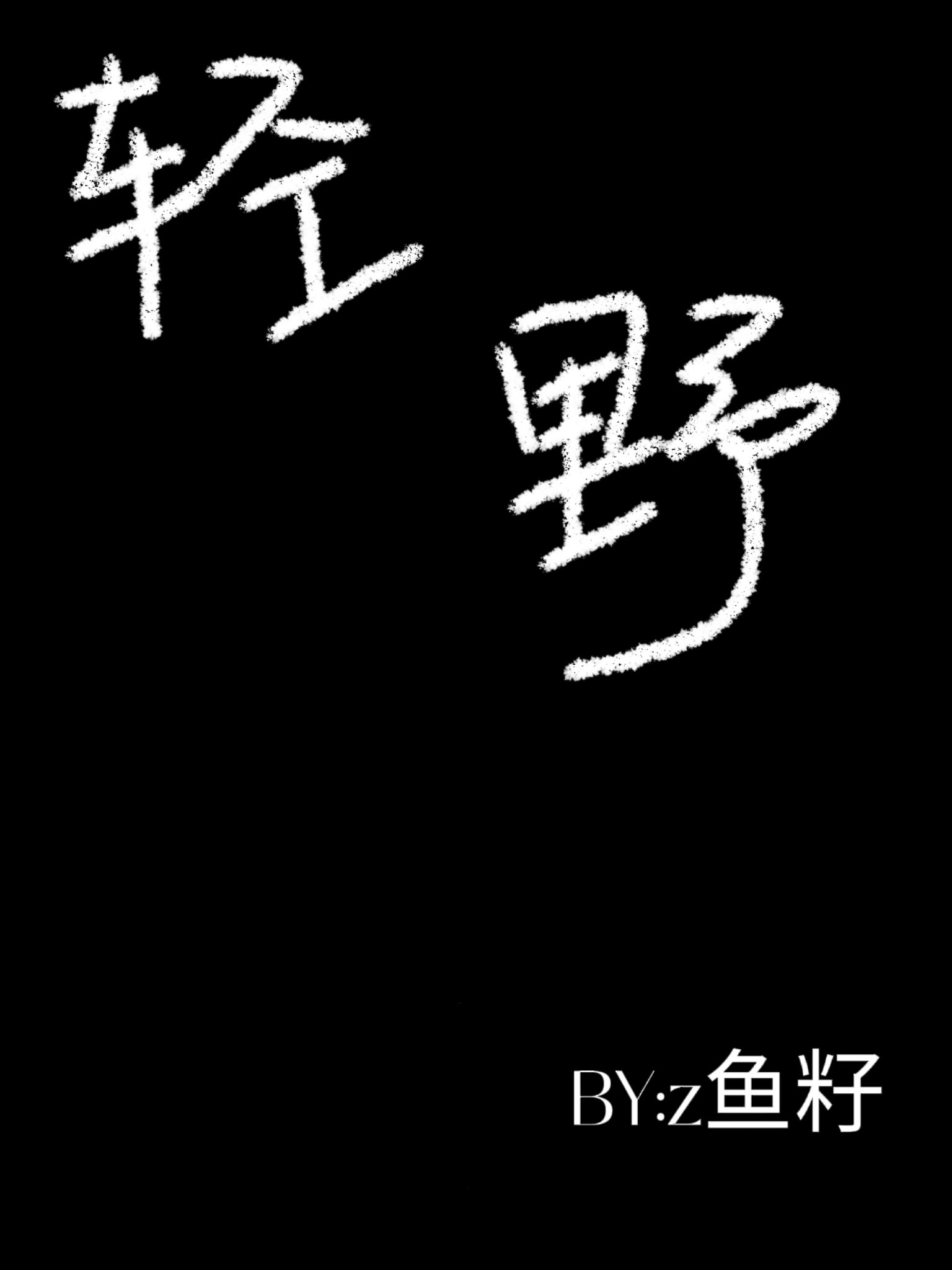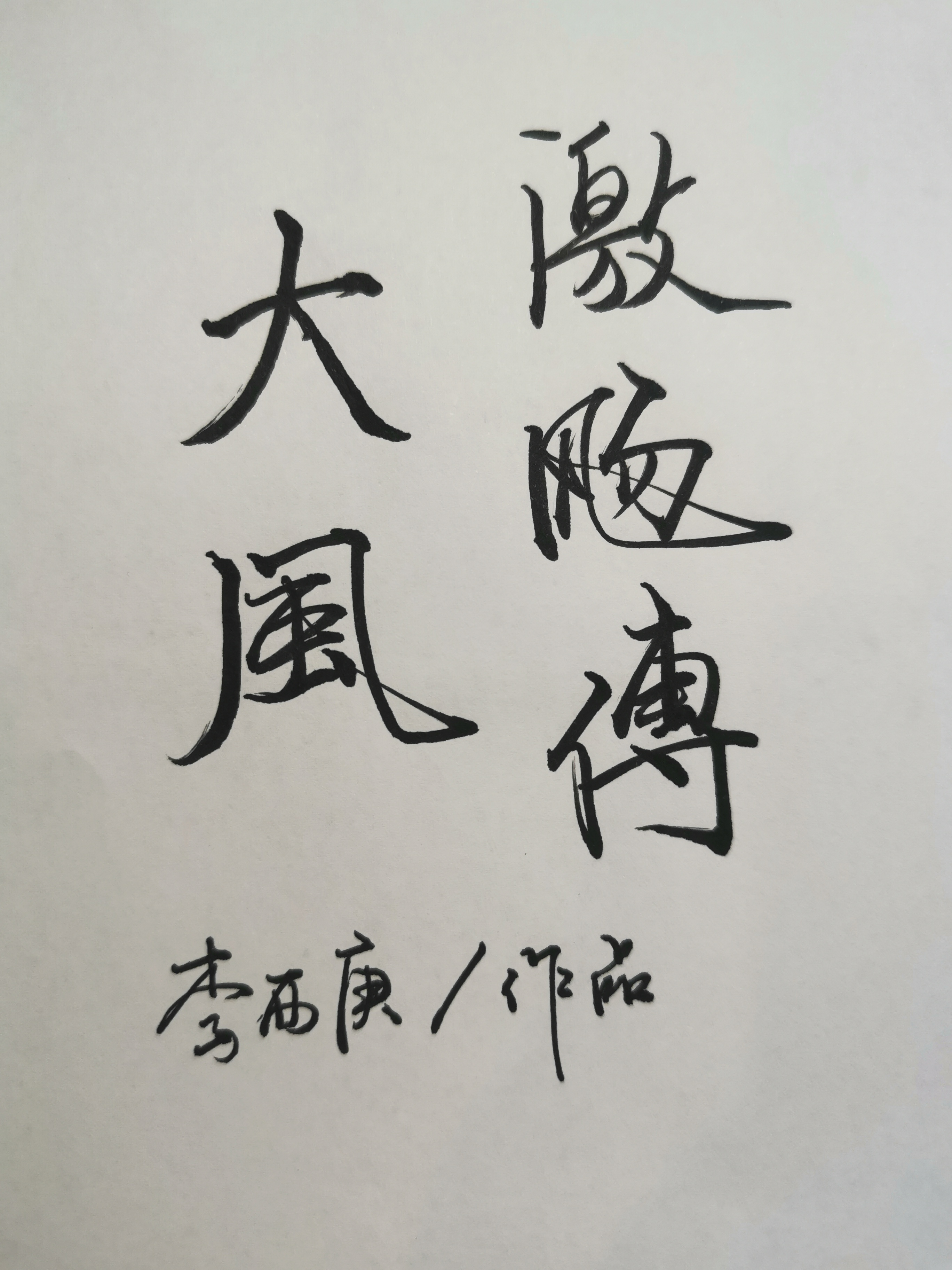从医院回家之后,多笑笑经常面无表情地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发呆。多宏毅夫妇以为多笑笑在为毁容而痛苦难过,只能在一旁不知所措地唉声叹气。
但多笑笑听不见他们的叹息,她目光呆滞地突然站起身子,要往外走。
“你去哪儿?”陈晓丽紧张地站起来,多宏毅也跟着站起来。
“我去外面走走。”多笑笑的眼睛转动了一下,她伸直胳膊,扭动一下身子,“睡得太久了,浑身不舒服。”
“那我们陪你去吧。”陈晓丽随手拿起一只口罩,递给多笑笑。
多笑笑摇摇头,“不用了。”
“还是戴上吧。”多宏毅看着陈晓丽手中的口罩。
多宏毅低着的头上,白发增加了许多。隔着老远,多笑笑都能嗅到他身上浓烈的香烟味。她没有再说什么,接过口罩戴上。
他们走过一片又一片田地,路过一户又一户人家,大家仍然像往常一样向他们打着招呼,不过他们看多笑笑的眼神已不似从前,不是多了怜悯,而是多了其他的东西,多笑笑很轻易地便察觉到了这点,但是她不愿细想,也不愿承认。
在一棵华叶如盖的榆树下,多笑笑停住脚步,回头看向身后,多宏毅夫妇站在离她身后两米的地方,望着她,眼神里满是讨好的意味,太过于明显了,她的心中油然而生出一种惭愧,她讨厌这样的眼神。
“爸、妈,咱们家最近应该也耽搁了不少活,是吧?”
多宏毅摇摇头。
“你们去忙吧,我想一个人走走。”
陈晓丽也急忙摇头,“不用,不着急。”
多笑笑走近他们几步,用恳求的眼神看着他们,“去吧,真的不要再跟着我了。”
多宏毅夫妇只好回去,带着一肚子的担心。
多笑笑看着他们走远,迅速拐上了一旁的山路,去了后山。后山上的野花正开得烂漫,五颜六色的,微风拂过,很是美丽。然而这是鲜有人到访的后山,没过脚面的野草,让这个静谧的地方变得神秘,并掺杂了些许恐怖的气息。多笑笑却没有留意到这些,她表情木讷地一直向前,走到悬崖边上,脱掉鞋和袜子,坐下来,将脚垂下去,双脚浸在风里,全身凉爽起来的同时,心里也畅快了许多。
她顺着脚尖往下看,在鬽山,这里就是波涛汹涌的幻海,凭着记忆,她似乎真的看见了幻海,但是无论她怎么努力,脑海里都形不成幻灵或者其他人的样子,倒是隆虺的脸,清晰无比,她甚至听到他在自己耳边讲话……多笑笑闭上眼睛,使劲摇摇头,隆虺的声音散去,林家栋的低吼又在耳边回荡起......她抬头看向天空,白云清风依旧,她却觉得憋闷至极,几乎喘不过气来,她捶着胸口站起来,朝着山崖大喊大叫。
“笑笑,快回来,笑笑......”
多笑笑回头,身后是多弘毅夫妇,他们张着双手,担心地看着她。小时候,多笑笑刚开始学走路时,他们就是这样的动作吧,害怕她跌到,小心地用双手为她围出一个保护圈。她看看脚下的悬崖,再看看风中略显老态的多弘毅夫妇,原地蹲下,失声痛哭。
林家栋最终没有回来,对于多弘毅夫妇来说,那已经不重要了,所以当林家栋的母亲充满歉意地告诉他们没有联系到林家栋时,他们几乎都没有听见,只是无所谓地笑着点了点头。
陈晓丽将家里的所有镜子都收了起来,卫生间的镜子,是她以不小心失手打碎了为由,使其彻底消失掉的。多笑笑像一具行尸走肉,穿梭在村子里、后山上和家里。她看起来很憔悴,似乎几天几夜未合过眼睛,黑眼圈围绕着她布满血丝的眼睛,以前水汪汪的眼睛现在变得洪浊不堪。蓬乱的头发罩在脑袋上,让人觉得反胃。多弘毅终于看不下去,在她再次拒绝吃饭的那一刻,彻底爆发,他把碗咣当一声摔在地上,碗里的汤和面条洒了一地,一块碎片迸进了书桌低下,掉在了多笑笑的脚上。这还不够,多弘毅依旧怒火满胸,他开始破口大骂,骂多笑笑是个懦弱的人,是个胆小鬼,是个没有良心的不孝之女......陈晓丽哭着把多弘毅拽出了房间,过一会儿,她提着一把扫帚走进来,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扫地,扫了半天,都不见扫干净。多笑笑呆呆地坐在凳子上,看着她。
“我想出去走走。”
“好啊。”陈晓丽停下手上的活,勉强笑一笑,“我陪你去。”
“我的意思是......”多笑笑将头扭向窗外,“我想离开这里。”
“离开这里?”
“嗯。”
“什么时候,我们一起走。”
多笑笑没有作声,上床睡了。陈晓丽终于将地板弄干净,她关了灯,悄悄走了。院子被埋在黑暗里,夜空中一弯新月,沉浸在碎宝石铺成的银河里,时间仿佛被静止一样,没有了声息。
多笑笑开始准备行李,其实也没什么可带的,她的大脑一片空白,根本想不起来路上需要什么。但在陈晓丽的眼里,多笑笑带走了一切,她抚摸着多笑笑的行李,感觉沉重得喘不过气来。她从仓库找出自己已经多年不用的行李箱,去了自己的卧室。
多弘毅知道她要做什么,起身挪了个地方,好让她能利落地收拾。
“出去也好,省得闹心。”他皱着额头上多出来的那条皱纹,吐出一口烟,“等笑笑好点了,就提醒她回家来。不过不要太唠叨她,她会烦的。”
陈晓丽自顾自收拾,没有理他,他依旧自顾自说着,“家里你不要担心,我会照看好的。走哪了,有什么困难,你就给我打电话,我们一起想办法......”
陈晓丽收拾好了行李,心里才踏实一点。多弘毅去地里干活,她就守在院子里,她在等,等多笑笑提着行李从房间一出来,她就会拉上她的那只大箱子,不管多远,她都跟着去。然而多笑笑像是忘了自己要走的事,时间过去了好几天,她都没有再提过。
有天晚上,多笑笑喝醉了。那个时候,多弘毅夫妇已经睡了,多笑笑在房间里找到了不知什么时候放在柜子里的两瓶白酒,她开了灯,从床底下拿出一面镜子,那是陈晓丽告诉她不小心打破了的卫生间的镜子,其实是被藏进了仓库。她一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边咕嘟咕嘟喝酒。喝进肚子的酒越多,脸上的那条疤痕就变得越粗,越狰狞,她拿起空了的酒瓶,朝镜子里的疤痕砸过去。
“去死啊!”她对疤痕大喊。
多弘毅从梦里惊醒,陈晓丽已经穿好鞋子,正往外跑。跑到院子里时,大门像一张巨大的口,吐着骇人的黑。陈晓丽跑向笑笑的卧室,里面没有人。多弘毅拿来手电筒,追着陈晓丽的脚步跑向后山。他们没有说一句话,黑夜里只有焦急的呼吸声,村子里的狗被惊动,凶巴巴地吠叫着。陈晓丽的眼泪和汗水在脸上蒸腾灼烧,她感觉什么东西堵着嗓子眼,肺剧烈地疼,腿在发软,但是他们还在狂奔。
陈晓丽“啪”地一声摔倒在了地上。
“笑笑?笑笑?”多弘毅喊着,跑过来,从陈晓丽脚下扶起多笑笑,黑暗中,是浓烈的酒味和发烫的额头。陈晓丽忍住痛,也爬过来,她帮多弘毅把笑笑扶上他的背,捡起一旁的手电筒,一瘸一拐地在前面带路。
“他爸,送她去那里吧。”黑暗中,陈晓丽哽咽着说道。
“嗯。”多宏毅轻声应道,“不过再等等吧。”
“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