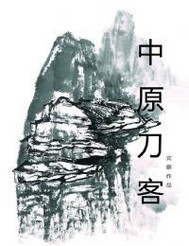俗话说,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不到晚饭的功夫,孙迁染花柳的事情已经传遍前锋军每一个兵士耳中。第二天天一亮,各级将领也都获悉此事。
前锋军中军大帐,各营偏将齐聚。趁着孙迁未到,都在交头接耳。
“哎,听说了吗?孙迁将军染花柳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常年打仗是个男人也受不了啊。”
“不过孙将军怕是饥不择食啊”
“这选姑娘就要选肤色白皙嫩滑的,若不是孙将军……”
几个偏将聚在角落里嚼舌根,说的那叫一个绘声绘色。许是声音大了些,又引得两名好事者上前凑热闹。
正在这时,帐外一声长喝:“孙迁将军到。”
众将闻言连忙各自走到大帐正中分列两班,随后一阵甲胄声响,帐外走进一员大将。
来者比寻常人足足高出一个头来,走起路来虎虎生风,那面相实在是有够猛恶。只见其面如重枣,双眼犹若铜铃相仿,一双浓黑剑眉直插入鬓,蒜头鼻子大嘴岔。再加上一身甲胄挎着腰刀,这摸样真如庙里的金刚画上的太岁一般。
众将齐齐抱拳道:“孙将军。”
孙迁鼻子里哼了一声,大步走到正堂条案后落座。
“各位将军请各自就座吧。”孙迁摆摆手,众将闻言各自落座。
有兵士持了水罐来到孙迁身旁,在条案上的海碗中倒了一碗清水。孙迁有个习惯,每日升帐议事总要喝一大碗水。
喝了水,孙迁伸手一抹嘴巴,这才粗声道:“昨日元帅给咱前锋军派了一个新将军来,叫什么张大奎的,此人据说有些本事。昔年后宋大兴之时,此人便是大将军。后宋亡了之后此人也就此销声匿迹。不过不知怎么就做了江南通政使,还去了云南招降梁王。结果梁王不买账,险些将他杀了。他独身一身逃回江南之地,又因贪赃之罪入了狱。”
说到这里,孙迁看了看众位将领,这才续道:“说这些,无非是想问问众位将军,你们想叫一个鸡鸣狗盗之辈来做你们的大将军吗?”
众人面面向觎,却皆是不发一言。孙迁见状不由得大怒:“嚼闲篇一个个这般来劲,说正事便都哑巴啦?”
骠骑营千总起身向孙迁拱手道:“将军息怒,张大奎即是中军委派,无论其是何等样人,却不是我等可忤逆的。想徐元帅将此人派来前军,自然有其道理……。”
“道理个屁!”孙迁拍案而起,指着这骠骑营千总骂道:“瞎了你的狗眼,这前锋军中大将军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我孙迁。”孙迁绕出桌案,在大帐中来回疾走,半晌又道:“在朝中,我乃皇亲。在军中我也是拿军功说话。那张大奎什么玩意?一个待罪的囚徒,也敢与本将军相提并论?”
众将惊若寒蝉,都知道孙迁的脾气,故此没人再说一句话。孙迁在帐中来回走动,半晌才道:“我已传下将令,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入军营,我倒要看看那张大奎如何来赴任。”说罢走回条案后的太师椅落座。
望着众将,孙迁又道:“前锋军每日按平日里的法度操练,就算没有那张大奎,我孙迁一样能练好兵马打胜仗。”说罢端起水碗,将碗中清水一饮而尽,这才吼了一嗓子:“散帐。”
风轻云淡落日余晖,大奎立在帐前遥望远处,缓缓将右手的鸡腿放在嘴边咬了一口,直吃的满嘴流油。左手拎着酒葫芦,不时喝上一口。这烧刀子入口甘冽,甚合大奎口味。大军马上要开拔兰州,军中每个人都忙的没头苍蝇一般,唯独大奎清闲自在。
情闲不是没来由,伙头军有真校尉盯着,杨小虎不时来照应一下,故此大奎才有闲暇躲在没人处吃喝。
随手将手上鸡骨头扔了,仰头喝下最后一口酒。大奎这才满意的咂咂嘴,还有些意欲未尽的意思。
拎着空酒葫芦,慢慢悠悠的向回走,刚好酒劲上头,大奎飘飘欲仙好不快活。
刚回到伙头军营地,迎面碰上一人,却是一名伙头老军。老军见大奎回来了,忙上前拦住大奎去路。
“张校尉啊,你怎么喝成这样?不要命啦?”老军如此一说,大奎却是满不在乎。
老军续道:“军中不得饮酒,这你不是不知道。若是被监军看见,谁也保不了你。”
“监军?哪里又冒出个监军?”大奎醉眼朦胧,望着老军已是两个影。
老军左右看看,忙拉着大奎到了僻静处。这才语重心长道:“国有国法,均有军规。军中不得饮酒,这是定律。张校尉先在此少待,我去给你泡壶茶来醒醒酒。”
大奎呵呵笑道:“你这人不错,茶就免了。我回去睡觉。”说着大奎回到了营帐中倒头便睡。老军站在账外不由唉声叹气一番,自去忙自己的了。
未及天黑,大奎正睡得香,突闻帐外一阵铜锣响。接着就传来脚步纷杂之声,大奎不仅烦躁起来,拉过被子蒙住头脸接着睡。不想帐外连滚带爬奔进一人来,却是那个老军。老军奔到大奎床边气喘吁吁道:“张校尉快醒来,监军点某了(点名)。”
大奎迷迷糊糊一推老军,口中喃喃道:“别吵,我正睡得香…好酒!”
老军急的一把揭了大奎的被子,将大奎拉了起来。
“张校尉莫要拿性命耍笑,快跟我走。”说着架起大奎出了营帐,帐外不远处伙头军数百人早已齐集完毕,老军架着大奎来到人群中站定。还好监军还未到,老军四下望了望,这才在大奎耳边轻声道:“莫要言语,只管站在这。等点某的时候应一声便了。”
大奎站在原地,身子直晃荡。老君无奈只得扶着大奎的肩膀站在大奎身侧。
不多时,场外一声高唱:“监军大人到。”本是噪杂的人群立时静了下来。
暮色中行来一人,锦袍玉带头顶笼巾,胸口绣着孔雀朝阳图。这监军大人一路行来说不出的潇洒飘逸。这也难怪,军中俱是见惯了军服铠甲,猛然来个三品文官,却有鹤立鸡群之感。
监军到了众人前站定,身后行军主薄忙凑到监军身旁低声问道:“大人,开始点某?”
监军鼻子里哼了一声,行军主薄向着建军一躬身,这才向着众人扬声道:“念到谁的名字谁就应一声。”说着翻开手上的账簿开始念道:“校尉方勇。”
伙头军那个真校尉忙答道:“在!”
行军主薄又念道:“校尉张大奎!”半天没人吱声。
监军却是道:“且慢,这伙头军怎么有两名校尉?”
行军主薄忙道:“回大人话,这是新来的校尉。姓张名大奎。”
监军又问:“此人何在,为何没人应某?”
“这……。”行军主薄无奈又喊了一遍:“校尉张大奎!”还是无人应答。
大奎站在队列里,竟是打起了呼噜。站着也能睡着,真是咄咄怪事。老军推搡大奎几次不见反应,心中不仅暗道:“完了,这下没折了。”
监军站在人群外,却正在下风口。大奎一身酒气隔老远就能闻到,监军自然已有所察觉。
“是谁违反军令私自饮酒?自己站出来”监军板着脸冷声问道。
众老军你看我我看你,竟是无人搭话。监军见没人站出来,当即向前走了几步,随后分开人群占到了大奎身前。
说来也巧,这监军喜好干净,平日里沐浴更衣都要熏香一番。而大奎醉酒之时最闻不得檀香味,这监军一到身前,大奎睡梦中眉头一紧,接着腹中一阵翻江倒海。“哇”一声,竟是吐了监军一身的污秽之物。
监军毫不防备下遭此突变,心中自然是火冒三丈,当下厉喝道:“违抗军令私自饮酒,竟是醉成这样。”说话的工夫不禁后退数步,早有侍卫上前替他擦拭污物。
监军指着大奎道:“把这目无法纪之徒与我绑了。”话音一落,另有两名侍卫冲到大奎身前,一左一右架了大奎拖出人群。
监军也不点某了,带着亲随扭头便走。
大奎醒来之时,却是浑身被五花大绑的丢在一座营帐内。身子动了动却是越动越紧,无奈之下只得作罢。按说军中饮酒,论罪最轻也是五十军棍。但大奎得罪的却是监军大人,监军发了狠,定要将大奎斩了方解心头之恨。
大明军中自有军法,军法曰:士卒触犯军令者斩,校尉以上将领皆一视同仁。不同之处在于,校尉以上将领犯了军令要斩首,须报请大将军核准方可动刑。
监军大人找到孙迁报曰:“昨日酉时点某,伙头军中有人违令饮酒,以致大醉不醒,为正军法请大将军定夺。”这监军单单忘了报上名字。孙迁却是不敢善做主张,一时没了主意。元帅徐达已将其贬至副将,主将印信早已收回。既然不是主将,便没有生杀大权。孙迁无奈,只得命人将张大奎看押起来。